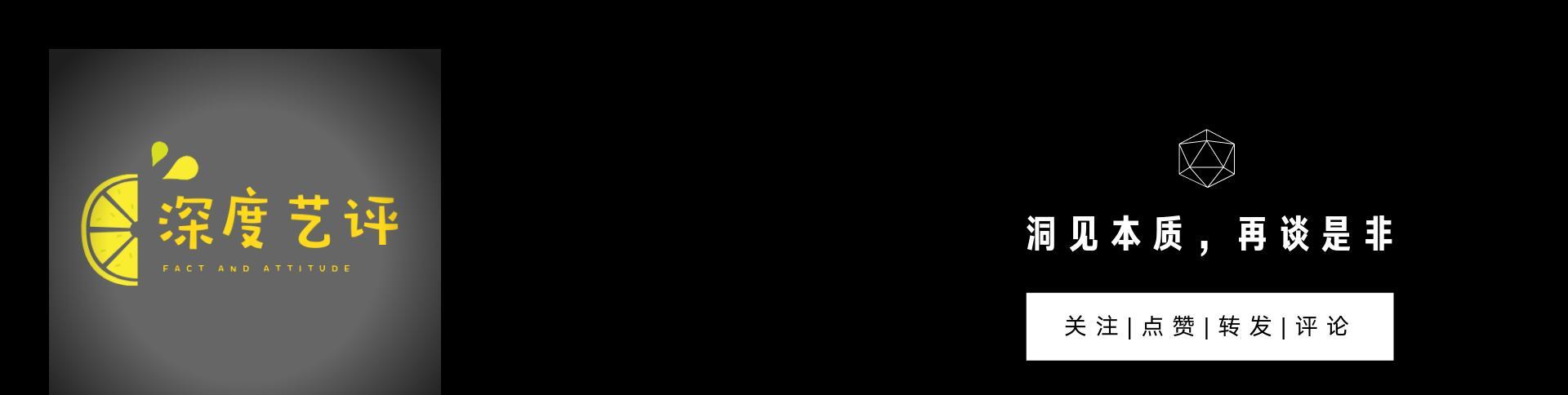
作者:小太爺
一個是背景高貴、錦衣玉食的富翁,一個是家境貧寒、入不敷出的貧民。
很難想象在現實生活中他們會以怎樣的形式産生交集,但這部根據真實事例改編的電影為觀衆提供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可能性。
“這就是我想要的,沒有同情心的他。”
菲利普是一位高位截癱的病患,盡管他的财富足以支撐其度過一生的時光,但每一天幾乎都是煎熬。
在推掉了衆多前來應聘的陪護專家後,他毅然選擇了剛剛出獄且隻是為了拿失業補助金的德希斯
因為在他身上,菲利普看不到那種使他挫敗與頹靡的同情。
面對他人的苦難,我們似乎都熱衷于泛濫自己的同情心,但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又何嘗不是對當事人的二次傷害?
而電影《觸不可及》則提供了一個真摯且溫暖的答案:對他人最大的溫柔,不是同情,而是共處。
<h1>殘障群體的内心獨白</h1>
當我們以正常人的姿态去窺探殘障群體的生活時,我們可以一眼望穿他們生活的窘迫與無奈。
“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在憐憫與同情的驅使下,我們總會以一個提供幫助的“志願者”身份去涉足于他們的世界。
這是一種充滿正義感的越界,我們在付出,可能是無償的,也可能是有償的,但不管怎麼說,從事這樣的工作的确可以給人帶來一種人道主義的滿足。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說,殘障群體從外界得到的幫助越多,他們所失去的也會越多。
“你這樣生活友善嗎?”
“你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嗎?”
“還是我來吧,你這樣比較吃力”
在他人善意的提醒與刻意的躲避中,殘障群體看到了他們的小心翼翼,也看到了他們的良苦用心,但這些也無時不刻地都在強化正常人與殘障群體之間的界限。
在電影中,菲利普便是這樣一個在溫室中被呵護的殘障人士,他活在衆人的同情與憐憫之中。
但也正因如此,他失去了往日的自信與尊嚴。
大家都試圖讓他遠離外界的危險因素,就連出行工具,他也無法選擇。
所有人都預設了,體驗危險是正常人才能擁有的權力,但沒人能意識到,菲利普想要做的,就是成為一個正常人。
有時候,菲利普以及像菲利普這樣的殘障群體,他們需要的不是細緻入微的呵護,而是淡然處之的平視。
<h1>逃跑可恥,但很有用</h1>
恐懼、不安以及挫敗,對于那些在苦難中掙紮的殘障群體來說,這個世界是鋒利的。
而為了抵禦傷害,他們也會由表及裡地為自己構造一個盾牌。
“如果痛苦,那就别努力了。”
對于正常人來說,這是一個極具消極意味的價值觀,但對于菲利普這樣的殘障群體來說,這可以被當做是一種用于自保的規避機制。
在很多時候,我們都太過固執,以至于時刻準備着與這個世界針鋒相對,但卻沒有勇氣以及決心完成一次戰略性的撤退。
菲利普在失去了對生活的掌控權後,他也學會了逃避。
“他們來參加聚會,主要是來看我是否還活着。”
對于自己的生日聚會,菲利普盡管猜到了許多人是并非真心對他進行祝福,但他每次都會裝作很驚喜,以掩蓋他的真實情感,以避免不必要的尴尬與麻煩。
不僅如此,他同樣也逃避着他的愛情。
由于對自身的懷疑和自卑,他隻能接受柏拉圖式的戀愛,而恐于讓對方了解到他現在的處境。
而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一群體的内心寫照,即他們對于痛苦的體驗已經“習以為常”,但誰又原意為自己不斷劃上新的傷疤呢?
戰勝現實的不幸,本身就是一場戰線極長的拉鋸戰,而殘障群體無論是在心理上還是生理上都毫無優勢可言。
逃避是一條不甚光彩的小路,但他們也由此獲得一種不可多得的安全感。
逃跑可恥,但很有用。
<h1>讓愛治愈自我</h1>
如果說殘障群體與正常人之間在哪一點上不存在功能性差異的話,我想答案應該包括由個體内在建構的自我。
但無論是受他人同情,還是主動逃避,這些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傷害到當事人的自我意識以及自我價值。
那麼到底是什麼能治愈受到傷害的自我呢?
我想《觸不可及》便提供了答案,即愛,它可以來自友情,也可以來自親情,當然也可以來自愛情。
但同情與憐憫就不是愛的表現形式嗎?
我想沒人會否認人們是出于對他人的愛才表現出同情與憐憫,但這種愛若不因地制宜,其結果便是傷害。
而比起直白地流露出同情與憐憫,“不問過往,不問将來”的共處可能更能讓殘障群體感受到一種真摯且舒适的愛。
德希斯雖然無陪護的職業經曆,更沒有過硬的專業背景,但他懂得如何與菲利普共處。
在生活上,他給予了菲利普以正常人的待遇,因為他知道,對于菲利普來說,沒有比擁有一個正常人的待遇更讓他高興的事了。
而當菲利普難過或者逃避時,他可能并不了解,但仍會主動留出一段心理上的距離,而這便是愛的默契。
面對他人的痛苦和難過,你或許無能為力,但你所需要做往往隻是出現在那裡。
至于對方是沉默還是傾訴,請給予對方充分的選擇權。
有時候,愛是克制,而是迫不及待的表達。
《觸不可及》以無比幽默且輕松的筆調講述了跨越階級的兩個人是如何互相治愈的故事。
并以獨特的視角關注到了殘障人士這樣一個弱勢群體,并提醒着我們,除了對他們提供生活上幫助,如何呵護他們的内心世界,或者說如何使他們重建一個擁有足夠自尊與自信的自我也是我們應該思考的課題。
當然,電影也提供一個可以借鑒的方案,即與其同情與憐憫,不如以行動(共處)歸還他們所失去的做一個正常人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