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索菲亞·古德弗蘭德(Sophia Goodfriend);譯/龔思量
編者按:今年7月,多家新聞媒體揭露了一家以色列公司NSO旗下的“飛馬”(Pegasus)軟體服務如何為不同人士或組織所用,以監聽多國的反對派和異見人士、記者以及普通群眾。然而,作者在采訪了多位以色列網絡間諜公司的員工後發現,國際社會的批評并未引發以色列高科技社群的重視。對于在特拉維夫高科技社群工作的榮民們而言,他們已經習慣去忽視自身工作的道德後果,并心安理得地享受這些工作帶來的豐厚報酬。榮民通過以色列政府建立的軍事和高科技領域“快速通道”,将“以國家安全名義進行的監視技能”轉移到基本不受監管的私營部門,這些部門也一直在未經群衆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監視。目前,記者、民間社會組織和政界人士聯合要求私人監控行業遵守國際人權标準,這可能會帶來變化。但更為重要的是,員工和群眾需要意識到以色列的私人監控行業背後的重大危害,并不再把這些工作視作“無害”的高薪職業。本文原載于《波士頓書評》,作者索菲亞·古德弗蘭德(Sophia Goodfriend)是杜克大學文化人類學的博士生。她的博士研究處于科學技術研究、監控研究和數字權利的交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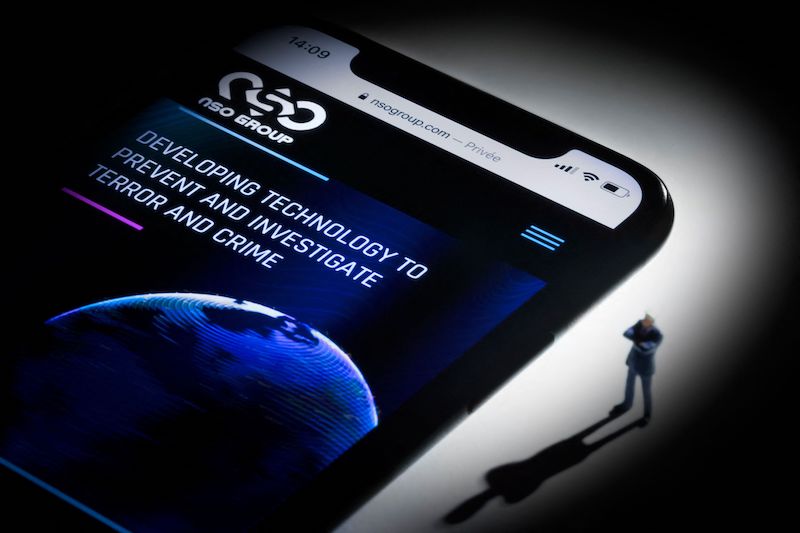
飛馬(Pegasus)
今年夏天,一個由17家媒體組織組成的聯盟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指控以色列網絡間諜公司NSO集團。這個由記者組成的聯盟與民間社會組織合作,聲稱世界各地數以千計的異見人士、人權工作者和反對派政客已經成為了NSO的“飛馬(Pegasus)”間諜軟體的目标。一名美國白宮發言人譴責該行為是“法外監視”,這引起了全世界的憤怒。然而,在以色列與世隔絕的高科技社群内,幾乎沒有人對這一消息感到震驚。
上個月,曾在特拉維夫一家間諜軟體公司工作的J在特拉維夫市中心喝咖啡時告訴我:“在這裡,整個倫理問題都被淡化了。”我問J,為什麼在以色列的高科技生态系統中,似乎很少有人關心對NSO集團的新一輪批評。不願透露姓名的J表示,這是一個文化問題:私人監控公司的大多數員工“會被各種條件吸引:工資、假期、很酷的工作氛圍和辦公室”。“在特拉維夫,這并不罕見,”他說,“你可能在向一家不尊重人權的公司出售軟體,但人們不會對此進行深入思考,因為他們賺了很多錢,整天待在漂亮的辦公室裡工作。”
NSO集團是過去10年内進入以色列高科技領域的“少數幾家小型間諜軟體公司”之一,該公司推銷的間諜功能曾經是軍事超級大國的專利。大多數此類公司都在全球各地設有辦事處,比如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或以色列國防軍(Israel Defense Forces)的8200網絡部隊(Unit 8200),公司中不乏從世界頂尖情報機構挖來的開發人員和分析師。這些公司将侵犯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人隐私的能力賣給出價最高的人:無論是像沙特阿拉伯這樣的獨裁政權,還是像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這樣的私人罪犯,并由此賺取了數百萬美元。今年夏天的爆料更是揭露了其罪行:調查報告發現,約5萬名不知情的平民手機上存在NSO的飛馬軟體,其中包括記者及其十幾歲的孩子、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等知名政客,以及巴林的政治異見人士。
盡管國際媒體和聯合國等管理機構譴責NSO侵犯人權,但以色列的高科技生态系統中似乎沒有人對這些披露感到擔憂。對以色列科技界的許多人來說,NSO隻不過是又一家在這個以軍事間諜技能著稱的行業裡“施展軍事級别的間諜活動”的高科技公司。在特拉維夫,有過軍隊教育訓練背景的IT專家的能力受到全球科技巨頭、新興創業公司和小型網絡間諜公司的追捧。他們所做的工作,包括專業資料分析、網絡安全、數字間諜或多或少都是相同的,隻不過是從軍事領域轉移到了民用領域。不同之處在于這項工作的影響:批評人士指責網絡間諜行業通過讓記者噤聲和壓制政治異見,在全球範圍内大規模助長了侵犯人權的行為。
2021年8月2日,印度新德裡,NSUI活動人士舉着智語牌高喊口号,抗議莫迪政府使用以色列NSO集團的軍事級别間諜軟體“Pegasus”監視政治對手、記者和活動人士。
與許多以色列網絡安全公司一樣,NSO集團也是由8200網絡部隊的校友所創立的。該部隊是負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土監控的精英情報機關。幾十年來,8200部隊的行動一直都是保密的,直到2000至2010年中期,以色列的私營高科技部門登上了全球市場。那是“9·11”事件後監控國家的黎明,以色列的軍事機構正在更新其經常被稱贊的間諜能力,以滿足數字時代的需求。以色列軍方在網絡安全方面投入了數百萬美元,其對巴勒斯坦領土的監視促進了新形式的網絡間諜活動實驗。作為回應,以色列培養了一批IT專家,他們可以将自己的軍隊經驗移用到新興的數字經濟之中。
當時,借用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員丹·塞諾(Dan Senor)和《耶路撒冷郵報》(Jerusalem Post)編輯索爾·辛格(Saul Singer)的發言:以色列正在把自己重塑為一個創新的“創業國家”。 負責網絡安全的初創公司激增,幸運的初創公司很快被在以色列開設分支機構的全球科技集團之一以數百萬美元收購。摩天大樓在特拉維夫市中心拔地而起,它們的開放式樓層設計模仿了矽谷的形象:辦公室裡充斥着豆袋椅、桶裝啤酒和迷你燕麥棒。與灣區一樣,特拉維夫吸引了年輕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科技員工,他們多為男性。但與灣區不同的是,大多數高科技勞動力直接來自以色列國防軍。很少有人能拒絕這樣的機會——把在軍隊裡學到的間諜技術運用到蓬勃發展的私營部門,并以此賺取數百萬美元。
Shoshana Zuboff将這個時代描述為“監控資本主義”的黎明。這是一個全球科技巨頭通過征用使用者的資料,用于廣告和他們自己的分析和程式設計,進而獲得經濟和社會權力的時代。有時,科技公司會與政府分享這些資料,而政府則将國家監控的某些内容外包給谷歌等公司。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企業和國家監控之間的界限幾乎變得難以分辨:科技平台産生了不受監管的使用者行為資料庫,政府經常出于國家安全的目的挖掘這些資料。通過這種方式,谷歌的某些程式員正在做與網絡間諜公司的程式員相同的工作:跟蹤使用者并與出價最高的人分享他們的資料。
國家監視和數字經濟間的重疊,解釋了為什麼許多國家會在軍事和高科技領域之間設定一道轉換行業的“快速旋轉門”。在美國等國家,對這種勾結的内部異議正在增長,至少在名義上是這樣。然而,在以色列,以色列國防軍的戰鬥或技術部隊的榮民占到了高科技勞動力的60%。這些部隊提供了一種滲透到以色列高科技部門的獨特文化:一套共同的價值觀、參照和實踐标準,這些因素在特定的環境中交織在一起。借用現在坐在利潤豐厚的科技公司董事會上的以色列政治家和軍事将領的說法,這種文化是“冒險的”同時也是“積極的,有些人會說它是一種盲目信仰,相信事情都會好起來的”。 正如商業主管和8200部隊校友Inbal Arieli在她的書《厚顔無恥:為什麼以色列是創新和創業的中心》(2019)中所說。這種文化培養了高技能、充滿積極性的工程師和開發人員,使他們能夠投入長時間的工作,高效地解決複雜的問題,并帶領大型團隊執行敏感任務。
如今,這種文化也阻止了許多人去探究自己工作的道德含義。情報部門的榮民渴望獲得六位數的起薪,把在軍隊學到的攻擊性網絡安全技能運用到私營部門。他們不太願意質疑将軍事情報能力外包給出價最高者的道德後果。今年9月初,在特拉維夫的一次采訪中,8200部隊的榮民、網絡安全首席執行官G向我坦言:“我們真的不需要考慮這項工作的道德問題,我們當然不習慣這樣。”“許多老兵受過良好的教育,甚至可以反對占領,但仍然向在剛果或其他地方活動的專制政權出售他們的技能,”人們繼續為NSO這樣的公司工作,G說,因為“他們在22歲時就獲得了巨額薪水。”
情報部門的榮民也不習慣解析網絡間諜活動的混亂倫理。情報部門的服務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擺脫了戰鬥的道德窘境;技術技能被認為比軍事行為在政治上更加中立。事實上,許多情報人員來自以色列社會的富裕和自由階層,他們努力在情報部門工作,以避免執行諸如襲擊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住宅的任務。據我在耶路撒冷喝咖啡時交談過的8200部隊的榮民M表示,情報機構“更像一個專業組織,更像一家初創企業,而不是軍隊。”士兵們享受着一個幹淨、裝備齊全、福利充足的基地:每周放映《權力的遊戲》(Game of Thrones),與營利性行業領袖進行私人課程,定期在特拉維夫的摩天大樓裡進行社交活動。正如M所說,所有這些福利“讓人們更容易感覺‘我不服務于該職業,我隻是為服務于該職業的人編寫代碼’”。
雇傭網絡也會讓年輕的榮民認為,從事網絡間諜工作與從事其他高科技行業沒有什麼不同。例如,那些在8200部隊服役的人通過Facebook上的“校友”頁面建立聯系。我的一個采訪對象允許我浏覽該網站。加入精品監控公司的廣告夾在招募開發約會應用程式和财務管理初創公司的廣告中。這兩種類型的廣告通常都配有這樣的圖檔:20多歲的年輕人穿着相配的公司襯衫,面帶微笑,房間裡堆滿了子產品化的家具。一個“數字身份解決方案組織”需要一個“精通英語/阿拉伯語”,并“對激進的伊斯蘭教有深刻的了解” 的研究分析員。再往下看,一家因侵犯人權而被調查的間諜軟體公司正向那些渴望“異國情調”的畢業生招手,他們的薪水會讓你驚訝(“揉眼睛”)。在這下面,一個移動遊戲應用程式呼籲“有創意的編碼員”加入一個具有“偉大文化和令人難以置信的福利”的公司。
2021年7月21日,塞普勒斯尼科西亞,一名婦女正在檢視以色列制造飛馬間諜軟體的網站。
網絡間諜工作的清單遭到定期張貼,以至于它們看起來很平庸,廣告宣傳的是一種時髦的、高科技的富裕模式,令人向往,但又不出格。實際上,網絡間諜公司與不那麼邪惡的高科技部門提供的生活方式并沒有什麼差別。在特拉維夫,私營化的監控公司就坐落在承載約會應用、遊戲平台和生物醫學成像裝置的辦公樓裡。來自微軟或WAZE的開發人員與來自Black Cube或NSO的開發人員出去喝酒。他們一起讨論職業壓力,工作場所的戲劇性事件,以及戰略性的職業發展。他們每天都在收集個人使用者的資料,或找出作業系統中的纰漏,為客戶生産更好的産品。當然,差別在于産品。
當網絡間諜活動像其他任何高科技服務一樣被常态化時,即使是那些想要遠離該行業的人也會發現自己陷入了私人監控之中。今年9月下旬,當我在耶路撒冷一家路邊酒吧喝酒時,前情報分析師S向我講述了她是如何從軍隊直接加入一家金融科技初創企業的。當時是2019年底,在沙特阿拉伯等政權使用以色列間諜軟體的消息遭到披露之際,她很高興能在一個不那麼陰暗的高科技行業工作。在加入公司時,S希望能把時間花在研究全球金融市場上。相反,她發現自己在為以色列武器集團進行研究,并編輯支援BDS活動人士的檔案。她強調說:“監視工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都夾在正常的全球投資趨勢研究之間。如果你願意,很容易就能忽視一項任務與另一項任務的不同。”
與我交談過的大多數熟悉以色列網絡間諜行業的情報人員都認為,以色列閉塞的高科技領域文化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改變,尤其是随着國際社會對NSO集團的憤怒在媒體上逐漸消失。“壞公司不會停止招募以色列人才,”前開發人員J向我保證,“我認識的大多數人都會繼續被吸引到這項工作中去,因為工作提供的報酬和福利越來越好。從這一點來看,批評有點像背景噪音。”
是以,與其說NSO集團的醜聞指出了一家公司的道德問題,不如說它說明了數字經濟文化的腐朽,這是以色列的問題,也是全世界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醜聞是不可避免的。那些配備和管理以色列高科技公司的人員來自軍隊情報部門;榮民毫不費力地将以國家安全名義進行的監視技能轉移到基本不受監管的私營部門,這些部門也一直在未經群衆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監視。記者、民間社會組織和政界人士聯合起來要求私人監控行業遵守國際人權标準,這可能會帶來變化。但要真正控制這個行業,我們需要確定網絡間諜活動不再僅僅被視為“另一種辦公室工作”。
責任編輯:韓少華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