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這一段傳世的濠梁之辯我們若隻作詭辯解,就有點辜負惠、莊二子的哲學智慧了;它涉及主-客體邊界劃分的重要問題。這一問題在動物行為的研究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二分法有助于建立一個擺脫主體思維的客觀視角,也會因人為劃界構築無益的思維阻隔。它在多大程度上展現着人的一種心理優勢或優越感,我們很難說清楚;它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人們對于動物行為的認識,或阻礙了動物與人的行為一緻性的判斷,也尚沒有清晰的結論。弗朗斯·德瓦爾的《萬智有靈》這本書呈現了動物行為研究的各種方法觀念及價值評判,也許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線索思路,進而擺脫局于一隅的人為設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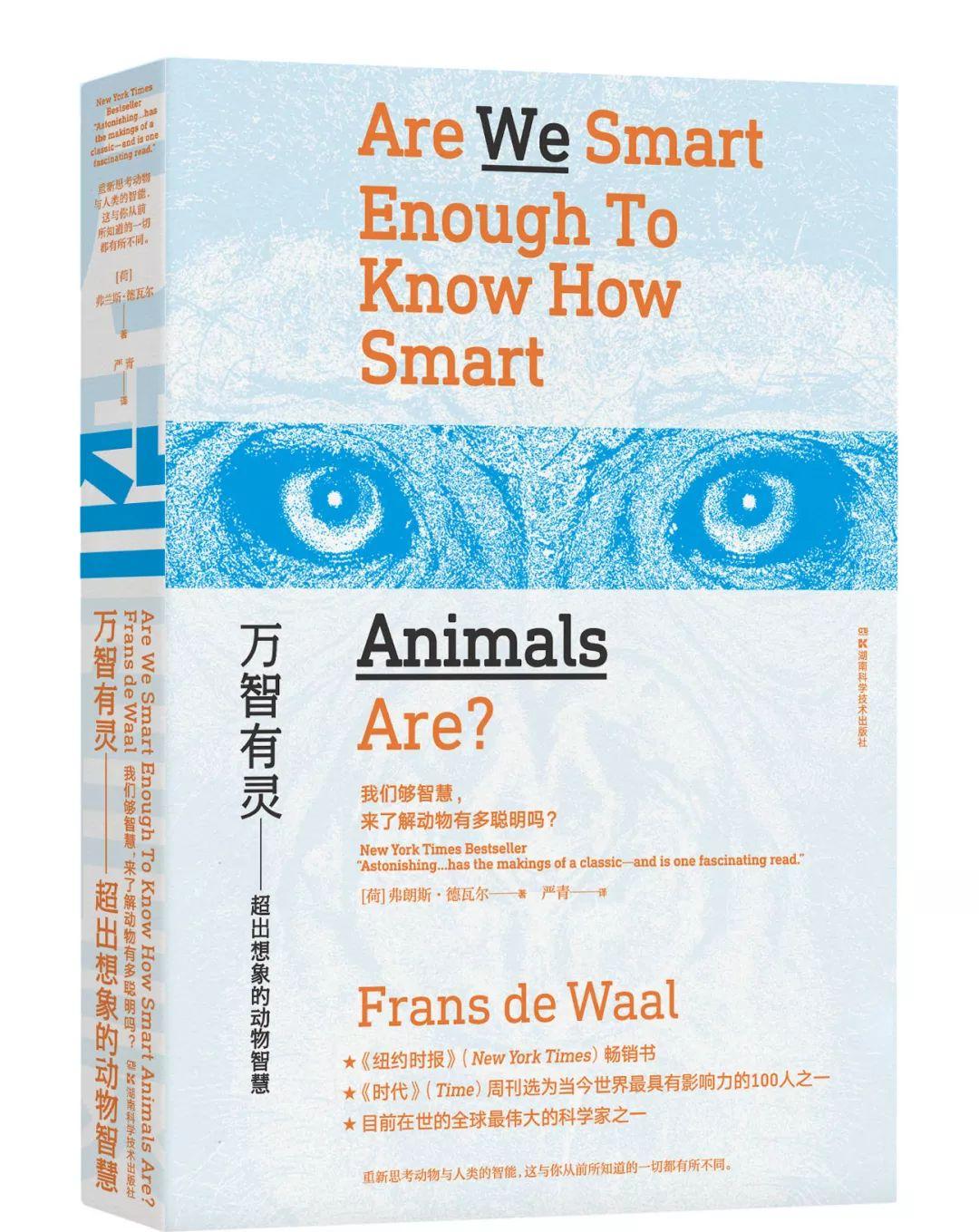
點選“http://product.m.dangdang.com/27949170.html?&unionid=P-115389446m”可購買此書。閱讀本文發表您的感想至微信公衆号的留言區,點選“在看”,截至12月1日中午12點,我們會選出3條留言,每人送書1本。
撰文 | 弗蘭斯·德瓦爾
曾經有一段時間,科學家認為行為的産生要麼是因為學習,要麼是因為生物學原理。他們把人類的行為歸因于學習,動物的行為歸因于生物學原理,而兩者之間的中間地帶則幾乎什麼也沒有。這種二分論是錯誤的(實際上,在所有物種中,行為都是這兩者共同導緻的)。但漸漸地,第三種解釋出現了:認知。認知關乎某個生物收集的資訊的類型以及該生物如何處理和應用這些資訊。比如星鴉能記得它們儲藏了數以千計的堅果,狼蜂在離開自家地洞前會先進行定位飛行,黑猩猩能毫不費力地學會它們所玩耍的東西的可供性。不需要任何獎勵或懲罰,動物就會搜集未來會用到的知識,從如何在春天裡找到堅果,到如何回到自己的地洞,再到如何拿到香蕉。學習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但認知的特别之處在于它将學習放在了合适的位置。學習不過是一件工具,它使動物能夠收集資訊。而世界就像網際網路一樣,資訊多得令人難以置信,使動物很容易溺死在資訊的沼澤中。生物的認知則縮小了資訊流的範圍,使生物學會它所需要知道的特定關聯性。而這些需要則是由該生物的自然史決定的。
許多生物都有相似的認知能力。科學家們的發現越多,我們就能注意到更多的漣漪效應。人們曾認為一些能力是人類所獨有的,或者至少是人科(一個小型的靈長動物科,包括人類和猿類)所獨有的。但最終人們通常會發現這些能力是廣泛存在的。幸虧猿類明顯具有智力,傳統的發現首先是在關于它們的研究中做出的。在猿類打破了人類與動物王國中其他動物之間的堤壩之後,防洪閘便不斷打開,囊括進了一個又一個物種。
造紙胡蜂生活在等級森嚴的小型種群裡。這種等級生活是它們能辨認出每個個體的代價。它們通過面部黑黃相間的斑紋來區分不同的個體。另一種與它們親緣關系非常接近的胡蜂物種沒有如此等級分明的社會生活,也沒有面部識别能力。這表明認知是相當依賴于生态需要的。
認知的漣漪從猿類擴散到了猴子,又擴散到了海豚、大象和狗,然後還有鳥類、爬行動物、魚類,有時還有無脊椎動物。我們不能将這一曆史程序與把人科置于頂端的階梯式看法混為一談。我更願意将這一曆史程序看成一個由可能性構成的池塘,在不斷擴大。在這個池塘中,有些動物,比如章魚,其認知可能和哺乳動物或鳥類的認知一樣令人難以置信。
想想面部識别吧,人們最初認為這是人類獨有的能力。如今,猿類和猴子都已加入了這個“非臉盲上流社會”。每年當我來到位于阿納姆的布格爾動物園時,有些30多年前見過我的黑猩猩依然記得我。它們從人群中認出了我的面孔,興高采烈地尖叫着向我問好。靈長類不僅能辨認面孔,面部對它們而言還有着特殊的意義。就像人類一樣,他們會表現出“倒置效應”:當一張臉倒着放時,它們就辨認不出來了。這種效應是對面部所特有的。一張圖按什麼方向放置并不大會影響它們辨認其他物體,比如植物、鳥類,或者房子。
當我們用觸屏對僧帽猴進行測試時,我們注意到,它們會随意點按各種圖像,但當第一張面孔出現時,它們吓壞了。它們抱緊自己,哀哀嗚咽,不願去觸碰那幅肖像。莫非将手放到臉上會觸犯某種社會禁忌,是以它們對這幅面孔比對其他圖檔更為尊重?當它們從這段猶豫期中恢複過來之後,我們給它們看了一些它們同伴和一些陌生猴子的肖像。對于沒有經驗的人類來說,所有這些肖像看上去都差不多,因為肖像裡的猴子都是同一物種。但猴子們很輕松地把這些肖像區分開了。它們輕輕點選螢幕以告知哪些猴子是它們認識的,哪些是陌生的。我們人類認為自己有面部識别能力是理所當然的,但這些猴子必須将像素組成的二維圖形和真實世界中一個活生生的個體聯系起來,而它們做到了。科學界總結說,面部識别是靈長動物特化的認知技能。但在這一結論的不久之後,第一圈認知的漣漪便到來了:人們發現,烏鴉、綿羊,甚至胡蜂都有着面部識别能力。
面孔對于烏鴉來說意味着什麼尚不可知。在烏鴉的自然生活中,它們有非常多種分辨彼此的方式,比如叫聲、飛行方式、體型大小,等等。是以,面孔并不一定是它們用來辨識不同個體的途徑。但烏鴉的眼睛極尖,是以,它們很有可能注意到辨認人類最容易的方式是通過面孔。洛倫茨記載過烏鴉對特定的人進行騷擾,并且對烏鴉記仇的本領深信不疑。于是每當他要抓住他的寒鴉并把它們拴住時,他都會用特殊服裝把自己僞裝起來(寒鴉和烏鴉同屬鴉科。這個科的鳥類很聰明,還包括松鴉、喜鵲和渡鴉)。西雅圖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野生動物生物學家約翰·馬茲盧夫(John Marzluff)抓捕過許多烏鴉,是以這些鳥兒對他毫無尊重。每當他在周圍轉悠的時候,這些鳥兒就會對他尖叫并“空投”鳥糞,正應了它們的“謀殺”之名譯者注:在英語中,一群烏鴉亦稱為“a murder of crows”,直譯便是“烏鴉的謀殺”。
“我們不知道它們是如何在四萬多個像兩條腿的螞蟻一樣在光秃秃的小徑上匆匆奔走的人中選中我們的。但它們能夠将我們分辨出來。并且,附近的烏鴉在發出一聲在我們聽來充滿厭惡的叫聲後便溜掉了。但這些烏鴉卻不同,它們大搖大擺地走在我們的學生和同僚中間——這些人從未抓捕、測量、拴住,或者以其他方式羞辱過它們。”
馬茲盧夫準備對烏鴉的面部識别能力進行測試。他用的工具是橡膠面具,類似于我們萬聖節時候戴的那種。畢竟,烏鴉也可能是通過體形、頭發或者衣着來辨認特定的人的。但通過面具,你就可以把一個人的“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進而分離出面孔的特定作用。馬茲盧夫的“憤怒的小鳥”實驗包括戴着某張面具抓捕烏鴉,然後讓同僚戴着這張面具或者戴着另一張沒參與抓捕的對照面具走來走去。烏鴉們很容易就記住了抓捕者的面具,并顯然不喜歡這個面具。有趣的是,我們所用的對照面具是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面孔,它在校園裡的學生中引起了比在烏鴉中強烈得多的負面反應。不僅從未被抓捕過的鳥兒能夠辨認出“捕獵者”面具,而且幾年以後它們還會騷擾戴這個面具的人。它們肯定注意到了同伴的憎惡反應,并是以導緻了對于特定人類成員極大的不信任。正如馬茲盧夫解釋的:“幾乎沒有老鷹友好地對待烏鴉,但對于人類,烏鴉則必須按照個體将我們歸類。而它們顯然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
鴉科常常令我們印象深刻,而綿羊則更進了一步——它們能夠記住彼此的面孔。由基思·肯德裡克(Keith Kendrick)上司的英國科學家教綿羊辨認25對綿羊面孔間的差別。對于每對面孔,當綿羊選擇其中某一個時,會得到獎勵;選擇另一個時則沒有獎勵。對我們來說,所有這些面孔看起來都驚人的相似,但綿羊學會并記住了這25個差別,并在長達兩年間一直記得。在綿羊這麼做的時候,它們用到的腦區和神經回路與人類是一樣的,其中有些神經元會對面孔做出特定的反應,但對其他刺激沒有反應。當綿羊看到它們記住的對比圖檔時——它們會對這些圖檔發出叫聲,就好像圖檔中的個體在場一樣——這些神經元便被激活了。科學家們将這項研究成果發表了,其副标題為“綿羊畢竟不太蠢”。我是反對這一标題的,因為我不相信任何動物是愚蠢的。這些研究者将綿羊的面部識别能力與靈長動物的這一能力相提并論,并猜測說,一個羊群在我們看來不過是毫無特點的一大團,但實際上不同的羊是很不一樣的。這也意味着,有時人們會把多個羊群混在一起,而這給綿羊帶來的痛苦可能要多于我們所意識到的。
在把靈長動物沙文主義者弄得如綿羊般局促不安後,科學界用胡蜂進一步推動了研究程序。在美國中西部常見的北方造紙胡蜂有着組織嚴密的社會。該社會有着森嚴的等級,其中蜂後要比所有工蜂的地位都高。由于社會中競争激烈,是以每一隻胡蜂都需要對自己的社會地位一清二楚。第一蜂後會産下大多數卵,其次是第二蜂後,以此類推。在這小小的種群中,種群成員不僅對種群以外的胡蜂頗具攻擊性,對那些面部斑紋被實驗人員改過的種群内雌性也是如此。它們靠着每隻雌性臉上都有的黑黃斑紋分辨彼此,不同個體臉上的斑紋大不一樣。美國科學家邁克爾·希恩(Michael Sheehan)和伊麗莎白·蒂貝茨(Elizabeth Tibbetts)測試了造紙胡蜂中的個體識别,發現造紙胡蜂具有與靈長動物和綿羊一樣的特化能力。造紙胡蜂能在很遠處就辨認出同類的臉,而對于其他視覺刺激則沒有這麼好的辨認能力。有一種和它們親緣關系很近的胡蜂,其一個種群中隻有一個蜂後。這種胡蜂辨識面部的能力大不如造紙胡蜂。這種隻有一個蜂後的胡蜂,其社會中基本沒有什麼等級制度,其不同個體的臉部也更為相似。它們并不需要個體識别。
如果動物王國中這些如此不同的種類都演化出了面部識别能力,那麼你可能會疑惑這些物種的能力是如何彼此聯系的。胡蜂并沒有靈長動物和綿羊那麼大的大腦,它們隻有很小的幾組神經節,是以,它們得以識别面孔的方式肯定與靈長動物和綿羊不同。生物學家一直不厭其煩地強調機制(mechanism)與功能(function)的差别:對于動物來說,通過不同的方式(機制)來達到同樣的作用(功能)是極為常見的。但是,出于對認知的尊重,當人們質疑擁有較大腦部的動物的思維能力,并指出“低等動物”也能做類似的事情時,這種機制與功能的差别有時便遭到了忘卻。懷疑論者很喜歡問:“如果胡蜂也能做到這點,那這又有啥了不起呢?”這種向底部進發的競争曾給過我們經訓練能跳上小盒子的鴿子。
演化學對同源性(兩個物種的性狀來源于它們共同的祖先)和同功性(兩個物種各自獨立地演化出了相似的性狀)作了區分。人類的手和蝙蝠的翅膀是同源的,因為從同樣的胳膊骨骼以及五根指骨可以辨認出來,二者都源自脊椎動物的前肢。另外,昆蟲的翅膀和蝙蝠的翅膀是同功的。它們有着同樣的功能,但有着不同的起源,是趨同演化的結果。
以貶低克勒對黑猩猩做的實驗;還阻礙了對于靈長目以外的動物具有智能的承認,以質疑人類與其他人科動物在頭腦上的連續性。這一切背後潛在的想法是一個線性的認知階梯,以及一種觀點:由于我們很少假設“低等動物”擁有複雜的認知,是以在“高等動物”中做這樣的假設也是不合理的。這就好像要達到某個特定的結果就隻有一種方法一樣!
其實并不是這樣。自然界充滿了反例。一個我親曆的例子便是成對出現的亞馬孫麗魚,亦稱之為鐵餅魚。它們有着與哺乳動物喂奶類似的行為。一旦幼魚吸收完了卵黃中的營養,它們會聚集在父母的身體兩側,啃噬父母身上的黏液。這對成魚會分泌出比平時更多的黏液以哺育幼魚。在大約一個月的時期内,幼魚會一直享受這種營養供應和保護,直到父母給它們“斷奶”——每次它們靠近的時候,父母都會避開。沒有人會用這種魚來說明哺乳動物的哺乳行為有多複雜或者有多簡單,因為很顯然,這種魚的行為和哺乳動物哺乳的機制極為不同,二者間的相似之處不過在于對幼小後代的喂食和養育。在生物學中,機制和功能的關系永遠如陰陽之分:它們互相作用且密不可分,但倘若将它們混為一談,那無疑是極大的錯誤。
要想了解演化是如何在演化樹中施展自己的魔力的,我們通常會用到一對概念:同源性(homology)和同功性(analogy)。同源性指的是來源于同一個祖先的相似性狀。人類的手與蝙蝠的翅膀是同源的,因為二者都來源于其共同祖先的前肢。二者中骨骼的數目完全相同,這便是證據所在。而同功性則不同,它出現在親緣關系很遠的動物各自獨立地向同樣的方向演化的時候,這種演化叫作趨同演化(convergent evolution)。鐵餅魚的親代哺幼行為和哺乳動物的哺乳行為就是同功的,但肯定不是同源的,因為魚類和哺乳動物并沒有任何會哺育後代的共同祖先。另外一個例子是,海豚、魚龍(一種已滅絕的海洋爬行動物)和魚類的外形都非常相似,這是因為它們所處的環境需要流線型的身體和鳍來提供速度和機動性。由于海豚、魚龍和魚類并沒有水生的共同祖先,是以它們的外形是同功的。這種思路也可以用于研究行為。胡蜂與靈長動物對面孔的敏感性是各自獨立演化出來的,是出于辨認群體裡每個夥伴的需要。這種同功性令人歎為觀止。
趨同演化的力量是驚人的。它給蝙蝠和鲸魚都裝上了回聲定位系統,給昆蟲和鳥類都裝上了翅膀,給靈長動物和負鼠都裝上了對生的拇指。趨同演化還讓地理上相隔遙遠的地區産生了相似度驚人的物種,比如犰狳和穿山甲身上都披着硬甲,刺猬和豪豬都用刺自衛,塔斯馬尼亞虎和郊狼所用的捕獵武器非常相似。甚至有一種靈長動物長得很像外星人E.T.,那就是馬拉加西的指狐猴。它們有着極長的中指(用來敲擊木頭,找到空洞并從中挖出蟲子)。這一性狀也存在于新幾内亞(New Guinea)的有袋目哺乳動物長趾紋袋貂身上。這些物種在遺傳上相隔十萬八千裡,但它們卻演化出了同樣的功能。是以,對于在不同紀元、不同大陸的物種身上找到相似的認知和行為性狀,我們并不應該驚訝。正是因為認知漣漪的擴散并不受演化樹的限制,是以它是很常見的——同樣的能力會在幾乎任何需要它的地方出現。這并不像某些人從前所說的那樣是認知演化的反證,反而完全符合演化發生的方式——要麼通過共同祖先的遺傳,要麼通過對相似環境的适應。
特 别 提 示
1. 進入『返樸』微信公衆号底部菜單“精品專欄“,可查閱不同主題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樸』開通了按月檢索文章功能。關注公衆号,回複四位數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擷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類推。
版權說明:歡迎個人轉發,任何形式的媒體或機構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和摘編。轉載授權請在「返樸」微信公衆号内聯系背景。
《返樸》,科學家領航的好科普。國際著名實體學家文小剛與生物學家顔甯共同出任總編輯,與數十位不同領域一流學者組成的編委會一起,與你共同求索。關注《返樸》(微信号:fanpu2019)參與更多讨論。二次轉載或合作請聯系返樸公衆号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