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軍在明朝末年是明帝國的心腹大患,自從薩爾浒之戰努爾哈赤殲滅明軍主力以來,遼東形勢惡化。
明朝自萬曆末年到天啟崇祯年間,為了鎮壓後金之亂,可以說用盡了全力,但是無論明朝派誰去遼東,不管用了什麼辦法,都沒有能夠遏制後金的崛起。
那麼,明朝真的沒有可能壓制後金嗎?實際上是有可能的,有一個人甚至已經算出了一筆細賬,隻要能實作,就可以壓制後金,削平遼東。
這個人就是遼東經略熊廷弼,他提出的政策就是練“十八萬精兵”,每年用軍費三百多萬兩,最終鎮壓後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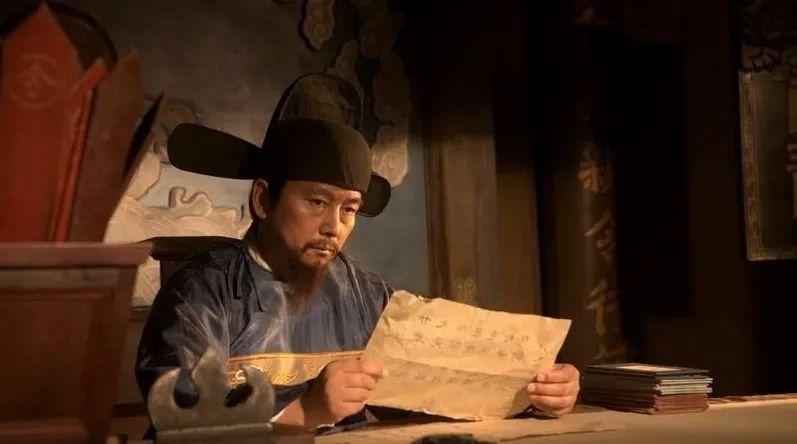
熊廷弼是薩爾浒之戰後的又一任明朝遼東經略,他對于當時滿洲八旗軍強大的野戰能力,和遼東明軍廢弛的軍備有着深刻的認識。
針對明朝在東北地區的弱勢,熊廷弼認為貿然出擊風險太大,被動防禦又捉襟見肘。
想要扭轉局勢,隻有先訓練精兵,穩住陣腳,然後聯合北韓蒙古,通過政治經濟軍事的多重壓力,壓倒後金。
而熊廷弼給明神宗萬曆算的賬是:練出來十八萬精兵,屯駐在雲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等地,再派精銳突擊隊野戰打擊敵軍,最終将後金困死在白山黑水之間。
熊廷弼是懂軍事的,明朝按照他的政策對後金采取圍剿,後金的局面一度很難看,經濟凋敝,人口逃離,八旗軍活得并不輕松。
但是,熊廷弼的政策難以完全貫徹落實。
第一,明朝經濟支撐不起十八萬精兵,明朝在萬曆末年财政情況已經十分嚴峻,大量的皇莊、王爺田宅、免稅的士紳占大部分的良田,卻不負責賦稅徭役,廣大貧民承擔着帝國繁重的賦稅徭役,不堪重負。
而熊廷弼十八萬精兵的開銷,一年至少需要三四百萬兩白銀,當時整個明帝國每年财政收入至多不過五六百萬兩。将國家超過半數的收入全部投入一個區域,這等于将整個國家的血放幹了。
第二,明朝後期的軍事力量已經很衰弱,看似數額龐大的常備軍,兵員大多不足額,将領吃空饷是常态。即便服役的士兵,條件也十分惡劣,遼東士兵甚至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軍隊裝備常年失修,铠甲糜爛,兵器殘破。這樣的軍隊賬面實力再強,也沒有什麼戰鬥力。
熊廷弼要編練精兵,就等于從将領手中将空饷拿回來,遼東遼西的将領不會支援熊廷弼,事實上熊廷弼在編練新軍的過程中就是遇到了這個問題,他處罰了吃空饷的将領,結果是以得罪了朝中要員,後來是以要了他的命。
第三,明朝的“傳統藝能”黨争,在遼東問題上仍舊如此。與熊廷弼配合的王化貞,倆人在對遼政策上有沖突,結果互相掣肘,彼此攻讦,最終釀成廣甯戰役的失敗,此戰的戰敗直接導緻熊廷弼被殺,并被“傳首九邊”。
熊廷弼死後,他的十八萬精兵計劃也擱淺了。
但是,明朝對遼東地區的輸血不但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
因為接替熊廷弼的孫承宗袁崇煥等人,都是“堡壘防禦”派,他們主張修建堡壘城池,步步為營,消耗八旗軍,這項工程開銷之大一點你也不比養兵少,甚至開銷更大。
袁崇煥在任期間,明朝在遼東方向的經費每年要四百萬兩白銀,結果袁崇煥耗費巨資打造的甯錦防線被皇太極繞過,直接打到了北京城下,明朝的“遼東馬奇諾防線”成了廢物。
明朝耗費巨資修建的城堡被一一攻破,城中堆積了大量錢糧成為八旗軍的戰利品,而那些投降滿清的遼東遼西的将領們,很多人家财萬貫,這些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他們吃空饷喝兵血,靠A錢明朝賦稅所得。
而這些賦稅每一兩銀子都是百姓的血汗,最終,遼東這個破裂的大動脈耗盡了明朝最後一滴血,明帝國終于在内憂交困下,轟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