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
</h1>
熊沛軍/文
(肇慶學院 文學院,廣東 肇慶 526061)
摘要:肇慶古稱端州,曾是嶺南政治、經濟、文化重鎮,遺存了大量的各個曆史時期的碑刻,其中以清代最多。這些碑刻大部分采用端硯石材制成。在書法藝術價值上,其尺寸規模大小不一,款形多樣,書體風格豐富。在文獻價值上呈現了肇慶清代各方面的曆史文化,是重要的地方文獻資源。
關鍵詞:肇慶;清代碑刻;書法藝術;文獻價值
肇慶古稱端州,位于廣東省的中西部,曾是嶺南一大郡,據三江之沖、扼五洲之要,屏藩西江上下流,素為嶺南軍事重鎮、西江流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及西江的水運樞紐。宋以後,随着政治經濟中心的南移,中原朝廷開始加強對嶺南地域的開發與控制,是以,中原儒家禮儀文化得以在嶺南地區開枝散葉。到了明清時期,中原朝廷為了平息持續不息的兩廣瑤亂,又在肇慶府治高要縣設立兩廣總督府,故高要縣成為粵西地區政治、軍事、文化重鎮,一度騷人墨客駐留于肇慶,在肇慶地區吟誦會唱、題銘作記,留下了大量的書法藝術及文獻資料,使得今人探索肇慶曆史文化的變遷有迹可循。其中,僅碑刻文獻一項就數量可觀,尤以清代碑刻數量多、價值高。這些碑刻書法藝術價值凸顯,形式多樣,内容豐富。本文僅就肇慶市現存清代的碑刻文獻作一窺探,以就教于方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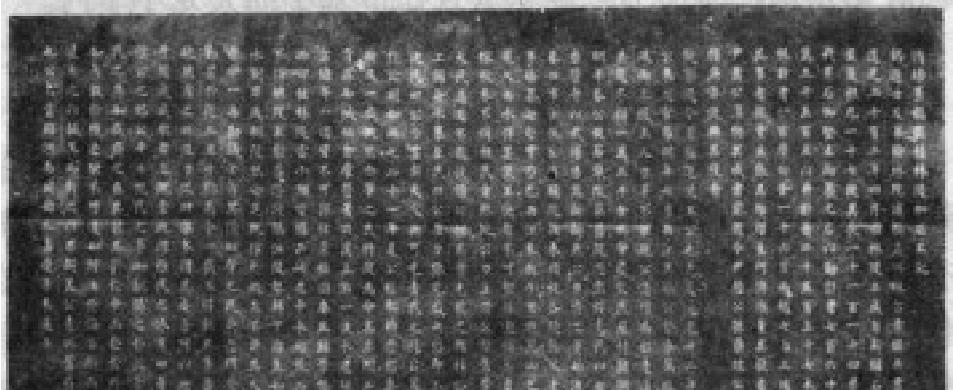
圖1《修培景福圍桂林堤加石工記碑》
<h1 class="pgc-h-arrow-right">一、碑刻遺存現狀</h1>
碑刻作為曆史活動的産物,記載當地曆史内容,是反映當地曆史活動的重要文獻資料。碑刻文獻多為第一手史料,被譽為刻在石頭上的曆史。由于是當時人記當時事,碑刻很少出現像傳世史書因各種影響而誤記、失記史實的情況,是以是更可靠的文獻史料。根據1986年出版的《肇慶星湖石刻全錄》①、1988年出版的《肇慶文物志》[1],以及田野調查整理得出,肇慶市現存清代碑刻約160多件。這些碑刻分布在梅庵、閱江樓、肇慶府學宮遺址、原肇慶府署遺址、五君祠遺址、星湖、鼎湖,以及散存于市郊荒野等。
碑刻一般是用于頌德記事或告示禁忌,是以人們選取的碑刻石材特别講究,一般選取不易侵蝕的、且能就近取材的石材。現存的肇慶清代碑刻,材質主要為端硯石,其次是雲石,還有少部分是花崗岩、青石。
端硯石盛産于古端州,這自然成為肇慶地區人們立碑刻石的首選石材。端硯石的石質細膩、滋潤,石品花紋豐富多彩,易雕刻,蟲蟻不蛀,是極為理想的碑刻石材,能在風雨中屹立數百年。如存放梅庵刻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的《梅庵置香燈田碑記》、原位于盤古廟遺址刻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重修盤古殿題名記碑》、原位于飛鵝廟舊址刻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修培景福圍桂林堤加石工記碑》等,大部分肇慶清代碑刻均為端硯石。端硯石色澤多樣,有紫端、綠端、白端等,尤以紫端普遍名貴,故肇慶清代碑刻大部分用的是紫端硯石,但也有綠端石、青灰端石等,如原放置在市郊小湘大龍國小内、刻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重建聖湖廟碑記序》用的就是綠端石。而原肇慶府署遺址所存的碑刻是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肇慶府禁官差勒索雜貨鋪告示碑》則是青灰色硯石。
原肇慶下轄的雲浮縣盛産雲石,手感平滑、細膩,色淺而質實,不易風化,古人也用于制作碑刻,如刻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的《郭世隆述禦書來曆碑》,用的即是雲石。而比較常見的花崗岩,古人也會用于刻碑,如刻于清光緒九年(1883年)的《陳建侯詩碑》為花崗岩石,三碑并立。但相對于端硯石、雲石,肇慶地區花崗岩的碑刻比較少見。
現遺存的清代碑刻,至今最少已經一百多年,其碑文清晰情況,取決于石碑材質受風化情況。肇慶清代碑刻中,大部分碑刻材質選擇了比較耐風化的端硯石、雲石。從其分布來看,多數碑刻又立在亭台樓閣之中,或者山林村落的大樹之下,免受日曬雨淋,其風化程度不甚嚴重,因而大部分碑刻的碑文至今仍然儲存完整清晰,能夠準确辨讀。如刻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修培景福圍桂林堤加石工記碑》(見圖1),材質是端硯石,此碑原立王雲錦生祠,後祠毀,市民将其放置在市堤圍管理所倉庫(即飛鵝廟舊址),現文物局又将其移至梅庵,是以該碑儲存完好,字迹清晰,可以全部識讀。也有不少碑刻散存于郊野山林,但有樹木遮陽避雨,再加上石材優質、刻工深,其侵蝕亦不嚴重,碑文也基本能夠全部識讀。
有些碑刻盡管選用了端硯石或者雲石這些石材,卻因為碑身長期暴露在外,受到風雨侵蝕,碑面損毀嚴重,導緻碑面極個别或者大面積的字難以辨認,有些碑石字迹甚至不複存在,如刻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的《重建炮台修築城垣披雲樓碑》,此碑原放置于西仁裡,長期受到日曬雨淋,剝蝕甚為嚴重,許多文字已經缺漏不全。有些碑刻的碑面多處風化嚴重,碑文難以識别,雖能根據部分碑文知悉該碑大緻意思,但一些具體内容缺失,導緻碑文内容不完整,如位于七星岩阆風岩含珠洞内的一塊殘碑,刻于康熙七年(1668年),該碑已經被毀壞,字迹難辨,大約隻能識得“高要縣”“下黃崗葉”“桂林都茶灣接前……”等字樣。有些碑刻可能受到人為的破壞,也已經破碎不全,如《慶雲寺浮圖碑記》,此碑刻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現存鼎湖山慶雲寺,已斷裂成數段。此類殘損不全的碑刻因缺乏完整性,其史料價值也受到較大影響,實則是地方曆史文化研究的一大遺憾。有些碑刻因受到人為或戰争的原因,甚至已經不複存在,隻能在地方文獻中見其相關的記載,如現位于閱江樓的五塊《康熙禦書碑》,系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汾州的郭世隆任兩廣總督,在閱江樓側崧台驿建禦書碑,把他與其父郭洪臣所得康熙手迹摹勒石上,原本有六塊,現存五塊。實因抗日戰争時期,閱江樓屢為日機襲擊,崇文閣所置禦制碑被累及,其中一塊毀于斷瓦殘垣之中,其它五塊亦有殘損之處。
總體而言,現存肇慶清代碑刻,幾乎都有受到不同程度毀損,但基本上還能完整識讀,風化極為嚴重、内容模糊不清的極少,而且許多有價值的碑刻已經得到文博部門的監管與保護。
圖2《康熙禦書碑》
<h1 class="pgc-h-arrow-right">二、碑刻的藝術價值</h1>
肇慶清代碑刻外形的藝術特征,因為刻碑人或記事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差別。下面從碑刻尺寸、碑刻的款形和碑刻的書體藝術風格三個方面來論述碑刻的藝術價值。
1.碑刻尺寸。從尺寸方面來說,官方修繕的重要寺廟殿堂、堤圍樓閣和禁忌告示碑,一般高大雄偉,其高約150厘米左右,寬約60厘米,顯示官方造福地方、官威權正。如原放置在盤古廟遺址、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的《重修盤古殿題名記碑》,碑高180厘米,寬100厘米;存于梅庵的刻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重修梅庵碑記》,高180厘米,寬80厘米;原在原肇慶市第一人民醫院内、刻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官吏常捐基圍經費碑記》,高180厘米,寬86厘米。
而位于鼎湖山慶雲寺後山栖壑和尚墳前、刻于順治十七年(1660年)的《栖壑禅師塔銘》,是為慶雲寺第一代住持栖壑和尚所立之碑。慶雲寺原名蓮花庵,始建于崇祯六年(1633年),後栖壑應邀在蓮花庵開山主法,将蓮花庵擴建為慶雲寺,慶雲寺自此聲名大振,位列廣東四大名刹之一,是以栖壑和尚之弘揚佛法與擴建慶雲寺,可以說是功德無量,後人為他所立的《栖壑禅師塔銘》碑,甚至高達240厘米,寬達120厘米,是現存肇慶清代佛事碑刻中最雄偉的一件。另外,前述閱江樓的現存五塊《康熙禦書碑》(見圖2),系兩廣總督郭世隆,因感蒙皇恩,在古崧台驿勒石樹碑,五碑高222厘米,寬110厘米,都是雙龍頂額,雲紋鑲邊,下有雕龍基座。其氣勢宏偉,藝術性非一般碑刻所能及。
而一些無涉官方、重大事件或人物,僅事關捐贈、修寺廟等地方事務所立碑刻,其尺寸規格一般較小,如刻于清嘉慶二十年(1815年)的《知感堂小引》,記載肇衆親捐金重修城西清真寺,碑高僅52厘米,寬僅71厘米。積善堂刻于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立永遠送屋入寺碑》,記載的是積善堂自願将其所買的房屋一間永遠贈送“□西寺”一事,其碑高僅32厘米,寬僅48厘米。
2.碑刻款形。碑的款形一般可由碑首、碑身和碑座幾個部分組成。碑的最上端稱為“碑首”或“碑頭”,碑首的正中部分是碑額,用來書刻碑題,一般稱為“額題”。碑額題字有提綱挈領的作用,看到碑額就基本上能知道是什麼類型,或者表達什麼主觀願望的碑刻。現存肇慶清代碑刻有碑額的不多,均是從右往左橫刻,陰文,其字号大于正文的字号,字型有篆書、隸書、楷書,如《重修梅庵碑記》刻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碑額篆書;《重修佛殿碑記》刻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碑額隸書;《梅庵置香燈田碑記》,刻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碑額楷書。碑首形狀有平首形、尖首形和圓首形三種,其中尖首碑也稱“圭首碑”。
碑額之下為碑身,碑身是碑刻的主體部分,碑身的正面一般會被人工磨平,刻上正文,稱“碑面”或“碑陽”,“碑面”的反面叫“碑陰”,碑的兩邊叫“碑側”[2]。“碑面”或“碑陽”的文字就是碑刻的内容,其文字的字型也會多樣形式,肇慶清代所刻碑刻的正文字型一般多用隸書、楷書、行書、草書,尤以楷書和行書最多。如存于梅庵的《重修盤古殿題名記碑》,此碑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碑額“重修盤古殿題名記”為篆書,正文楷書;《重建聖湖廟碑記序》,此碑刻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無碑額,正文行書,碑側有雲紋花邊。原在原肇慶市人民醫院内、現儲存于梅庵的《官吏常捐基圍經費碑記》,此碑刻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無碑額,正文楷書,碑面的反面碑陰有《楊霈詩碑》,道光二十年授肇慶知府楊霈撰文并書,字型為行書。
首題是碑刻第一行起标題、總領作用的銘刻文字,镌刻在碑面最右側,豎直順寫而下。一般有碑額的碑刻就沒有首題,無碑額則有首題,如刻于清道光二年(1822年)《建立長赓書塾碑》,沒有碑額,但有首題“建立長赓書塾碑”,類似這種沒有碑額的碑比較多見,可能因為碑額的制作工藝複雜,費用比較高,是以除了官方重大記事會有碑額,一般的碑記就直接采用首題形式。但也有部分碑刻既有碑額又有首題,如慶雲寺後山右側順治十七年刻(1660)的《鼎湖山栖壑禅師塔銘并序》,碑額書寫“淨禅總持”,又首行題“鼎湖山栖壑禅師塔銘并序”。有些碑刻既沒有碑額也沒有首題,如白雲寺右側小山路右側的、刻于同治七年的(1868)《植寬延公之塔碑》,這類碑刻也比較少。
碑身下方起承載作用的石基叫做“碑趺”,俗稱“碑座”。如《康熙禦制碑》下有雕龍基座。而《重修閱江樓詩碑》《端江雜詠詩碑》等也有碑座。但現存清代碑刻有碑座的并不多見。
3.碑刻的書體風格。肇慶清代碑刻書體多為楷書和行書,其風格豐富多樣,相容并收。
肇慶清代的楷書碑刻法度嚴謹,多為唐楷筆法。其碑刻多為藏鋒起筆,中鋒行筆,提、按、頓、挫明顯,轉折方圓兼顧;用筆圓潤而不失力度,間架結構沉穩,結體緊湊,方正嚴謹,清秀溫潤,令人賞心悅目。此類碑刻有如位于梅庵刻于明萬曆十二年(1584年)的《梅庵舍田記》(見圖3),其字形豐腴跌宕、運筆輕松自如,其書寫清晰端麗,頗有褚遂良楷書的風格。而位于仙女湖的《迎仙平寇碑》則字迹清晰雅緻,多有歐陽詢楷書特色。
而行書碑刻主要有兩種風格:一種則繼承了魏晉時期的流暢飄逸之筆意,如《重修肇慶府梅庵碑記》(見圖4)、《石峒廟記略》等,此類碑刻有魏晉以來風格;一種渾厚有力且多具圓潤之姿,如《平嶺西紀略》《在犙和尚禁伐樹木碑》等,富有唐人豐腴雄渾之氣象。兩種風格的碑刻,雖然藝術特點有所不同,但其用筆技法并無二緻。行書碑刻書法多露鋒起筆,筆鋒淩厲,中側鋒并用,寓方于圓或寓圓于方;結構緊湊,雖形體取斜勢,但重心穩健;行筆流暢靈動,筆斷而意不斷;章法氣韻貫通,疏密有緻,氣象雄俊。
值得一提的是,前文所述《康熙禦書碑》的書法藝術厚重雄渾,有帝王之氣。該碑刻勒了康熙的詩作及其臨米芾、董其昌的書迹。康熙自幼酷愛書法,尤喜臨米芾、董其昌書法,擅長楷書、行書,其書法風格厚重灑脫。據考證,康熙所臨米芾的《淨名齋》和《闾門舟中戲作》均不見于曆代文獻,系米芾佚作。是以《康熙禦書碑》展現的兩大書家之書迹,作為遺存實物,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史料價值,能補文獻之遺缺,實乃碑刻之珍品。
另外,原位于肇慶府署遺址的《福字碑》也有獨到的書法特色。此碑刻于清鹹豐七年(1857年),碑高161厘米,寬90厘米,紫端硯石,屬殘碑。“福”字凸雕,題款行書凹雕,此碑大“福”字,由雀、鹿、龜、田四種意象組合而成。據碑前題,系陳抟所書。陳抟,字圖南,自号扶搖子,系五代宋初道士,亳州真源(今河南省鹿邑縣)人;生于唐末,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隐居華山。陳抟沒有到過肇慶,此“福”字系清代人摹刻的。此碑在書法、雕刻方面都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總體上看,肇慶清代碑刻規模大小不一,形制多樣,其中,以皇帝禦制碑與佛事人物碑記的規格較高,這反映了清代肇慶地區佛事興盛的狀況。而此類有碑額、碑座的碑刻并不多見,多數碑刻僅是制作簡單的碑身。碑刻的碑首書寫字型有篆書、隸書、楷書、草書等,而正文書寫字型多為楷書和行書,其風格豐富多樣。
圖3《梅庵舍田記》
<h1 class="pgc-h-arrow-right">三、碑刻的文獻價值</h1>
肇慶清代碑刻不僅在書法藝術上價值頗高,其文獻價值亦極為豐富。其豐富的内容幾乎涵蓋了肇慶地區曆史文化的各個方面,諸如官府告示、學校教育、寺觀廟宇類、祠堂宗族類、地方公益事業記事、刻詩題名、塔銘墓志等。
1.官府禁令告示碑。禁令告示碑是地方官府為矯正地方弊端問題而立的,通過告示向鄉村社會傳達國家的各項政策,表達官方的基本态度。是以刻石申明禁令,是明清地方禁令的重要表現形式[3],主要包括地方官府的示禁、褒獎、布告、判案等,此類碑刻已收集有13件。清初,肇慶為南明王朝的主要根據地,也是清廷與南明勢力的主戰區之一,其兵禍連綿近三十載,至康熙十一年,清王朝始收複肇慶地區。經過明末清初戰亂的肇慶,社會凋敝,民生凄苦,是以至清初,中央王朝在肇慶地區,一面設屯田兵,兵民結合,防“匪患”,促軍墾;一面采取鼓勵墾荒、保護工商、輕徭薄賦、加強赈災、興修水利等惠民政策,以促進肇慶經濟的繁榮。為了加強對地方民商的保護,官方釋出了一系列的告示,并勒石永禁。如刻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磁器鐵鍋缸瓦鋪永禁碑記》,釋出“不得藉有公務簽差,擅向鋪戶借取租賃,緻滋擾累”的告示;刻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奉督憲嚴禁簽取各行什物碑記》記載,因高要縣磚窯、瓦窯、燈籠、錫器等各行業商民,反應“各衙門所用什物,複行簽取,胥役家人不免藉端滋擾”,于是官府釋出“各衙門所用各行什物,俱照時價現銀置買,不得藉有公務簽差,擅向鋪戶借取”,也不得藉有公務簽差,“擅向鋪戶借取租賃及恃勢短價壓買”的禁約;刻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肇慶府禁封江勒索碑》,是官府嚴禁官差借賒欠、封江等名義勒索商戶和商船的告示。這些告示展現了清初政府的“恤商”政策。而乾隆元年(1736年),時任高要縣知縣顧彜所刻《魚埗歸疍民資生告示碑》,則記載了官府治理高要縣疍民的情況,這對研究當地疍民是不可或缺的文獻。
在這些禁令碑刻中,“勒石永禁”“勒碑示禁”“禁令永垂”是碑刻中常見的标志性詞語,出現的頻率也較高。其内容與國家政策一緻,往往具有法律的效力,也是肇慶官員治理地方的重要舉措。
2.學校教育碑。明清時期,兩廣總督府駐于肇慶,曆任總督大吏以及知府縣令都倡修學宮、書院,是以關于發展儒學與修建書院的碑刻非常多。原肇慶府學宮存碑就有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立《重建肇慶府儒學碑記》、乾隆十年(1745年)立《置田修學宮碑》、道光十二年(1832年)立《重修肇慶府學宮記碑》,這些碑記記述了清代不同時期高要學宮的修繕情況。
還有些碑刻是關于肇慶各村鄉民集資辦學,如祿步鎮之東有祿步文社,建于清嘉慶丁卯年(1807年)間,落成于辛未(1811)年,又稱“祿溪社學”,文社遺址有道光二十年(1840年)才補遺刻石立記的《祿步文社碑記》,載:文社為裡人監生鐘永魁、恩職陳嘉韶、監生陸逢源等人,熱心為地方培育人才,發動祿步全境村民、殷戶捐款建成。而龍崗村東的小山崗上,有五雲書院,始建于清朝乾隆甲辰年(1784年),書院大門後面的牆角側,鑲嵌着一塊由地方學者彭泰來撰寫的《五雲書院碑記》,記述了五雲書院修建的經過。在高要市南岸鎮山口村北側有十八坊書院,始建于清光緒六年(1880年),廣塘何鳳飛撰文的《十八坊書院記》刻碑鑲嵌在書院右襯祠内,1992年兩襯祠被拆除時,将該碑改嵌在正間天井左廊的左外牆上,至今儲存完好。碑記記載了諸鄉父老倡議集資建學的過程。為了鼓勵衆子弟好學向上,書院還制訂了《十八坊書院規條》,并刻石立碑于書院中,以策勵教師勤教,學生勤學,培育坊中英賢。此類碑刻還有刻于清道光二年(1822年)的《建立長赓書塾碑》。這些碑刻為我們研究當地教育狀況提供了最直接的史料。
3.寺觀廟宇類。此類碑刻是現發現清代碑刻中最多的一項。包括寺廟宮觀以及民間信仰等。自古嶺南地區就巫風盛行,對鬼怪神靈崇拜不斷,到了唐代以後,肇慶地區又佛教盛行,不僅出了禅宗六祖惠能大師,風景優美的鼎湖山的慶雲寺也是嶺南四大名刹之一,是以祭拜神靈、供奉香火的廟宇比比皆是。目前,發現肇慶清代碑刻中涉及的廟宇有梅庵、盤古殿、聖湖廟、朝龍祖廟、白雲寺、慶雲寺、石峒神廟、星岩大覺寺、象崗廟、清真寺等。與這些廟宇相關的碑刻,記錄了這些寺觀廟宇的修建過程、置産、寺廟管理以及捐贈者的姓名。此外,清代鼎湖山慶雲寺僧衆與周邊村落沖突重重,為了保護鼎湖山林木,禁止周邊村民上山伐木,分别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刻《在犙和尚禁伐樹木碑》,乾隆八年(1743年)刻《僧衆護山碑》,光緒十九年(1893年)刻《禁伐鼎湖林木碑》等。這些碑至今都儲存在慶雲寺中,為我們探究肇慶地區的僧衆生活與地方社會狀況提供了一個視窗,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
4.祠堂宗族類。明中葉後,随着正統禮儀文化在嶺南地區的擴張,地方士紳紛紛以修建家廟祠堂來顯示其正統的身份,強化他們在鄉村中的權力,并在基層社會的管理中發揮着重要作用[4]。是以在肇慶的城鄉聚落中也留存了衆多不同時期的宗族祠堂,如刻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的《重修小宗祠碑記》,現在黃崗鎮河旁村覃氏宗祠内,該碑記錄了五世之祖文右公重修覃氏宗祠的過程。高要金渡劉氏祠堂的《劉氏祠堂記》,記載其先祖劉貴祥,遷入廣東肇慶岩前村,為開族始祖;後世子孫,分支各村定居,繁衍生息,後又遷入高要金渡大坑村定居的曆史過程。雍正九年(1731年)的《東禺村梁氏族規碑記》、乾隆三年(1738年)的《西庵祖垂訓碑志》、嘉慶三年(1798年)的《添立紅白銀碑志》等則是這些宗族将家規條例、族産配置設定、懲戒賞罰等勒石,以訓誨後世子孫,為我們提供了研究基層社會活動和社會組織的曆史資料。
5.刻詩題名碑。明清時期,肇慶作為兩廣總督府所在地,外加鼎湖山、七星岩名勝寶地,往來文人絡繹不絕,在肇慶留下了許多文賦詩詞,為我們留下了一份珍貴的遺産。1784年秋,浙江錢塘著名詩人袁枚(1716—1797年)因其弟任肇慶知府,來遊鼎湖,期間創作了大量的詩作,并請人刻于碑石之上,名為《袁枚遊鼎湖詩碑》,現存鼎湖山慶雲寺,嵌于客堂壁上。該碑藝術價值較高。福建省福州人陳建侯,曆任知府于安陸、漢陽、德安、武昌,光緒六年(1880年)以服喪辭官,後南遊各地,光緒九年(1883年)曾遊肇慶,留有《陳建侯詩碑》。還有《端江雜詠詩碑》,此碑刻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詩作者宋廣業,字澄溪,江蘇長洲(今吳縣)人,年老辭官到端州,其時他的兒子宋志益(字端齋)在肇慶當太守。宋廣業曾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作《梅花百詠》詩,命工匠镌石于端州府署梅花書屋壁間,該詩碑現存慶雲寺。另有《蘭臯詩抄》及《羅浮山志》傳世。詩後題跋作者鄭際泰,首創鼎湖十景詩,曾為《鼎湖山志》寫序。詩中提到的迹删方丈,即慶雲寺七代住持成鹫迹删和尚,曾主編《鼎湖山志》。
6.其它。包括地方公益記事、墓志塔銘等。公益事業活動紀念碑,是地方官府為了紀念個人或者衆人為地方公益事業作出的貢獻所立的碑,地方公益事業如興水利、建路橋,如刻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的《重修周塘橋大路記碑》記載,肇慶府縣官員捐俸修築城西周塘一路的事迹。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立的《修培景福圍桂林堤加石工記碑》,共四塊碑,記述了景福圍桂林堤修堤的原因及經過,極力贊頌肇羅道王雲錦修堤的功績。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官吏常捐基圍經費碑記》,記載肇慶知府楊霈,因景福圍基基身低薄,每遇西江盛漲,即欲沖決,是以商議集資捐款修築圍基基柱,并附刻捐築基柱章程。光緒十四年(1888年)的《重建禹門坊馬頭街道碑記》記述城東禹門坊舊有馬頭基址,每遇積雨餘濘之天,泥侵屐齒,行人不堪其苦,于是裡人捐資修築街道。而墓志塔銘在内的人物類碑刻真實而詳盡地記錄了清代肇慶地區各個階級和階層人物的活動,是研究肇慶地區人物的極為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墓志銘中既有封建朝廷官員,也有地方士紳、節婦等墓志銘,如位于鼎湖白雲寺右側小山路、刻于乾隆八年(1743)的《梁門黃氏始祖妣墓碑》,刻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淡凡和尚墓碑》。塔銘是佛教僧尼的墓志,或嵌于塔上,或置于塔内,其文體、内容、埋設目的與墓志相近。現存塔銘有刻于清順治十七年(1660年)的《栖壑禅師塔銘》,刻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石箭禅師塔銘》等。
綜上所述,清代肇慶碑刻的書法藝術形态多樣,文獻價值豐富,為我們展示了肇慶曆史上的興廢和政令、禁約、曆史事件,名人事迹、學制,水利、交通、民情風俗、自然災害以及書法、雕刻藝術等,既有很高的書法藝術價值,又是一部非書本能永久儲存的文獻史料,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圖4《重修肇慶府梅庵碑記》
參考文獻:
[1]肇慶市文物志編纂委員會.肇慶文物志[M].廣州:廣東新聞出版局,1988:66.
[2]毛遠明.碑刻文獻學通論[M].北京:中華書局,2009:256.
[3]李雪梅.法制“镂之金石”傳統與明清碑禁體系[M].北京:中華書局,2015:59.
[4]科大衛.禮儀與地方社會[M].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123-128.
(原載于《肇慶學院學報》 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