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一個熱搜,讓魚叔心頭一緊——
#全球五分之一的人聽力受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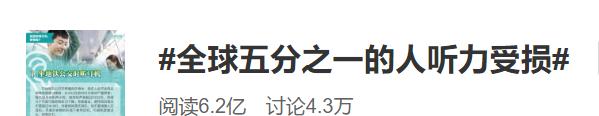
也就是近15億人。
其中4.3億人有中度或以上程度的聽力損失。
魚叔隐隐感覺自己也屬于這五分之一,吓得趕緊調低耳機音量。
越來越嘈雜的環境,無處不在的噪音,耳機長期高音量。
這些都是聽力受損的元兇。
更可怕的是,聽力的損傷是不可逆的,甚至可能導緻失聰。
今天要介紹的電影,就拍出了後天失聰的「無聲之痛」——
《金屬之聲》
Sound of Metal
《金屬之聲》獲得了今年奧斯卡的6項提名。
包括「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這樣的大獎。
口碑也很不錯,爛番茄新鮮度高達97%。
本片是英國演員裡茲·阿邁德的獨角戲。
他曾憑借美劇《罪夜之奔》,獲得過「艾美獎視帝」。
此次飾演一位突然失聰的鼓手魯本。
他有着一雙深邃的大眼睛,輪廓分明的修長臉型,能夠表達複雜的情感。
《金屬之聲》中的角色簡直為他量身定制——少言語,重表情。
裡茲·阿邁德把握住機會,貢獻了生涯最佳表演。
獲得了一衆奧斯卡前哨站的影帝提名。
雖然不是呼聲最高的大熱選手,但入圍已是一種肯定。
如果最終爆冷拿下「奧斯卡影帝」,魚叔也不意外。
魯本和女友露易絲組了一支雙人樂隊。
音樂風格偏向噪音實驗,現場聲浪特别大,震耳欲聾。
有一天,魯本突然感到一陣強烈的耳鳴。
緊接着他發現自己聽不見任何聲音,耳朵裡隻剩「嗡嗡」的低沉回響。
他嘗試用各種方法恢複聽力。
比如捏住鼻子呼氣,用手去掏耳洞,不停地張嘴閉嘴。
顯然,所有方法都無濟于事。
他來到醫院檢查,被告知:「你的聽力隻剩下兩成。」
并且受損的部分難以恢複,目前所能做的,就是保護好僅存的兩成聽力。
可想而知,對于一個搞音樂的人,這個消息無疑是晴天霹靂。
唯一的補救措施,是植入人工耳蝸。
但費用在4萬-8萬美元之間,魯本負擔不起。
突如其來的變故,深刻改變了魯本的生活。
他不僅無法繼續玩音樂,連和人的正常交流都極其困難。
露易絲得知魯本的情況,立刻終止了接下去的巡演。
現在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幫助魯本去适應幾近失聰的狀态。
更要防止他的毒瘾因為此事再犯。
經人介紹,露易絲帶着魯本來到一個位于郊區的「失聰人士社群」。
這是專門幫助失聰人士的公益社群,魯本可以在這裡學會基本的溝通技能。
他學到的第一課就是:
「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是思想層面的問題,而不是聽力。」
相比生理上的障礙,更需要克服的,是心理上的認知障礙。
最初肯定是不适應的。
魯本不會手語,也看不懂其他人在比劃什麼。
就算在飯桌上,大家也在用手語熱烈地交流。
隻留魯本在一旁默默吃東西。
白天和大家在一起時,魯本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緒。
可一旦夜幕降臨,就會被自怨自艾的沮喪所淹沒。
魯本試着和大家打成一片。
他開始教這裡的孩子打鼓,很招大家歡迎。
他學習手語的速度很快,偶爾還會和孩子一起比賽,用手語拼出26個英文字母。
輸了一局還不服氣,非要再比一局赢回來。
在飯桌上他也加入了讨論,與初次吃飯時的拘謹和孤獨截然不同。
電影在這裡用了一組巧妙的平行關系,來呼應魯前後的心理變化。
魯本第一次走進房間,剛一坐下就崩潰了。
憤怒地用拳頭把面包敲碎。
揉成一團後繼續敲碎。
然後失控地大笑,自言自語說着胡話。
第二次進入房間,他自然地拿起面包,然後在紙上塗塗寫寫。
等到第三次進入房間,他已經可以心平氣和地坐下來思考。
三次進入房間,情緒層層遞進。
裡茲·阿邁德幾乎全憑表情和肢體語言,完成了對現實從抵觸到默許再到接納的過程。
他的眼神既捕捉到了日常的脆弱,又閃爍着對新生活的向往,非常考驗演技。
鑒于魯本表現良好,創始人決定為他提供一個繼續留在社群生活的機會。
可這番話,瞬間把魯本從社群的美好時光一把拽回到現實中。
對魯本而言,「未來」是個分外紮心的詞。
一想到未來,魯本留下來的決心便動搖了。
因為他還是想恢複聽力,繼續玩音樂,不願一輩子留在社群。
是以,魯本做了一回「叛徒」,離開了。
他瞞着喬變賣家産,湊錢去醫院接受了心心念念的耳蝸移植手術。
手術完成後,才回到社群把離開的原因告訴創始人:
「我覺得我是時候該做點實事,努力拯救我這操蛋的人生。這就是我這麼做的理由。」
言外之意,留在社群得不到救贖,也算不上實事。
這番話傷透了創始人的心,他對魯本說:
「這個地方永遠不會抛棄你,是你抛棄了這個地方。」
然後便把魯本趕出了社群。
因為這個社群不僅僅隻是把失聰人士聚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把大家的心連在一起,分享相同的理念和信仰。
而魯本的所作所為,等于否定了這個社群的意義和價值。
他背叛了社群,這正是創始人所無法容忍的。
被趕出社群的魯本,很快将迎來第二次幻滅。
新植入的耳蝸被激活了,他滿懷期待,以為可以回到以前的狀态。
可事實卻令他失望。
雖然可以再次「聽見」外界的聲音。
但聲音經過人工耳蝸的轉化,被扭曲成刺耳而尖銳的金屬聲音。
此時終于點到了電影的名字:金屬之聲。
這些聲音和魯本原有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他在努力适應這種聲音。
同時思索着這樣的金屬之聲到底有沒有意義。
誠然,它可以幫助魯本聽清别人說的話,完成正常的溝通。
可然後呢?
風聲、雨聲、哭笑聲、汽笛聲、海浪聲…
人世間一切美好的聲音,都成了冷冰冰的金屬之聲。
這裡就不得不提到本片的聲音設計,絕對是一個亮點。
在不斷變化的人物視角中,聲音也在不斷變化。
當畫面切換至魯本的第一視角時,聲音也跟着來到魯本的世界。
時而是低沉的噪音,就像身處深海,時而是完全無聲。
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音效總監尼古拉斯·貝克爾。
他曾操刀過《地心引力》《降臨》等科幻大片的音效。
此次憑借《金屬之聲》再獲得奧斯卡「最佳音響獎」提名
當然,靠的不是刺激感官的炸裂音效,而是巧妙的變換。
時刻在利用聲音調動觀衆的情緒。
聲音,仿佛成了電影的第二主角。
在露易絲的家庭聚會上,魯本聽她唱起一首從未聽過的法語歌。
在場的每個人都陶醉其中。
唯獨魯本是個例外。
他流淚了。
但不是被露易絲的歌聲打動。
而是因為,動人的嗓音和琴音,傳至耳朵都變成了同一種聲音。
更令人難過的是,長此以往,記憶中聲音帶來的美好與感動,也都會漸漸被這樣的金屬之聲所取代。
想到這些,魯本破防了。
電影結尾,魯本做出一個大膽的決定——
他摘掉了耳蝸的體外機。
瞬間,整個世界都安靜了。
沒有了金屬聲,他再次擁有了無限的想象。
足以調動起所有關于聲音的回憶,填補無聲的缺憾。
兜兜轉轉一大圈,魯本終于想明白:比失聰更煎熬的,是失去感覺聲音的能力。
後天失聰的魯本,一路上面臨了許多選擇時刻:
選擇留在社群,還是選擇接受手術回歸社會;
選擇手語,還是選擇金屬之聲。
手語雖然無聲,卻飽含情感與溫度。
人工耳蝸雖能帶來聲音,可卻是冰冷尖銳的金屬之聲。
這樣的兩面性就像魯本身上的紋身:
他的胸前紋着「請殺死我」,手指上紋着「活着」,可見魯本自身就是一個沖突綜合體。
他一直在做錯誤的選擇,等到付出慘痛代價才知後悔。
通過魯本最後的選擇,電影想要告訴我們:
不要等到失去後,才懂得珍惜。
這個道理看似簡單,卻往往容易被人忽視。
就像魯本,當初沉浸在他的音樂世界時,從未想過噪音會對聽力造成怎樣的傷害。
等到被醫生告知情況不妙,他再想去補救也無力回天。
做完人工耳蝸手術後也是如此。
當魯本被金屬之聲淹沒之時,他才意識到這世界上自然存在的每一種聲音,都何其美好。
好在,他最後成功與自己達成了和解。
利用記憶、感覺、想象力,将腦海中的聲音永久儲存。
正如《東邪西毒》裡的那句話:
「當你不能夠再擁有的時候,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