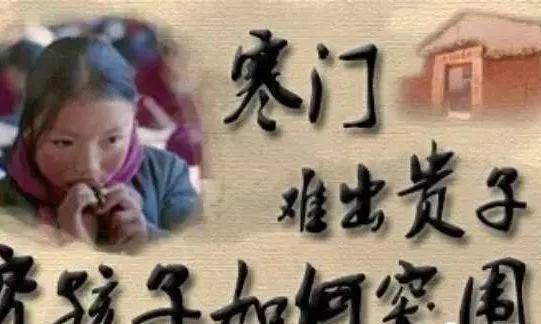
大學就是“營盤”,學生是“流水的兵”。今年的高校新生報到,校園依舊又擁擠喧鬧了幾天,随處能見到東張西望的年輕人,後面緊随着手拉肩扛的父母。就我調查,能百裡千裡送孩子來我所在這偏遠的海島學校報到的,在八千多新生中不足三分之一。
更多不可能來的是在田裡的農民或在各城市角落裡的農民工,他們可不敢随意離開工作崗位一步,農民工家庭多數不隻一個孩子,如果停了工,他家裡交不上學費的很可能不隻一個學生。
網上常見誇張的奴仆般的父母給潇灑時尚子女拖背行李的貼圖,招來罵聲,在這所普通高校裡,我沒親眼見到。就在秋季開學前的7月底,我在東北長白山區露水河鎮林業局飯店住過兩天,中午晚上兩個“飯點”,餐廳裡很多人面有喜氣,魚貫而入兩小時,又魚貫而出,人人都喝得臉上紅通通的,餐廳因忙不過來不對外開放。飯店的人說每年這時候都連天辦“謝師宴”。
我問:都是哪的?回答:都是這街上的。我問:農村考上的呢?回答:下邊?下邊的就啥也别說了。我再問:畢業後有回來的?回答:費多大勁考上,還回來?回這癟地方?夜裡,當地電視台播一個節目叫“金榜題名”,學生的大頭照片配在大紅底上,每人停留幾秒鐘,下面列出考中的學校名稱,一個接一個輪番不止。
一轉眼,從“謝師宴”和“金榜題名”穿越進了大學的年輕人就探頭探腦出現在身邊。有關統計數字說,2011年高等教育招生錄取的農村學生約占30%,其中重點大學的農村生比例不到兩成,中國農業大學農村生占三分之一,北京大學在2010年隻有一成,清華大學2011年來自縣以下的學生不足兩成,1980年代清華的農村生大約占二分之一。在就業形勢嚴峻的今天,人們普遍認為隻有“一線名校”出來的學生就業才比較有保障,而在教育公平上始終處于劣勢的小地方普通人家和農村貧困家庭的學生比起20年前或30年前,現在想進入一線名校是難上加難,這一先天弱勢者大多湧進二三線城市的普通大學。
我們這海島學校恰恰錄取了更多的農民之子,按我的粗略計算,連續幾年都超過一半。農村生集中擠進非一線名校,很快會有失落感,他們發現身邊太多的不如意,校内校外都看過了,和電視上網絡上斑斓光鮮讓人心動的生活差距很大,他們歎氣啊感歎啊,後悔沒考好,沒進得了大城市名學校。
其實,今天中國的很多城市都存留着粗鄙肮髒的城鄉接合部,從北大西門出去幾百米也好不了多少。但他們心不甘,苦熬了12年分明應該熬出更時尚更現代的好生活,打開電腦就能看見的那些“潮”,忽然發現其實離得很遙遠,甚至比曾經的憧憬還遠。他們短促鮮嫩的人生一開始就遇到不公,很多憤懑自然會滋生。課上讀了食指詩歌“相信未來”的一個中午,有個女生随我離開教學樓。她問我:老師你相信未來嗎?
我得實話實說,我說:我不信。她說:我信,我什麼也沒有,隻有拼未來。這是個湖北姑娘,父親在北京打工,老家還有弟弟在讀書。和她分手後,我想到一年前,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編輯跟我說,他雖然每接到老家人的電話,都會叮囑要供孩子讀書,其實自己也知道這已經不是心裡話,他家鄉也在湖北,他們那兒稱呼剛畢業的大學生“廢人”:苦活累活技術活都幹不來,做什麼都不會,白花錢白念書,不就是廢人嗎?兩年前我教過的學生盧小平來做客,他大三了,從大一起一直在肯德基打工。坐了兩小時,幾乎都是他在說,我在聽,說他在肯德基打工一年多的各種趣事,他騎什麼樣的電動車去送外賣,配有什麼樣的頭盔,遇到什麼樣的顧客,善良的女人和無理的富人,平時怎樣考核晉升,集體組織的旅遊。他說,老師我這下知道了,“旅遊”就是坐車到一個地方下車轉一圈,再坐上車回來。這個貧困家庭出來的孩子,在這次出遊之前是沒有過“旅遊”的。
我實在沒想到,在一家快餐店裡見到的瑣碎細節對于這個鄉下來的孩子,會這麼盎然有趣。我問他晉升沒。他說提前好幾天就背題了,最後還是沒考上。老員工提醒過要送禮的,但是盧小平說他不想“那樣”,不想學那個,他說:這個我還是堅持,即使沒錄取也不抱怨。起身離開前,他忽然抱歉說:怎麼全是我在說呀,說得太多了,耽誤老師休息了。盧小平是帶了禮物來的,兩包當地的茶,非要給我。我說你怎麼能帶禮物呢?其實我不該說出“禮物”兩個字,這讓他有點不安,連說幾遍:是我奶奶說的,看老師不能空着手,是看老師嘛。
不知道他奶奶是個什麼樣的老人,不知道他老家江西是不是也供着“天地君親師”的牌牌。我知道這個學生平時沉默腼腆,他來做客或者就是想說說話,自由流暢快樂地表達。兩小時裡,他一句都沒談到在學校看了什麼書聽了什麼課。
連續做了五年問卷調查,關于課外閱讀一項統計,被讀到最多的是早已離世的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而一個大二學生說,進了大學她才看第一本不是教材的書:王朔的《千萬别把我當人》。
我接觸的這個大學生群體,跨過了人生的18歲,已長大成人,在來大學之前幾乎沒有課外的閱讀,他們的意識裡灌滿了教科書,甚至連中國鄉間千百年來形成的鄉規民約、最簡樸的道德傳輸也缺失了,空了巢的鄉間沒有唠叨,沒有戲台,沒有族群間的溫暖和限制,有說服力的可信賴的道德對他們是空洞狀态。
是以才有學生在看過好萊塢的《聞香識女人》後,說那個中學生很虛假,保送哈佛,這麼大的誘惑誰能放棄,告密又有什麼,要保護的又不是家人朋友。年輕人的價值判斷标準已經一路混沌一路後退,隻剩了本能,既有本能的嫉惡如仇義憤填膺,又有本能的趨利避害實用哲學,刀槍劍戟,該用哪個操練哪個,不覺有沖突。
一個女生興緻勃勃去上海看世博,回來對我說,原來沒怎麼見過紅綠燈,到上海吓得夠嗆,那麼多人啊,很怕看錯了燈。中國的12年基礎教育,沒有課文和老師告訴鄉村的孩子什麼是紅綠燈,這類常識都缺失,怎麼能去要求他們有完整的價值觀和判斷力?曾經,讨論一條新聞,我問,如果你目擊了一個事件,你知道事實,在需要站出來作證的時候,你是選擇沉默還是說出真相。
兩個班的學生反應截然不同,大三的教室裡頓時安靜,神情僵住,鴉雀無聲。下課後,一個女生對我說:老師,出來作證的人比死了的還慘。另一女生說:我得問我爸爸,他讓我說我就說。而大二那個班級曆來踴躍,聽我一說,立刻有三分之一人攢動舉手:要說真相!我對剛放下手的他們說:請你們設身處地,我相信真的事到臨頭你們會害怕,當舉手沒有絲毫風險的時候,這選擇不難,而堅持正義必定有風險。一個人的本性裡有害怕,同時也敬仰正義和英雄,和後者比,害怕更該是人的常态。
現實往往以理想主義的失敗收場,因為人不能不害怕,不能不自保,這個更真實,眼下的你們隻要堅信,這世上是存在對和錯的。另一次,我在課上說“活着就是掙紮”,沒幾天,收到學生短信問,怎樣才能找到表達“活着就是掙紮”的場景,她要趕作業。現在這同學已經畢業,曾經想回廣西老家,在首府南甯找份工,離鄉下的父母近一點,但她父親不同意,說你不要回來,回來我們幫不上,你就要到外面闖,她在海口找了份工作。
大學四年,父親從不主動給她電話,父親對她說得最多的就是:沒啥事挂吧。她一工作,父親總來電話問這問那。她跟我說,這回明白活着真是掙紮了。20歲,兩手空空,看不見未來,這些在作業中自稱“小可憐蟲”的人,幾乎被那個龐大而完全不可控的社會給吓着了。
有人告訴我,接到一同學短信說:咱們倆一起去死吧。他就回答:好啊,你快來吧,我先把你殺了。說這些的時候,他表情平靜,還帶點笑意。我說:怎麼就說到了死,這不是随口說着玩的。他說:就是嘛,是以我沒搭理他。9月,我買了幾本書分發給他們自願傳遞閱讀,10月,有一本書已經默默無聲地傳回到講台上,并沒收到一個人的閱讀回報。
讀書重要還是吃飯重要,吃飯重要;義憤重要還是吃飯重要,還是吃飯重要。他們正在努力向前看,發現看不到路徑,而很多來自鄉村的學生還沒有意識到,一旦把戶口遷到大學,再想遷回去做農民已經不可能,曾經他名下的土地被收回了:你念了大學,變成吃紅本的,是國家的人了,戶口隻能落在鎮上。出來四年,土地沒了。
是以,真正的問題也許不是寒門是否出貴子,而是寒門無退路。他們是懵懂着靠本能長大的一代,沒有一份工作等着他,他就心虛得很。在這種狀态下,讓他們選擇無所畏懼地去捍衛理想,不真實,甚至不道德。至于想擠進公務員系統,在我所接觸的學生中很少有人動那念頭,那是一線名校的事兒。
他們有份工就行,月月領得薪水就行,與其讓他們擔當,不如先等他們找到飯碗。在“揾食”的過程中,等待擔當的自然發生,讓我看,幾乎是必然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