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形容一些大學者“著作等身”,但這對顧誠先生(1934-2003.6)卻不适用。這位當代明清史學家生前隻出版了兩本專著,即《明末農民戰争史》與《南明史》。作為他的代表作,出版于廿年前(1997年)的《南明史》堪稱顧誠先生“十年磨一劍”的傑作。
學術苦行僧
1934 年11月28日,顧誠先生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乳名“小六”。其父顧祖蔭在民國年間擔任過國立中正大學副教授。出身書香門第給顧先生與其兄弟姊妹提供了良好的治學潛智,日後國務院公布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中,顧家有包括顧誠先生在内的三人榜上有名,這在全中國也是極其少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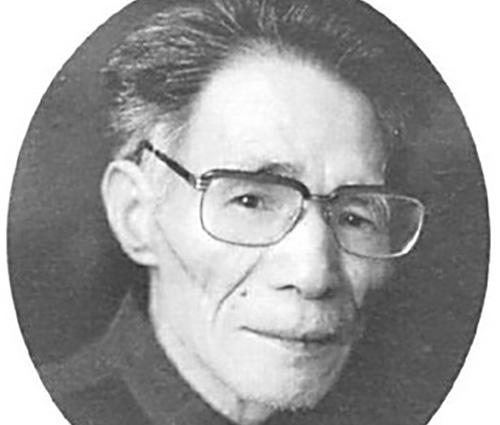
顧誠先生
1957年,顧誠先生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曆史系。讀書期間,他就參與了故宮博物院檔案部(今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的檔案整理和周一良先生主持的通用教材《世界現代史》的編寫工作。由于他出色完成了任務,也得以在1961年畢業後留校執教,最初到白壽彜主持的“中國史學史組”工作,被安排從事明清史學史的研究,從此與明史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1978年5月,顧誠在《曆史研究》發表了《李岩質疑》一文,逐一否定了與李岩有關的記載,并解釋清楚了李岩傳說的來龍去脈;這也成為他的奠基之作。李岩其人因郭沫若的名著《甲申三百年祭》而變得家喻戶曉,在姚雪垠的曆史小說《李自成》裡也成為重要角色。然而顧先生在研讀史料時發現,這位據說地位僅次于李自成的農民起義将領的史料竟然沒有一條能站得住腳,大量可靠史料證明李岩完全就是位“烏有先生”。由于此文觀點新穎,立論有據,在國内外引起了比較廣泛的注意,也令顧誠先生名聲鵲起。
《甲申三百年祭》
在看似“一鳴驚人”的背後,是顧誠先生一生心無旁系,潛心治學,平均每天讀書時間在10小時以上。顧誠自己說過,從年輕時他就騎着自行車,到城裡各大圖書館和檔案館去看書、查資料。為了節省時間,中午啃個自帶的幹饅頭充饑,直到閉館才回家。不管是盛夏還是嚴冬,從未停止。寒冬臘月,有時朔風怒吼,雪花飛舞,握着車把的雙手凍麻木了,就到街邊商店裡的火爐邊烤烤。他去的次數太多了,以至許多圖書館和檔案館的管理人員都認識他。到了晚上,他則在燈下整理抄回來的資料,或者撰寫論著。據說,在顧誠書房的桌子上擺着幾大摞一尺多高的稿紙,那都是從圖書館和檔案館摘抄下來的資料。他不用卡片抄資料,說是卡片抄不了幾個字,而代之以稿紙,一張稿紙不夠就再加一張二張,可以完整抄下一大段資料。可想而知,在沒有網際網路與電腦的時代,用筆一字一字地抄寫,得花費多少時間和精力啊!也就是以,由于長期白天黑夜連軸轉,腦子高度亢奮,顧誠先生很早就落下個失眠症,起初是要到夜裡三四點鐘才能入睡,後來則要待到東方發白才能入眠,而且還得服用安眠藥才能睡着。久而久之,生物鐘完全颠倒,形成了晚上工作、上午睡覺的習慣。甚至北京師範大學曆史系裡都知道顧誠先生的這種習慣,把他的課都安排在下午或晚上來上,以免影響他的休息。是以有人稱顧誠先生為“學術界的苦行僧”,這個評價是不過分的。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十年磨一劍
不過,在以多産為特色的當代學術界,顧誠堪稱是位寡作的學者。遲至1982年,他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專著《明末農民戰争史》。這是一部顯示作者治史功力的大作:史料近乎窮盡,考證可謂周密詳審,至今在同類課題中尚無出其右者,是以也榮獲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顧誠在《明末農民戰争史》的前言中曾有一個對讀者的承諾,即打算寫一部南明的曆史,作為《明末農民戰争史》的姊妹篇。然而,10多年裡,“隻聽樓梯,不見人下來”,一直延宕至1997年,凡77萬餘字的《南明史》才宣告正式付梓,它與《明末農民戰争史》一起,也成了顧誠先生生前出版的僅有的兩部專著。隻可惜天不假年,長年累月的苦行僧式的刻苦鑽研,終究損害了顧誠先生的健康。他僅得中壽便與世長辭,未能實作完成第三部大作的願望,實在令人痛感惋惜。
《南明史》
這部《南明史》實在是顧誠先生十(多)年磨一劍的嘔心瀝血之作。相比當時已經出版的有關南明曆史的著作,如謝國桢的《南明史略》(1957年)、美國史家司徒琳(L.A.Struve)的《南明史》(1984年)、南炳文的《南明史》(1992年)等,顧誠的《南明史》對史料的搜集遠遠過之。此書直接引用的地方志達200多部,從東北、西北到東南、西南,縣志、府志、州志、省志應有盡有。未引用但查閱過的地方志數更是數倍過于此數。如顧誠先生曾在雲南昆明停留一月有餘,在雲南博物館和省圖書館内遍閱館藏的地方志和相關典籍,細讀并摘錄地方志一百多部,而《南明史》書中引用的卻隻是其中23部,可證其勞動量投入之大。甚至為了進一步對讀者負責,顧誠先生在書中提醒,所引用的史料大多出自其個人的抄錄,盡管“在摘錄時經過核對,力求準确,也不敢說絕對沒有筆誤”。
除地方志外,一些珍貴的史料也是顧誠先生在圖書館裡首次發現或加以引用。《南明史》書中引用的其他古代典籍和第一檔案館、各博物館收藏的檔案材料達300餘部,其中不少為海内外所罕見,如柳同春的《天念錄》、李國英的《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劉武元的《虔南奏議》、張王治的《工垣谏草》等等。以在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發現的自清初武将柳同春所著《天念錄》為例,從書名根本看不出同南明曆史有任何聯系,但此書實際上記載了順治五年(1649)南昌守臣金聲桓、王得仁“反清複明”,柳同春化裝出逃,向清軍報信,南昌城破之後終慘遭屠城的曆史,書裡并配有珍貴的插圖(即《南明史》封面),包括清軍圍困南昌明軍的真實寫照。若不是顧誠先生對史料的仔細搜尋,如此重要的文獻恐怕仍會湮沒在書庫之中。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顧誠先生在全面、系統發掘史料的同時,還認真進行稽核、辯僞和考訂,訂正了許多史書記載的訛誤。比如權威性的《辭海》裡曾經記錄了一個長達十八年(1646年-1663年)的“定武”年号,并歸之為南明“韓王”所有。按此說法,這位韓王在位時間幾與衆所周知的末代南明皇帝朱由榔(1646-1662年在位)的永曆年号相垺,而史書上對這個定武政權的記載實在寥寥無幾,正是顧誠先生利用衆多南明史籍和清初檔案的資料進行排比考訂,指出“根本沒有什麼年号定武的韓主”,厘清了清初遺民查繼佐撰寫的《罪惟錄》據不可靠的傳聞,在南明曆史中增添了一個韓王定武政權而對後世研究南明史事所造成的混亂。
《辭海》
千金難買《南明史》
二十年前《南明史》出版時,堪稱石破天驚。它被譽為南明史研究的裡程碑,而榮獲中國國家圖書獎和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明清史專家,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的何齡修先生為之折服,評價這部《南明史》“它當然不是填補空白之作,但卻代表南明史研究迄今為止所達到的最高水準”;“隻有顧誠教授一人真正前後貫通地、比較透徹地掌握南明史。”
何齡修
由于《南明史》打破了傳統學界以弘光帝繼統為上限和以永曆帝敗亡為下限的南明史研究範圍,從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之變寫起至康熙三年(1664年)著名的夔東十三家抗清基地覆滅為止,“基本上是以大順軍餘部、大西軍餘部、‘海寇’鄭成功等群眾抗清鬥争為主線,而不是以南明幾個朱家朝廷(弘光、隆武、魯監國、紹武和永曆)的興衰為中心”;自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議。《吳三桂大傳》的作者李治亭就認為,這是“給予明清史諸多重大問題以不公正地評價,将80年代以來所取得的某些共識重新給翻了過去”,“按‘武裝抗清運動’終始時間界定南明史,顯然不正确”,“不過是蕭一山式的‘民族革命’論的翻版。”
盡管如此,正如何齡修先生所說,“任何治史者隻要涉及南明史,不管是贊成還是反對這本書(指顧誠《南明史》)的觀點,都不能不讀它,對它所理清的史實,即使不願意也不能不接受”。即使是理念與顧誠完全相悖的李治亭,也不得不承認“作為明清史研究者,我觀《南明史》,為其精湛的史實考辨,細密之論證所折服”。
更為耐人尋味的是,《南明史》不僅是學術精品的典範,受到海内外學術界的廣泛贊譽,而且寫得深入淺出,帶給諸如筆者這樣的具有一定曆史知識的讀者以賞心悅目的快感和啟人心智的愉悅,據說連印刷廠的《南明史》校對勞工也讀得津津有味。可能出于這個原因,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南明史》在市面上很快售罄,舊書網上甚至炒到了好幾百元一本,誠可謂是“千金難換《南明史》”。直到2011年(顧誠先生去世後的第八年),光明日報出版社才重新出版了這部顧誠先生的代表作,重版後的《南明史》更全文收錄顧誠先生生前撰寫的《我與明史》,回顧其幾十年的學術生涯,并附有顧先生的手迹。頗有些耐人尋味的是,當時的《出版參考》在《新聞播報》欄目為之所配的新聞标題赫然寫着:為真史學“衛道”《南明史》新版亮相。
新版《南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