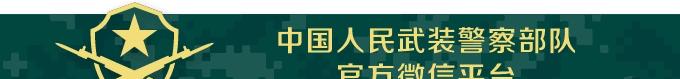
一部電影觸動的集體記憶
——走近武警官兵眼中的《長津湖》
“這場仗如果我們不打,就是我們的下一代要打。我們出生入死,就是為了他們不再打仗。”
——摘自電影《長津湖》台詞
武警第一機動總隊某支隊某大隊某中隊營區。
大螢幕上,電影《長津湖》已近尾聲。
在美陸戰1師有史以來“路程最長的退卻”途中,眼前一幕令他們膽寒:一排排志願軍戰士俯卧在零下40攝氏度的陣地上,手握鋼槍、手榴彈,保持着整齊的戰鬥隊形和戰鬥姿态,仿佛随時準備躍起沖鋒……
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情緒,豆大的淚珠從中隊官兵的臉頰滑落。
這是一場穿越時空的相遇——中隊前身:中國人民志願軍第27軍81師242團5連,就是在長津湖戰役中為國捐軀的“冰雕連”之一。
從中隊走出的“全軍士官優秀人才獎”一等獎獲得者、支隊部隊管理科科長邢貞濤這樣告訴記者:“我并不把《長津湖》當作一部電影,我更願意将這3個字稱為‘我們的陣地’。在這片陣地上,我看到了老兵,也看到了自己。”
如今繁華盛世,如你所想
與邢貞濤感受相同的,還有第二機動總隊某支隊班長賀澎。隻是對于賀澎來說,他的感受更為具體,他看到的老兵是他的爺爺賀月賢。
觀影結束後,賀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溫爺爺寄給他的一封家書。
“入朝作戰裝備,每人攜帶一支步槍、子彈100發、手雷4個、鐵鍬一把、幹糧袋一個,還有大衣和水壺等,約有60斤重……”家書中,爺爺簡述的入朝作戰情況和影片中的情景疊印在賀澎的腦海裡,賀澎仿佛能看到爺爺當年和戰友們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模樣。
得知賀澎的爺爺是抗美援朝老兵,中隊指導員金東方邀請老人通過視訊連線的方式,與中隊官兵進行一場特殊的“影迷見面會”。
“我們跨過鴨綠江,敵機白天對我們進行轟炸,我們隻能晚上行軍,白天宿營,風餐露宿。到了北韓大地,隻見滿目瘡痍……”通過視訊聊天,老人動情地為官兵們講述戰鬥經曆。
聽到賀澎班裡的新兵米思達問到“如何了解軍人的榮耀”時,老人回憶起了自己在戰場上寫下決心書的情節。他說:“我在決心書中寫道:要為祖國人民增光,要為北韓人民報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生而為英,死而為靈。”
一場線上“影迷見面會”,恰似一堂别開生面的網絡微課。賀澎說,一次不經意間,我看到米思達在筆記本扉頁上寫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幾個字。
在賀澎的筆記本裡夾着爺爺寄來的家書,從中可以看出爺爺對他的希冀:帶領全班同志學好政治理論,學好軍事,提高作戰能力,互相幫助,共同學習,親如兄弟……
這兩天,爺爺說為他寄來了自己親手謄寫的兩份黨史學習資料,要他注意查收,并利用開班務會的時機為戰友宣讀。爺爺在發來的資訊裡反複強調:黨史必須學好,要提高思想認識,汲取奮鬥力量。
相比于江西總隊萍鄉支隊教導隊指導員彭春華,賀澎是幸運的。彭春華雖然同樣擁有一封爺爺彭歸當的家書,但紙張卻早已泛黃、殘缺。
當年,當聽到鄉政府來人說,國家号召廣大青年保家衛國、抗擊美帝國主義時,已然結婚生子的爺爺毅然離開家人、報名參軍。1951年4月,爺爺到達河北,被編入志願軍第68軍204師610團。兩個月後,部隊就開赴北韓前線。
1951年9月,“聯合國軍”發起秋季攻勢,向金城、文登裡一線發動猛攻,并針對志願軍反坦克火力薄弱的短闆,集中大量坦克,實施坦克叢集突擊的“坦克劈入戰”。他們首先使用飛機和大炮對中朝軍隊陣地進行反複猛烈的轟炸和炮擊,然後以20至40輛坦克組成坦克叢集,引導步兵在飛機、炮火掩護下沿公路及兩側地域實施快速突進,迂回割裂中朝軍隊前沿各個防禦陣地間的聯系,再由步兵逐個占領各個高地。
當時,志願軍的反坦克火力分為3層,最遠的一層由野炮和山炮組成,中間一層為無後坐力炮和火箭筒,最近的一層為反坦克手雷和爆破筒。換言之,敵坦克越接近陣地,志願軍可以投入戰鬥的武器種類和數量也就越多,火力密度也就越大,對敵坦克的殺傷效能就越高。
據爺爺的戰友陳金生回憶,每當敵人對高地輪番轟炸時,志願軍官兵就一起進入地下工事躲避。當坦克逐漸靠近時,他們就在火力掩護下,迅速向坦克接近。當距坦克10米左右時,他們再以反坦克手雷将其炸毀,然後利用煙幕掩護迅速撤離,而後再以同樣方法打擊下一輛坦克。
憑借這種“貼身肉搏式”的攻擊,爺爺所在部隊在緊急接防、敵情不明、地形不熟、兵力火力不足、工事不完備的情況下,連續奮戰20多天,粉碎了敵軍的“坦克劈入戰”,創造了人民軍隊曆史上步兵反坦克的光輝戰例。
當看到電影《長津湖》中,穿插7連官兵拿炸藥包炸坦克的畫面時,彭春華想起了爺爺。在1952年4月的一次春夏鞏固陣地作戰中,一顆炮彈落入志願軍營地,爺爺倒下了。而在開赴北韓前,爺爺為了告知家人他在部隊情況所寫的家書,還未寄出就變成了遺書。部隊在整理爺爺遺物時把它寄回了家裡。于是,一封泛黃、殘缺的家書,一份志願軍第68軍204師政治部的犧牲證明和一張革命烈士證書,便成為爺爺留給家人的全部。
在彭春華的記憶中,奶奶總會拿出用紅布包了一層一層的物件,對他講:“春華,你爺爺可是志願軍戰士,打過美國佬,是英雄!”紅色的種子由此在彭春華心裡生根發芽。
2013年,高中畢業的彭春華毅然報考軍校。當他第一次穿着軍裝回家時,奶奶說仿佛看到了爺爺離家時的模樣。彭春華知道,從他穿上軍裝的那一刻,他和爺爺就不隻是親人,更是跨世紀的戰友。
彭春華多麼希望爺爺能看到自己穿的軍裝,厚實、暖和,再也不會冷了。就像電影《長津湖》官方微網誌釋出的海報上所寫的那樣:如今繁華盛世,如你所想。
當上海總隊執勤二支隊執勤十七中隊四級警士長穆青把自己當時新配發的17式作戰靴拿回家時,爺爺穆志根捧着那雙鞋,左看右看,直言曾經的自己根本想都不敢想。
自打穆青記事起,家中的鞋櫃上就一直放着一雙鞋。它破舊不堪,布滿了荊棘劃過的痕迹。但就是這樣一雙鞋,每年建軍節的時候,爺爺總會擦拭一番,對穆青和父親再次講起那雙鞋的故事……
穆青的爺爺參加過抗美援朝戰争,是志願軍第38軍113師337團的老兵。爺爺說,當年他們連受命夜襲松骨峰,在連夜趕往陣地時,他的鞋踩在了一枚鐵釘上,鞋底破了個大洞,腳上血流不止。這時,爺爺的老班長把自己的鞋脫了下來,讓他穿上。“當年要不是這雙鞋,估計我這條命就交代在松骨峰了。穿着這雙鞋,即使零下幾十攝氏度的天,雪窩子的水直往鞋裡灌,但我的心裡也是暖的。”爺爺回憶起當時的情景,眼裡閃爍着淚花。他挂在嘴邊的隻有戰友給予的溫暖,卻從未提及由于重度凍傷,他的大腳趾在戰鬥結束後被切除的苦痛。
受爺爺的影響,穆青的父親剛滿18周歲就光榮入伍。穆青兒時,父親經常會跟他講起參加邊境自衛反擊戰時的故事。聽父親講,為了防止叢林裡隐蔽的尖銳物紮腳,當時的膠鞋統統加裝了4層厚厚的底子,在炎熱的氣候條件下,這雙鞋讓戰士們分外難受。
2005年,穆青參軍入伍,腳上的99式作訓鞋讓休假回家的他格外“拉風”。當07A式作訓鞋配發部隊,幹爽透氣的網布,采用橡膠凹槽設計的鞋底,穆青直呼體驗“滿分”。
鞋櫃旁,爺爺整齊地碼放着幾代軍用鞋,嘴裡念叨着“祖國強大了”。在爺爺心中,這些鞋就像是時光的見證者,見證着一支軍隊從裝備簡陋到裝備精良,見證着一個民族從積貧積弱走向繁榮富強。
革命情誼本身就是一種戰鬥力
見證,多麼平常的字眼,我們每個人,無時無刻不在見證着這世間萬象。
見證,多麼珍貴的字眼,對于抗美援朝老兵而言,這兩個字卻是他們犧牲的戰友永遠無法實作的願望。
當看到電影《長津湖》中,穿插7連炮兵排排長雷公犧牲後,連長伍千裡一個人躲到汽車背後,淚如泉湧、顫抖地掏出懷裡的名冊時,甯夏總隊政治工作部新聞文化工作站記者雷鐵飛腦海中浮現出一個老兵的身影。
那是2020年仲夏,雷鐵飛駕車在六盤山颠簸泥濘的山路行駛40多分鐘後,終于到達了固原市西吉縣平峰鎮平峰鄉西莊村——年過九旬的老人尹國俊就住在這裡。
這位曾在北韓戰場上與美軍“掰過腕子”的老兵,雖已是耄耋之年,仍不失老兵風采。
看到穿軍裝的人來到家中,尹國俊就像見到親人一樣,很快打開了話匣子。他說,自己曆任中國人民解放軍7師20團機槍連戰士,志願軍某部班長、副排長。而後,又說起堅守的陣地在毗鄰上甘嶺的一座山裡,官兵們住在用鋼釺在山體上鑿出來的防空洞中,每遇飛機轟炸,都要用木頭抵住防空洞洞頂以防坍塌;吃的有上頓沒有下頓,有時幾天都吃不上一頓飯;夏天,防空洞内潮濕悶熱,隻穿條内褲身上仍長滿痱子,不僅要忍受蚊蟲叮咬,還常被陣地上的鐵絲網劃得渾身是傷;冬天,洞内冰冷刺骨,把所有衣服裹在身上,手腳還是凍得沒有知覺……
當被問及戰鬥經過時,老人卻沉默了。
雷鐵飛分明看到,遲遲不肯開口的尹國俊眼睛裡閃動着淚光。
老人的兒子尹維華在一旁接過話茬:“俺爸在戰鬥中失去了很多戰友,他常說能活下來就是幸運。”兒媳韓萍翠也說:“爸總說自己命大,雖然戰場上子彈亂飛,但他從未受過傷。”
尹維華接着說:“俺爸那時給我們講,美軍的飛機比夏天的蚊子還多,時不時就來轟炸。有一次,敵機飛過來扔下許多炸彈,把山體都炸塌了,30多名戰友被碎石掩埋。後來,當大家将被掩埋的戰友挖出來時,他們都已經停止了呼吸……”
老人不願提及戰鬥,因為每場戰鬥中都有戰友犧牲;不願提及自己的戰功,因為他覺得相比犧牲的戰友,自己做得不算啥。當雷鐵飛想要再了解一下老人三等功證書上面寫的“班長尹國俊指揮得力,帶領全班人員圓滿完成任務”背後的故事時,老人卻隻是輕描淡寫地說:“每次美國鬼子沖上來,都會用機槍狠狠地打,一次能幹掉十幾個……”
臨别之際,老人拿出一本紙張已發黃的戰地日記。身體硬朗的老人翻閱日記時雙手止不住地顫抖。原來,日記本上記錄着老人戰友的名字和家庭位址,老人仍與其中健在的戰友保持着書信往來。而其中更多的名字,卻早已留在了那段戰火紛飛的歲月中……
就像電影中,雷公犧牲之前嘴裡說的那樣,“疼,疼死了!别,别把我,别把我一個人丢在這兒。”雷鐵飛心裡知道,老人也一定曾緊緊握着彌留之際戰友的手,告訴對方,“我帶你回家。”
雷公沒有回家。
和雷公一樣同在炮兵序列的老兵朱再保回到了家。
10月13日,湖南總隊嶽陽支隊官兵代表來到朱再保的家中。
這位93歲的老人聲音洪亮、思維清晰,随着老人的講述,官兵們的思緒回到了抗美援朝戰争的最後一次戰役:金城戰役。
1953年7月13日,為了獲得精确坐标,協助後方炮兵射擊,作為志願軍第16軍47師炮兵團偵察班班長的朱再保奉命帶領5名偵察通信兵,與一支1800多人的部隊共同向前挺進。
“當時我們面對的是裝備精良的精銳部隊,防禦陣地堅固,敵前沿500米以内布滿了地雷,十分危險。”朱再保回憶道,“向前推進時,每一步都是踩在犧牲的戰友軀體上。”為了沖破敵人的防守,1800多名戰士以身蹚雷,保證了數萬大軍安全地向敵縱深挺進。
在執行任務中,朱再保的右腿膝蓋被地雷碎片擊中,皮肉炸裂,鮮血直流。他說:“當時,我的右膝蓋骨都露了出來,但那時候根本不覺得痛,腦子裡隻有一個信念,那就是完成任務。”
到達目标區域後,朱再保精确測量坐标,将要打擊的目标标在地圖上,并将資料通過無線電傳回炮兵指揮部,炮兵成功拿下了一個敵炮兵陣地和一處坦克集結地。因在戰鬥中表現英勇,朱再保被準許為中共預備黨員,火線入黨,并被北韓勞動黨中央授予“民族獨立勳章”。
當記憶從多年前的峥嵘歲月拉回時,朱再保滿懷深情地說:“我這條命是戰友們用生命換來的。我決心,隻要活一天,就要對得起長眠在異國他鄉的戰友們,繼承他們的遺志,傳承他們的精神。”
同樣是為了傳承犧牲戰友們的精神,在抗美援朝出國作戰紀念日即将來臨之際,抗美援朝老兵劉登逸走進重慶總隊執勤一支隊營區,為官兵講述那段難忘歲月。
“我出生于1939年1月,11歲就穿上了軍裝,曆任宣傳員、衛生員、通訊員……”當聽到老人12歲就跨過鴨綠江入朝作戰時,官兵們都感到吃驚,依稀還能聽到有人在小聲說道:“就像《長津湖》裡的伍萬裡一樣,是個娃娃兵!”
無論是影片中18歲的穿插7連戰士伍萬裡,還是現實中12歲的劉登逸,同樣都是孩子的他們,在戰場上逐漸成長。
就像伍萬裡遇到了穿插7連官兵口中的“雷爹”,劉登逸也遇到了許許多多像“雷爹”一樣的人。
劉登逸講起了連長劉克懷。
志願軍第15軍炮兵9團要夜渡清川江。清川江渡口約七八百米寬,水深過腰,水流湍急,稍不留意便有被江水沖走的危險。因為年齡最小、個子最矮,江水幾乎已沒過胸部,劉登逸感覺連呼吸都有些困難,隻能艱難地在水中挪動。“恰在這時,1連的炮車也來渡江了。1連連長劉克懷是解放戰争中的戰鬥英雄,他見此情景,不由分說地一下子就把我背在背上,而後又去指揮4輛炮車過江。”劉登逸說,等到部隊過江後,當他準備感謝劉克懷時,才發現劉克懷和他的連隊已消失在夜幕中。
劉登逸講起了班長宋大寶。
由于在五次戰役中戰鬥減員較大,團部決定把全部宣傳員都補充到作戰一線。出于對劉登逸鍛煉和培養的考慮,團裡把他派到1營當通訊員。報到那天,1營教導員王壽德在了解劉登逸入朝後的戰鬥情況後,叫來通訊班班長宋大寶,對他說:“這是我們全團最小的戰友,今天就交給你了,你可要好好地照顧他。”從那以後,宋大寶在白天執行任務的途中教劉登逸騎馬、打槍,在敵機突然襲擊時教劉登逸怎樣利用地形地物掩護自己;晚上陪劉登逸站崗放哨,教他怎樣判斷有無敵情及如何處理。戰鬥間隙,兩人還一起學習文化。因為劉登逸上過國小,宋大寶會尊敬地稱他為“小先生”,常問劉登逸自己不會讀或不懂意思的字詞。講到這裡,劉登逸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即便有時我把字念錯了、把意思解釋錯了,出于對我的信任,大寶班長總是一邊點頭、一邊默默地記着。”
……
劉登逸還講到了很多人。在宣傳隊時,隊裡的大姐姐們會用撿來的照明彈降落傘給他縫制内衣褲,讓他能有合身的衣服穿;調到1營後,王壽德生怕他被凍着,特地把自己貼身穿的毛衣脫下來拆了,請一位北韓阿媽妮給劉登逸織了一件毛衣……
那一天,劉登逸在台上動情地講述着一件又一件在這場殘酷的戰争中所發生的溫情故事。他說,“那時,戰友的深情溫暖着我的身體,在很多年過後,他們的深情依舊溫暖着我的心。”
那一天,官兵對“戰友”一詞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第14屆“中國武警十大忠誠衛士”、支隊執勤三大隊副大隊長李順說:“從一定意義上講,革命情誼本身就是一種戰鬥力。”“武警部隊士官優秀人才獎”三等獎獲得者、支隊執勤四大隊執勤八中隊四級警士長王凱凱說得更直白些:“平時親如兄弟,戰時生死相依。”
永遠做最可愛的人
說起戰友二字,湖北總隊執勤支隊執勤二大隊執勤九中隊上等兵文敖辰想起了他的“老戰友”,一級戰鬥英雄、志願軍特等功臣、“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七一勳章”獲得者柴雲振。
在樸達峰阻擊戰中,柴雲振帶領全班摧毀敵指揮所一座,攻克3個敵占山頭,殲敵200餘名。
為傳承紅色基因,赓續英雄血脈,中隊充分發揮紅色資源優勢,組建“柴雲振班”。2020年入伍的文敖辰,便是“柴雲振班”的戰士。
觀看電影《長津湖》時,看到伍萬裡被三營營長談子為問“叫啥”,卻用“第677名,伍萬裡”來作答,在文敖辰的嘴邊,一個數字也脫口而出。
969,文敖辰是“柴雲振班”的第969名戰士,這個數字就像許三多會不假思索地吼出“我是鋼七連第4956名士兵”一樣,早已深深銘刻在文敖辰心頭。
其實,文敖辰之是以來當兵,很大程度上是受軍旅題材電視劇《士兵突擊》的影響。
他清楚地記得,劇中,在許三多的入連儀式上,伍六一曾介紹過“鋼七連”的曆史:“抗美援朝時‘鋼七連’幾乎全連陣亡被取消番号,被全連人掩護的3名列兵卻九死一生地歸來。他們帶回107名烈士的遺願,在這3個平均年齡17歲的年輕人身上重建‘鋼七連’,從此後‘鋼七連’就永遠和他們的烈士活在一起了。”
那時,文敖辰不可能想到,未來,他會成為劇中“鋼七連”那樣連隊的一員,中隊前身——志願軍第15軍45師134團3營8連,在那場舉世聞名的上甘嶺戰役中,鏖戰43天,堅守坑道14個晝夜,最後在隻剩9人的情況下,把布滿381個彈孔的戰旗插上了上甘嶺主峰。
戰旗飄揚了半個多世紀,如今,依舊指引着中隊每一名官兵前進。
“柴雲振班”現任班長餘佩海,連續兩年在總隊軍事體育運動會上摘得“軍體之星”桂冠;六班班長餘旭文,榮獲總隊“巅峰”特戰比武偵察專業綜合成績第一名;一班副班長鄭寶達,在總隊“創紀錄、當标兵”比武中,打破總隊紀錄,取得執勤分隊全能冠軍的好成績……
“隻吹沖鋒号,不打退堂鼓”,中隊官兵不但平常時候看得出來,關鍵時刻更站得出來、沖得上去。
庚子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江城。大年初四晚上,中隊接到上級訓示,要求出動兵力幫助駐地搶運防疫器材和物資。收到通知後,中隊官兵紛紛請戰:“沖鋒,這是一名戰士的擔當。”“我是軍人,我不上誰上。”……一封封按着紅手印的請戰書交到了中隊黨支部,10名黨員更是挺身而出,組成突擊隊,奔赴某重點醫院擔負任務。
任務中的一員、中隊副班長張長勝回憶當時的情形時坦言,自己也會害怕,但想起曾在柴雲振的銅像前許下的“為黨和國家獻上自己的力量”的莊重誓言,他頓感熱血在心頭激蕩。
文敖辰說,自己最難忘的一刻就是新戰士入班儀式的場景。那一天,他也定下目标:要做一名當之無愧的“柴雲振式”的好戰士。
與文敖辰一樣,同為《士兵突擊》劇迷的北京總隊執勤六支隊執勤二十中隊列兵馬振傑,看電影《長津湖》時,耳邊就回蕩起“鋼七連”的連歌:“一聲霹靂一把劍,一群猛虎‘鋼七連’。鋼鐵的意志鋼鐵漢,鐵血衛國保家園。殺聲吓破敵人膽,百戰百勝美名傳。攻必克,守必堅,踏敵屍骨唱凱旋。”
幼時看許三多的入隊儀式,馬振傑第一次聽到“鋼七連”的連歌,就不由自主地跟着念。那時,他還不知道,未來會有一首歌,會像“鋼七連”連歌一樣讓他備受震撼。
回憶起新兵下隊第一天時的情景,馬振傑說,新兵們進的第一間屋子就是榮譽室,學的第一首歌就是已傳唱了70年的中隊隊歌。
在指導員劉英健的介紹下,馬振傑了解到,中隊前身是志願軍第66軍198師594團1營2連,先後3次榮立大功,被授予“大功連”榮譽稱号。1951年2月,2連奉命到五音山進行阻擊。戰鬥打響後,炮彈橫飛、碎石四濺,山頭被削低1米多,全連官兵經過浴血奮戰,連續10次打退敵人進攻。其間,在203高地争奪戰中,小組長王榮帶領3名戰士堅守陣地三天三夜,打退敵人32次沖鋒。戰鬥到最後,全連共斃敵500餘人,全連178名官兵僅剩11人,包括王榮在内的167名指戰員英勇犧牲。戰鬥結束後,連隊記大功一次,王榮被追記特等功。而為這場戰鬥譜寫的歌曲《英雄的陣地鋼鐵的山》,成為傳唱至今的隊歌。“鋼鐵堡壘”“堅守陣地”等4面用鮮血染紅的戰旗,也成為中隊官兵代代傳承的精神财富。
中隊擔負環京檢查站警戒防控任務。起初,檢查站設施陳舊、環境艱苦,16個人住在不足30平方米的闆房中。官兵們繼承發揚“大功連”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創業,修繕訓練場、粉刷舊營房,使營區面貌煥然一新。
結合近期正在熱映的電影《長津湖》,劉英健為官兵上了一堂題為《最冷的夜,最熱的血》的情景微課。“英雄的陣地、鋼鐵的山,摧不垮、打不爛,敵人要前進比登天還難……”授課接近尾聲,曾受邀參加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的中隊上士言文強站起身來,組織全體官兵合唱隊歌。
歌聲嘹亮,氣勢如虹。一曲唱罷,作為支隊距城區最遠環京卡點的骨幹,言文強又要帶領戰友出發,用他們的堅守確定進京“大動脈”的絕對安全。
出發之前,第一次擔負勤務的中隊列兵王鵬特意跑到榮譽室,又看了一遍著名作家魏巍在了解中隊的戰鬥曆程後為官兵寫下的題詞:“永遠做最可愛的人。”
當王鵬坐上巡邏車出發駛向哨位時,上海總隊機動一支隊十四中隊指導員田雨農也踏上了走訪“天德山英雄連”老兵活動的旅途。
田雨農此行的目的是去拜訪參加過天德山戰役的老兵胡宗文。打開行李包,田雨農拿出一張泛黃的《志願軍》報,一字一句讀着其中一則消息:“鏖戰四晝夜,5連榮膺‘天德山英雄連’稱号……”田雨農想把這張珍貴的報紙帶給參加過那場戰鬥的老兵。
田雨農告訴記者,中隊前身是志願軍第47軍141師422團2營5連。1951年10月1日,在北韓戰場上,美軍向臨津江東岸的天德山發起進攻。這天恰好是新中國的兩周歲生日。一大早,5連官兵們就把一副“争取創造英雄班,不當英雄不下山”的對聯貼在工事門口。連長楊寶山說:“今年的國慶節可真是有意思。敵人既然要來,那我們就給國慶節備上一份厚禮——多殺幾個鬼子,也好讓祖國人民過好這個節日。”
當聽到當年志願軍指戰員的想法時,記者突然想起了電影《長津湖》中穿插7連指導員梅生說的話,“這場仗如果我們不打,就是我們的下一代要打。我們出生入死,就是為了他們不再打仗。”
正如梅生為了讓下一代不再打仗,為了讓祖國人民過好國慶節,楊寶山和戰友們在四晝夜的戰鬥中,抱着“不當英雄不下山”的堅定信念,舍生忘死、頑強抗擊,成功擊退了敵人一輪又一輪進攻。隻剩下4名官兵,仍牢牢地堅守着天德山陣地。戰後,志願軍上司機關授予5連“天德山英雄連”榮譽稱号,記集體特等功。
在田雨農的行李包内,還有一面鮮紅的戰旗,那是“不當英雄不下山”連旗。田雨農說,他會請老兵簽上名字,而後帶回中隊。在抗美援朝出國作戰紀念日那天,中隊每名官兵都會在連旗上簽字,并莊嚴宣誓。
當記者完稿時,田雨農已踏上返程的列車,他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福建總隊廈門支隊機動二大隊機動五中隊上等兵王曉虎寫的題為《為了和平》的詩,作為此行的總結:
最可愛的人啊/是什麼讓你們舍生忘死/肝腸寸斷/是什麼讓你們犧牲自我/無畏極寒/我未曾聽見你們的回答/但我已知道你們的答案/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三次呐喊/彙聚成永不消逝的願/和平/和平/和平……上甘嶺/長津湖/松骨峰/無數的豐碑于此伫立/蔥郁的松柏萬年長青/陰霾褪盡的天空/陽光和雨露折出七彩的虹/橋下面的人群手拉着手/在開滿金達萊花的原野上并肩同行/無數的聲音彙在一起/發出宣告全世界的聲明/和平/和平/和平
。
評 論:
回望曆史 銘記英雄
高福景
1950年11月27日,北韓狼林山脈,美軍主力進入志願軍伏擊地域,聞名于世的長津湖戰役于當天傍晚的飛雪中打響。
70年後,抗美援朝戰争題材電影《長津湖》如當年戰場上的照明彈,升上了時代的天空,再次照亮了華夏兒女的集體記憶,引發情感共鳴和家國情懷。
在戰争影片的叙事下,武警部隊官兵想起了一些或見到、或聽到、或深植于靈魂的故事,心裡又産生了一波震撼。
這些故事,有的來自耄耋老兵的記憶,有的源自烈屬珍藏的家書,有的存于一代代官兵的血脈。走進曆史深處,我們看到,舍生忘死的“剛強”之外,“最可愛的人”的故事蘊含的是義、是情、是愛——
他們也渴望熱氣騰騰的生活,但遇到侵略者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往上沖,不惜以血肉同鋼鐵相搏;他們有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卻也因失去戰友而有“說不出的痛”,不願提及戰鬥和戰功;他們為了國家、民族,去執行一道指令、堅守一塊陣地,烈士英靈化作編号、唱成戰歌,永遠和布滿彈孔的戰旗活在一起;他們也是爹娘眼裡的孩子、妻子眼裡的丈夫、孩子眼裡的爸爸,卻有那麼多面容化作大山荒原裡一塊塊無名豐碑……
逝者如斯夫。在波瀾壯闊的曆史長河中,英烈的身影像江水一樣東流而去,但他們絕不是過眼雲煙的無名符号,他們不應被忘記。
為了下一代遠離硝煙,英雄把熱血融進土地,是壯歌,更是史詩。那些炙熱與苦寒、堅忍與深藏、盼望與現實的強烈對比,讓人感慨、引人深思。隻有親曆過戰争的人,才知道和平有多珍貴;隻有與死神抗争過的人,才懂得平安是多幸福;隻有凝視過、聆聽過、閱讀過這些“普通人”和他們故事的人才明白:銘記,是對他們最好的緻敬。
有一段關于電影的觀後感在網上熱傳:電影結束後等了很久,沒有期待中的彩蛋,當我走出電影院,雖已近淩晨,卻發現街道旁紅旗飄揚、燈火闌珊、熱鬧非凡,想來這就是最好的彩蛋。
祖國不會忘記,英雄将被永遠銘記!
文字:栗森陽
朱朝陽、謝昊男、彭春華、馮來來、穆青、雷鐵飛、姜炜、何濤、陳磊、陳佩、李岩、王曉虎、毛勝濤對本文有貢獻
供圖:張丹、謝昊男、彭春華、展燦、郭傳伍、鄭傑、趙明、李岩
來源:人民武警報·星期特刊
監制:劉鳳橋、張紅衛
執行監制:張金嶺
主編:關樹聲、王文
值班編輯:别特、王燕婷、梁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