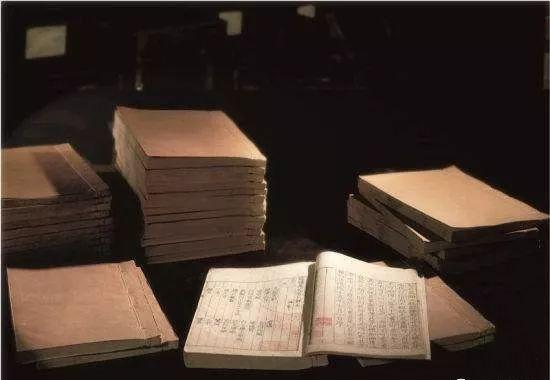
“内”與“外”是一組相對的概念,當這組概念與中國古籍和古文獻學的聯系日漸緊密的時候,中國古文獻學的曆史将會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同時,它也将成為中國學術國際化建設和中國傳統文化在世界範圍内複興的又一個具體展現。從中國古文獻學的角度明确提出其涉外問題,旨在以國際視野重新審視中國古籍及中國古文獻學研究。本文嘗試從當今凸顯的許多有涉外特征的古籍入手,探讨古文獻學研究在其影響下所出現的新問題。這是中國古文獻學國際化建設的重要起點,是拓展中國古籍和中國古文獻學研究次元的自覺。
一、中國古籍的“中國”問題
“古籍”是“中國古代書籍的簡稱,主要是指書寫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國古典裝幀形式的書籍”[1]1。這裡的古籍其實就是“中國古籍”,隻是這個内涵界定更側重“古籍”二字的具體闡發,而對概念中“中國”的含義語焉不詳。關于“中國”古籍中“中國”二字的内涵以往并未明确界定和深入探讨,中國學者大體約定俗成地認為,刊刻出版并收藏在中國境内的、作者是中國人的、以漢語或中國境内其它民族語言編撰的古籍就是“中國”古籍。然而,近些年随着古文獻學學術的繁榮發展,國際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學界對中國古籍内涵與外延的認識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内”與“外”的邊界在被突破與融合。在具體的古籍整理實踐中,遇到的相關具體問題也不一而足,很多時候需要暫停工作,思考和界定中國古籍的概念問題。是以,為當代中國古籍整理工作和古文獻學研究服務計,在已有認識的基礎之上,根據古籍整理的相關情況加以總結,補充中國古籍之“中國”的内涵和外延,是必要且重要的。這一問題主要涉及地域、作者、語言三個方面。
所謂地域的問題,指中國國内與國外之别,其實是說域外中國古籍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界定“中國”,需要結合中國古代曆史地理的知識,注意中國古代不同時期邊界的變更與邊界内外的差異。當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擁有主權的地區統稱為“國内”。這個意義上的中國古籍,原則上應該是指産生、流通、收藏于中國國内的古籍。但是,在“域外漢籍熱”的刺激下,究竟怎麼看待域外的——即流通、收藏于國外的——中國古籍就變成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其實,中國古已有中外文獻的交流,中國古籍流傳海外的情況早已存在。例如,1651年,意大利耶稣會士衛匡國傳回歐洲時,把他在中國搜集到的中國書籍帶回歐洲;1682年,柏應理抵達羅馬時,一次就攜帶中國書籍400多冊;1694年,白晉傳回法國時,将中國書籍300多卷贈送給法國國王等[2]41-42。中國古籍流傳海外後,被國外學者與機構翻刻的情況也很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和刻本”,即日本刊刻的中國古籍,主要指日本明治維新以前,1603-1866年間大批翻刻的中國漢語書籍。張元濟主持編纂的《四部叢刊》就收錄了日本正平本《論語》、天明本《群書治要》等一批可以對中國傳世典籍有所補益的重要典籍。雖然,中國古代曆史上就有了域外中國古籍的問題,但是,直到20世紀末“域外漢籍”興起,它才被中國學界所關注。目前,中國學界對于“域外漢籍是中國古籍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一觀點已達成共識。國外圖書館所編的館藏漢籍圖書目錄便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3],流傳并收藏于海外(國外)的中國古籍也被中國學者陸續考查、整理、挑選、影印回國,并在國内出版、流通,以飨學界。這些工作如今依然方興未艾,像《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書錄》《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錄》《西班牙藏中文古籍書錄》等書目,都是海外藏中國古籍整理編目的成果。而《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則是域外漢籍整理出版的代表作。是以,與中國地域内外相關的“中國”古籍問題中,中國境外的漢語古籍是中國古籍已毋庸置疑。
所謂作者的問題,即中國古籍的作者的國籍是不是中國,其實說的是外國人所作或整理的中國古籍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漢語古籍在中國産生、流通和收藏,但作者是外國人,這種古籍算不算中國古籍?這個答案也應該是肯定的。這種情況較為集中的一個古籍群是晚明時期來華的歐洲耶稣會士在中國用漢語編撰的書籍。在這些古籍中,有些是外國傳教士獨立撰寫的,像利瑪窦(Matto Ricci)的《天主實義》《同文算指》,龐迪我(Didace de Pantoja)的《七克》,艾儒略(Jules Aleni)的《性學觕述》《三山論學記》等;有些是傳教士與中國士人合作完成的,例如利瑪窦和徐光啟合作的《幾何原理》、鄧玉函(Jean Terrenz)和王徵合作的《遠西奇器圖說錄最》等。根據相關研究統計,著錄天主教文獻的古籍目錄書就不少于50種[4];僅“明末至清嘉慶時期的天主教中文書籍,大約有千餘部,詩詞、信函、檔案等其他類型的文獻,則起碼有數千種之數”[5]87;這些文獻從晚明産生起,就已被著錄于《趙定宇書目》《脈望館書目》,甚至《四庫全書總目》等中國古籍目錄中[4];而影印出版的天主教文獻叢書,除了上文提到的《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還有《天學初函》《天主教東傳文獻》《徐家彙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等;注釋整理本則有《明末清初耶稣會思想文獻彙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漢籍叢刊》等。
所謂語言的差異,是指中國的語言和外國語的差異,其實是古籍文本的語種問題。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多種民族文化的國家,但以漢族、漢語和漢文化為主,這裡的中國的語言即以漢語為代表,包括中國境内其它民族語言。而外國的語種則是其他國家諸如日、韓、英、法、德、意等語言種類。與這個問題關系密切的一個概念是“漢籍”。雖然“漢籍”曾指代過漢代典籍,但相對于國外,近現代中國往往采用其漢文典籍之意。“域外漢籍”中的“漢籍”主要就是指用漢語編撰的古籍。也就是說,該古籍是否是用漢語編著的被視為判斷其是否為“中國”古籍的最重要的一個标志。除了大量中國本土産生的漢語古籍以外,儒家漢語言文化圈的問題亦需重視。漢字在曆史上的東亞或東南亞曾經是通用文字。北韓使臣李粹光《芝峰先生集》曾多次以漢語記載他在北京與越南使臣、琉球使臣之間的詩文之交。我們應該将視野擴大至整個東亞曆史上的漢語書寫傳統,将北韓、日本、越南學者以漢語撰寫的古籍納入中國古籍的範疇。或者,至少在一些古籍整理工作中,為學術文化計而将其列入。國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工程《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收錄原采用漢字的國家與地區學人用漢文撰寫的、與漢文化有關的著述。那麼,由這些東亞或東南亞學者用外語所作的對中國古籍進行整理與研究的成果中譯本算不算中國古籍?例如,由日本高島吞象著、清代王治本譯、孫正治點校的《高島易斷:易經活解活斷800例》[6]。再如,日本書志學家長澤規矩也編著的《中國版本目錄學書籍解題》,是作者以日本收藏版本目錄之書最豐富的靜嘉堂文庫藏書為主,配以作者架藏,并補以東京帝國大學藏書及其友人麓保孝收集之書而作的解題書目,而且還附入了《經籍訪古志》《古文舊書考》等日本人編著的中文之作[7]。答案是,這些以漢語編撰或者被翻譯成漢語的、與中國古籍密切相關的成果也應該納入中國古籍整理與研究的範疇。
那麼,以外語撰成,但流傳、收藏于中國的古籍算不算中國古籍?例如中國各圖書館收藏的外文類圖書。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北堂書目》(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中就著錄有4101部西文善本。這批古籍作為晚明以來陸續進入中國、幾百年來在中國流通、現儲存于中國國家圖書館或中國群眾的私人藏書中的在華西國文獻群,曾是明清時期西學東漸的載體與“親曆者”,已被有些學者視為中國古代曆史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再如上海圖書館編的《上海圖書館館藏舊版日文文獻總目》所收錄的上海圖書館收藏的舊版日文文獻41766條,包括圖書、期刊、文集、小冊子、手寫本、非正式出版物等,覆寫館藏八萬餘冊。其出版時間為日本寬政四年(1792年)至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刊行的日文文獻,其中絕大部分為20世紀上半葉出版的圖書。它們存在于中國大地,與中國曆史文化産生了或多或少的文化與文獻的聯系,應該算作外延意義上的“中國”古籍而被中國古文獻學者所留意。
雖然上述分析是将相關問題清晰劃分成三種而論,但實際情況比理論分析要複雜許多。對于每一部古籍而言,它們都是這部書的基本資訊,但在實際的整理工作中,學者們需要綜合考慮這些标準。這就是當代重要的涉外漢籍的整理标準要寬泛很多的原因。例如郝潤華和侯富芳在編著《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古籍目錄提要》的時候,就酌情收錄了一些域外漢籍目錄,像“域外漢籍綜合目錄”、“域外漢籍善本”、“域外方志目錄”、“域外漢籍文學書目”、“域外版本圖錄”以及“域外目錄之目錄”[8]。梵蒂岡圖書館、羅馬智慧大學孔子學院、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原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大象出版社幾方聯手,精心遴選、複制、整理、彙編的《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既是影印的域外漢籍,其所收錄的漢籍的作者又兼具中外。再如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共同主持編纂,多位國内外知名學者出任顧問或編委的,旨在對域外漢籍進行完整而系統的整理,遴選孤本和善本,借此準确把握漢文古籍在域外流傳、遺散、收藏、儲存的基本狀況,為學界提供研究基礎,搶救性地保護世界範圍内的漢字文化遺産的《域外漢籍珍本文庫》。所收書籍均影印自國外圖書館、研究機構和個人收藏的國内不見或稀見的漢文文獻,主要内容有三部分:一是中國曆史上流散到海外的漢文著述,這就打破了傳統的地域界限;二是域外鈔錄、翻刻、整理、注釋的漢文著作;三是原采用漢字的國家與地區學人用漢文撰寫的、與漢文化有關的著述,這兩條則又同時打破了整理和研究者的國籍界限。而其附錄的數百年來歐美來華傳教士用漢字或雙語撰寫的、與漢文化有關的一些重要著作,則進一步突破了語種的界限。
二、中國古文獻學研究的新領域
中國古文獻學是以中國古籍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問,既然中國古籍及相關整理工作涉外的部分已很難被忽視,那麼中國古文獻學研究必然會在其影響下出現新的研究熱點。
第一,古文獻學的基本概念更新和基本理論新建構。在國際化浪潮洶湧的今天,對“中國”古籍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進行重新審視和總結。成為中國古文獻學基本概念更新的一個重要工作。由于中國古籍的“中國”涉及地域、作者和語言三個主要問題,那麼所謂中國古籍實際包括12種情況,分别是“中國産生、作者為中國人”;“中國産生、作者為外國人”;“外國産生、作者為中國人”;“外國産生、作者為外國人”;“中國産生、語言為漢語或中國其它民族語言”;“中國産生、語言為外語”;“外國産生、語言為漢語或中國其它民族語言”;“外國産生、語言為外語”;“作者為中國人、語言為漢語或中國其它民族語言”;“作者為中國人、語言為外語”;“作者為外國人、語言為漢語或中國其它民族語言”;“作者為外國人、語言為外語”等。是以,中國古籍實際上有三個層次:其最核心的部分是指在中國國内産生、作者為中國人、語言為漢語或中國境内其它民族語言的古籍,這既包括在中國的中國古籍和流通、收藏在國外的中國古籍;而以核心中國古籍為底本産生的衍生品,以及對核心中國古籍及其衍生作品進行再整理的相關成果也可納入中國古籍範疇,視為中國古籍内涵的第二層次;既不在中國産生、作者亦非中國學者、語言也不是漢語或中國境内其它民族語言,但與中國曆史文化密不可分并收藏于中國的外語古籍,則可視為最外圍的中國古籍,此為中國古籍的外延。當然,這是一個全新的問題,需要一個逐漸發展和成熟的過程。但是,對中國古籍這一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新界定是當代中國古文獻學的一個基本問題,亦是中國古文獻學國際化建設的起點。
一旦視野被打開,中國古文獻學的基本理論就會受到新的沖擊。近年來,一些年輕的古文獻研究者嘗試對“文獻學”一詞的緣起進行考察,并梳理日本和德國“文獻學”的情況,對它們與中國文獻學的關系提出自己的看法。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歐美文獻學領域的“新書籍史”研究給中國曆史文獻學帶來的改變。張升近些年對西方“新書籍史”研究用力頗多,不僅梳理了西方書籍史研究的專著、學者及觀點,還關注西方對中國書籍史的研究。在此基礎上,他總結了新書籍史對中國文獻學研究的啟示,認為新書籍史将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帶入文獻學領域,為古文獻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張升在西方新書籍史研究的視野下重新審視古文獻學,認為“文獻學是研究有關文獻産生、流通、收藏與整理的學問”。他在其新作《曆史文獻學》中突破傳統,按照“文獻學的理論與研究資料”、“文獻的産生”、“文獻的流通”、“文獻的收藏”、“文獻的整理”的思路诠釋了整體文獻學的理念[9]。另外,對國際相關研究成果的參考和利用,也極大地補充甚至改寫了一些中國古文獻學史及其相關專題的内容。
第二,域外漢籍整理與研究的深入開展。一個方面,域外漢籍及相關文獻的整理工作更加多樣化。除了繼續将域外漢籍善本分批影印回國出版,為保護中國古籍、為學界提供更多寶貴文本之外,很多域外文獻整理的系列成果出現。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出版反映東亞中、日、韓、越交流狀況的使行文獻叢書即是一例。他們倡導“從周邊看世界”,秉持借助異域眼光打量自己,以及域外文獻亦是中國史研究、中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資料寶庫的理念,繼《越南漢文燕行之文獻內建》《南韓漢文燕行文獻選編》之後,又整理出版了《北韓通信史文獻選編》,彌補了中國學術界在通信使文獻整理上的空白。再如《美國所藏容闳文獻初編》,收錄了耶魯大學所藏容闳緻各方友人13封書信、容闳緻衛三畏8封書信、容闳與耶魯大學1854屆同學互相留言選錄,1902年1月1日至1902年11月29日的日記,以及甄選的37頁容闳手迹。還有一種,是對域外文獻的校勘、注釋成果。例如,郝春文等著的《英藏敦煌社會曆史文獻釋錄》三十卷,以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全部漢文非佛教文獻為資料來源,将數百年前或一千多年前的古代寫本,全部按号釋錄成通行的繁體字,并對原件的錯誤加以校理,盡可能地解決所涉及文書的定性、定名、定年等問題。每件文書釋文後附有校記和一百年來學術界有關該文書的研究文獻索引。另一個方面,對中國古籍在海外的流傳及其影響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2007年,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的張西平教授帶領他的團隊開始申請題為“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的傳播與影響”的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2015年,他主持的“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更名為“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标志着域外漢籍與海外漢學的研究更加深入,并聚焦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傳播與發展研究。2015年,他的教育部重大課題結項書稿《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的傳播與影響研究》問世,成為國内乃至國際範圍内第一次對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25個國家的傳播做系統調查和研究的開拓者和中國文化走出去相關研究的先鋒。當然,在這股學術潮流中,還有很多相關學術成果不斷湧現,《從鈔本到刻本:中日〈論語〉文獻研究》[10]、《越南漢籍文獻論述》[11]等是著作代表;而論文則更多,例如《從西北漢簡與北韓半島出土(論語)簡看漢代儒家文化的流布》一文則利用中外出土文獻考察了中國古籍《論語》及其對周邊文化的影響[12];而《陶淵明在北韓的接受與傳播——以〈和歸去來辭〉為中心》則是以文獻為中心的專人研究,考察了中國晉代文學家陶淵明及其思想對北韓王朝的影響[13]。
其實,除了中國學界對中國古籍在域外的流傳、收藏情況進行爬梳和整理以及對中國古籍在國外的影響進行研究之外,國際學者也做了大量這樣的工作。這一狀況是以往學界關注和交流不多的部分。國外各大圖書館或博物館都有重視館藏中國古籍的傳統,并從16世紀以來開展過不止一次的整理編目工作。除上文所述及的幾部,再舉幾例,像1877年大英博物館負責人羅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K.Douglas)編著的《大英博物館藏中文刻本、寫本、繪本目錄》(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14]和法國伯希和編的《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15],等等。另外,出于漢學研究的需要,國外學者對相關中國古籍進行編目的成果也有很多。如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家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編著的《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研究論著手冊》(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16],是研究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的學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參考書,裡面著錄了很多相關中國古文獻。此外,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古籍的成果也應引起重視。杜鼎克的《晚明中國基督教研究五種》就是這方面很好的一個例子[17]。這部研究論著中的研究對象就有晚明時期的中國古籍《南宮蜀牍》《破邪集》《聖朝佐辟》《主制群徵》,成為外國學者從文獻角度研究中國文化的一個典型個案。
第三,開展中西方文獻學比較研究,以資借鑒。世界文明多元共同發展,就古文獻學科而言,中國有自己的古文獻學,其他國家亦有自己的文獻傳承與古文獻學。無論是古文獻的内容、曆史與獨特性,還是古文獻學相關的目錄、版本校勘、注釋等分支學科的理論、方法,都可以梳理、呈現于學林。就像白壽彜所說:“文化是賴比較而更明白的。”[18]434
中西校勘學比較研究的第一人應該是胡适。1933年,他為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撰序,認為中國校勘學不如西洋。他說:“西洋印刷術起于十五世紀,比中國晚了六七百年,是以,西洋書的古寫本儲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校勘,是一長。歐洲名著往往譯成各國文字,古譯本也可供校勘,是二長。歐洲很早就有大學和圖書館,古本的儲存比較容易,校書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較容易,是以,校勘之學比較普及,隻算是治學的人一種不可少的工具,而不成為一二傑出的人的專門事業,這是三長。在中國則刻印書流行以後,寫本多被抛棄了;四方鄰國偶有古本的流傳,而無古書的古譯本;大學與公家藏書又都不發達,私家學者收藏有限,故工具不夠用,是以一千年來,夠得上科學的校勘學者,不過三兩人而已。”[19]122後來,胡适又進一步指出:“中西校勘學的殊途同歸的研究方法,頗使我驚異。但是,我也得承認,西方校勘學所用的方法,實遠比中國同類的方法更徹底,更科學化。”[20]135雖然這僅僅是談及,還算不上真正的比較研究,但卻為文獻學的研究開拓了一個方向。到20世紀80年代末,西方目錄學理論與方法的引介一時成為熱點。2006年,餘英時為劉笑敢的《老子古今》撰寫序言,認為西方“文本考證學”源遠流長,倡導比較研究。他說:“西方在校雠、考證各方面都積累了十分豐富的經驗,文本處理的技術更是日新月異。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界十分熱心于中西哲學、文學以至于史學的比較,但相形之下,‘文本考證學’的中西比較,則少有問津者。事實上,由于研究對象——文本——的客觀穩定性與具體性,這一方面的比較似乎更能凸顯中西文化主要異同之所在。”近些年,蘇傑将西方校勘學的相關理論和論著譯介到中國,2009年編譯出版了《西方校勘學論著選》[21],2015年又翻譯出版了西方古典學、校勘學經典名著《抄工與學者——希臘、拉丁文獻傳播史》[22],做了些基礎性的工作。此外,相關研究課題的立項以及《20世紀西方文獻學發展曆程探析》《20世紀西方文獻學基礎理論研究述評》等論文的發表也說明西方文獻學研究日益受到重視。
第四,中國古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中外文獻交流史的研究是中國古文獻學的有機内容,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獨特存在。原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提出“漢籍之路”,就是要強調典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發揮的重大作用。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除了絲綢、茶葉、奇器外,還有一種十分珍貴的東西——典籍,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典籍交流已被國家高度重視。以往中外學者對文化交流的研究多側重于曆史事件、曆史人物等,而典籍文獻往往被認為是曆史研究的史料基礎。其實,文獻交流是文化交流——尤其是某些曆史時期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是文化交流史重要的研究對象之一。文獻不僅是記錄與儲存文化的重要方式,在文化傳播中也發揮着巨大的作用。而且,這些中國古籍在不同國家和文化之間流通的曆史本身就是文獻流通史的主要内容。明末清初,歐洲傳教士入華,西方書籍就是他們獲得中國人好感的重要工具,不僅從歐洲募集大量西方書籍并攜帶至中國,而且将中國古籍攜帶、譯介至歐洲,成為中西文獻交流史上濃墨重彩的一頁。1877年2月,英國哈福德史蒂夫·奧斯丁父子出版社出版的《大英博物館所藏中國古籍和印刷品目錄》中有這樣一段序言:“本目錄包括的中國圖書于不同時間、不同條件逐漸被收藏。圖書館小部分館藏來自斯隆、哈利父子、舊皇室和蘭斯等遺産,主要館藏來自1825年赫爾(Fowler Hull)先生所贈。1843年,英國皇室将在鴉片戰争中所獲中國圖書贈予圖書館。”記載了鴉片戰争中英國軍隊從中國掠奪的中國古籍大約有2萬冊之巨。清末陸心源皕宋樓藏書甲于海内,其子陸樹潘将其售于日本三菱财團岩崎家,落得“民族文化罪人”的罵名。而這四萬多冊中國古籍經過百年,完好儲存至今,這又不得不歸功于日本岩崎家的文化公益事業經營政策。2013年北京大學圖書館購入的“大倉文庫”典籍,是1912年董康赴日時将自己誦芬室部分舊藏和譚錫慶正義齋的部分典籍售于大倉文化财團創始人大倉喜八郎的重要古籍,在日本大倉文化财團大倉集古館以“大倉藏書的名義”儲存了一個世紀。這931部、28143冊典籍傳回北京大學圖書館,被以“大倉文庫”專藏形式永久整體儲存。這一段又一段的中外文獻交流的故事告訴人們,古籍不僅是記錄文化的載體,還是儲存文化的功臣、傳播文化的媒介。
三、中國古文獻學涉外問題研究的意義
2016年由中華書局主持、國外多家藏書機構共同參與的《海外中文古籍總目》已啟動,被列入“十三五”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五大重點之一,是中華書局長期以來關注海外中國古籍的整理編目與出版工作的一個重大項目,旨在摸清海外圖書館存藏中國古籍的家底。這樣看來,借助古籍數字化技術,《全球中國古籍聯合目錄》的編成指日可待。古籍數字化使傳統古籍與當代世界先進的資訊技術完美結合,建設“全球中國古籍數字圖書館”也會實作,中國古籍的國内、外地域差異問題有一天将會消失。其實,中國古籍數字化一直就不是技術層面的一個話題,而是一個對資訊技術時代的中國古籍整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傳播、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等很多方面産生巨大影響的革命性課題。而這些又勢必會對“中國文化熱”及“漢語熱”繼續在全球擴充産生不可估量的影響。目前,全球學漢語的人數和開設漢語課程的國家和地區數量激增,漢語教材已經進入美、英、日、韓等國的大中國小課堂。很多歐美漢學家自發研習中國古籍,并日益精通。可以想見,在國内、外産生的、作者為國外漢學家的中國古文獻整理和研究的漢語或外語成果也會日益增多,而這些外語類相關成果的中譯版本也會增多。是以,相關的中國古籍的整理工作将會不斷被提上日程,對中國古籍内涵和外延的清晰的認識必然會促進當代中國古籍整理事業的順利開展。
與此相适應的是中國古文獻學的國際化建設的逐漸展開。到目前為止,古文獻學的國際化建設大概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從國内學者所開展的工作角度來看,最重要和突出的成就是域外漢籍的整理與研究。《域外漢籍珍本文庫》《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海外中文古籍總目》《20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域外的傳播與影響研究》等一批域外漢籍的整理與研究成果是其代表。另外,中西文獻學的比較研究出現,如從20世紀80年代末西方目錄學理論與方法的引介開始,到當下各種課題立項及相關成果發表,這方面的意識逐漸增強,相關研究已經起步。還有國外書籍史等與文獻學相關的專著漢譯本的湧現,如蘇傑編譯的《書籍的曆史》《書籍社會史》《印刷書的誕生》等。這些均是中國古文獻學研究者在國際化浪潮下而初步産生的寶貴成果。但綜合來看,國内古文獻學研究者國際化建設的自覺意識還有待強化,有意識地、全面而深入地探研中國古籍與中國古文獻學的整體世界形象及其貢獻的研究尚顯薄弱。對國外學者在中國古籍的整理研究及其對中國古文獻學的了解與借鑒方面所做的工作,還沒有系統梳理和總結。而要從中國古文獻學的角度開啟這一領域的研究,必須明确提出中國古籍及古文獻學的涉外問題,自覺對其進行全面梳理與理論總結,并清晰認識和把握其對中國古文獻學的貢獻及其與海外漢學、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學科的互動關系。沒有對中國古籍及古文獻學的涉外問題進行的全面梳理和總結,就很難準确把握它在國際舞台上的位置和意義,遑論中西學者中國古文獻整理與研究之比較。
提出中國古籍和古文獻學的涉外問題,還是拓展中國古文獻學研究次元的自覺。20世紀初期,中國古文獻學學科被提出并逐漸建立起來。如今,中國古文獻學的曆史又将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由埋頭梳理和總結中國古文獻學的傳統到自覺将中國古文獻學置于全球視野重新審視,這是中國古文獻學研究次元的增加。次元的增加帶來的将是中國古文獻學研究的巨大變化。因為這樣一來,所研究問題的參照物就會完全不同,其内涵和外延必然需要重新界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古文獻學将可能被重建。當然,在這個重建的過程中,計算機資訊技術和網際網路是其技術革命性助力。在這樣的技術支援下,當代的文獻載體、文獻的産生與流通、文獻的收藏與利用乃至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均産生了颠覆傳統性的變化,中國古文獻學的國際形象建設也得到極大的推動。
另外,中國古文獻涉外的問題對于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國家戰略和中國優秀傳統文獻與文化在世界範圍内的複興亦有重要價值。中國古籍及古文獻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研究中國古籍及古文獻的涉外問題,就是要從中國古籍及古文獻學與其他國家或文化的關系、作用與價值的角度,以全球視野探索中國古籍與傳統文化在世界各國的傳播與影響。對在世界範圍内開展的中國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給予重視與觀照,才能更加準确地認識中國古籍與傳統文化的世界意義,進而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國家文化戰略與中國優秀傳統文獻與文化在世界範圍内的複興提供中國古文獻學角度的支援。(毛瑞方)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行業标準·古籍定級标準[S].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1.
[2]潘玉田,陳永剛.中西文獻交流史[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41-42.
[3]謝輝.歐洲圖書館所編早期漢籍目錄初探[J].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6(2):96-100.
[4]毛瑞方.漢語天主教文獻目錄編纂史概述——以教外知識分子為中心的考察[J].世界宗教研究,2014(3):143-150.
[5]董少新.《耶藏》編纂的構想與建議[C]//宗教與曆史(6):漢國文獻與中國基督教研究(上冊).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6:87.
[6]高島吞象.高島易斷:易經活解活斷800例[M].王治本,譯.孫正治點校.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7]長澤規矩也.中國版本目錄學書籍解題[M].梅憲華,郭寶林,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
[8]郝潤華,侯富芳.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古籍目錄提要[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9]張升.曆史文獻學[M].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10]劉玉才.從鈔本到刻本:中日《論語》文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11]陳益源.越南漢籍文獻述論[M].北京:中華書局,2011.
[12]郝樹聲.從西北漢簡與北韓半島出土《論語》簡看漢代儒家文化的流布[J].敦煌研究,2012(3).
[13]向世俊子.陶淵明在北韓的接受與傳播——以〈和歸去來辭〉為中心[D].青島:中國海洋大學,2013.
[14]道格拉斯.1877年版大英博物館館藏中文刻本、寫本、繪本目錄[M].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
[15]伯希和,高田時雄.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M].郭可,譯.北京:中華書局,2006.
[16]Nicolas Standaert.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ume One:635-1800)[M].edt.Brill,2001.
[17]A.C.Dudink.Christianity in Late Ming China,Five Studies[Z],manuscript.
[18]白壽彜.整理國故介紹歐化的必要和應取的方向[C]//白壽彜史學論集(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434.
[19]胡适.胡适文集(5)[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122.
[20]胡适.胡适口述自傳[M].唐德剛,整理,翻譯.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135.
[21]蘇傑.西方校勘學論著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來源:河南師範大學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