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女兒傑西告訴她的母親,她今晚将結束自己的生命......
《晚安,媽媽》(又名《晚安,母親》)是美國劇作家瑪莎·諾曼(Martha Norman)1982年的一部戲劇。這部普利策獎獲獎作品,其中女兒傑西自殺的原因,是人們關注的焦點。
01 家務,掌握命運之謎的"紐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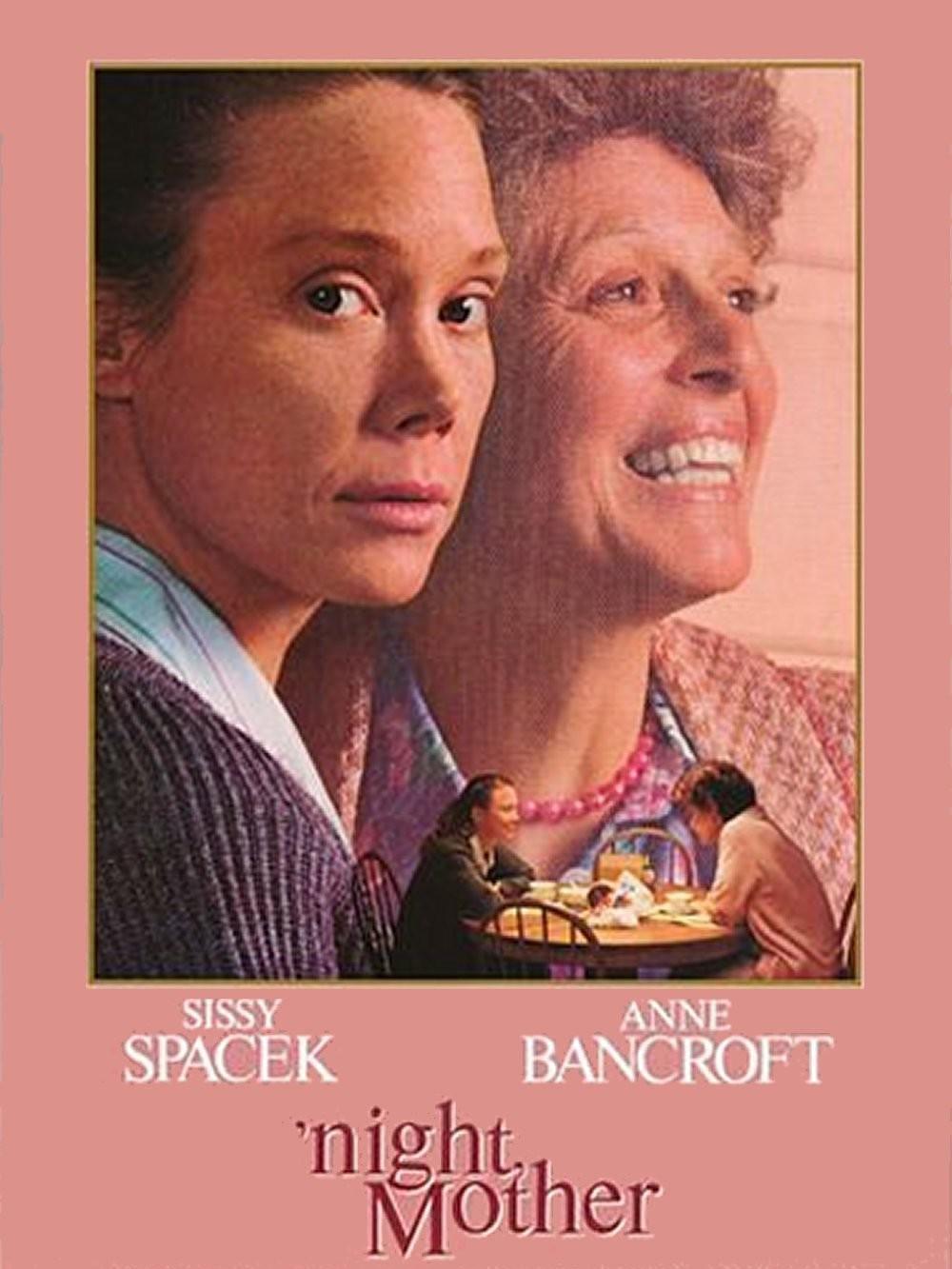
晚安,媽媽電影海報
一些觀衆說這是形而上學的存在主義,而另一些人則更喜歡将傑西解釋為一個抑郁的人 - 盡管劇本,舞台劇和電影都沒有提到"抑郁症"。
劇作家在劇本中沒有使用直截了當的描述,這為角色的命運下了定論,并為觀衆留下了适度的解釋空間。
而電影或舞台劇的創作者,在第二次創作中,從創作者的個人角度,找到緊跟人物命運之謎的按鈕,要更有力地呈現創作者的理論戲劇,就變得特别重要了。
也就是說,作為影視劇或舞台劇的創作者,必須對自己清晰的作品觀點,要有非常清晰的核心表達,并且非常清晰地用螢幕的每一幀、每一個排程來诠釋這個核心,即使從頭到尾都沒有說清楚。
近年來,《晚安媽媽》在內地廣泛的商業唱片中至少四次登上劇場舞台。
最近兩次,一次是由中國戲劇系導演和年輕演員劉丹的林銀宇教授制作的,另一次是由焦化實驗劇團的聯合主演,由舞台劇《金鎖》中的曹啟橋和香港女演員米歇爾主演。
在這些作品中,導演抓住它們來解釋該劇的核心"按鈕"?
在我看來,這似乎是不夠的,特别是與電影相比。
這部電影的成功之一在于對角色命運的诠釋,它采取了一種非常恰當的方式來呈現它。
做家務。
傑西幾乎不停地"做家務"。
校準鬧鐘;整理幹浴巾;緻電取消訂閱報紙;把媽媽回家時丢棄的鞋袋放好;擠壓牙膏皮膚;晚上定期拉起百葉窗;幫助媽媽戴上園藝手套;遞給她的睡衣;填充糖罐;清潔冰箱;扔垃圾,換垃圾袋...
家務總是在傑西的手上發生,合理,如此自然,以至于我幾乎忽略了它。
隻有當你意識到它的存在,來回走動,你才能發現這些瑣碎的瑣事,是電影導演在電影中偷偷放置的"按鈕"。
它沒有大驚小怪,你隻是一次又一次地看過去,直到你終于停止視而不見,去解決它,去解開角色命運的謎團,去了解傑西的真實生存狀況。
就像我們對待現實世界一樣。
02 如何對待家務就是如何對待自己
傑西把浴巾代碼完整地放了
起初,傑西的家務給我一個普遍的印象:
它們看起來"太好了",不會讓我感到困惑。
例如,在浴室中,浴巾是毛巾的大小,折疊成正方形并堆疊在指尖的地方。
這樣的接收方式,對于使用者來說,是好看又友善的,但對于看護人來說,是最不友善的——
因為沒有辦法用完挂回去,而且剛擦掉的浴巾一定是濕的,不能把它折回去一起做成豆腐塊層,唯一的辦法就是用它來清洗、晾幹、重新堆放。
這個過程似乎在酒店裡看得更多。在酒店裡,因為每天都有客房服務員要更換和整理,是以人們可以使用毛巾,随意地把它放在一個地方。
顯然,在傑西的家裡,母親不是負責更換和整理毛巾的人。
傑西在電影中做的很多家務勞動令人筋疲力盡:
例如,傑西的床,帶有毯子的末端,這更多的是裝飾而不是實用,需要照顧物體;
例如,傑西将裝在紙袋中的糖分揀并倒入不同的玻璃糖罐中,用裝有剩餘糖果的紙袋密封,然後按固有的順序放回櫥櫃中......
将糖果袋存放在分類類别中
同時,這些絕不是偶然的。
從傑西的動作來看,她已經太熟悉家務了。從她母親塞爾瑪的反應來看,傑西的所作所為似乎在她眼中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她習慣于不注意。
傑西今天晚上在這個房子裡所做的,絕不是節前的清掃準備,而是她的日常生活。
這使得電影中的傑西,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一個家務高水準的家庭主婦。
一個如此認真地保持家務标準的人不太可能對生活的其他方面沒有要求。
就像走進一個家庭,從家居布局和整潔中可以看出主人的性格。在這部電影中,家務由傑西承擔,就像生活在她身上一樣。
導演在名為"家務"的生活中呈現了傑西對生活的希望和要求。影片對家務勞動的詳細設計,就像是映射了傑西個性中的這種"超人"。
她希望家裡的一切都幹淨整潔,就像她想成為心愛的妻子,母親,職業女性,有吸引力的女人,一個正常的"超級青少年",在社會上似乎與此無關。
但别無選擇,她得了癫痫,丈夫出軌離開了她,兒子是個問題少年,想工作卻繞着牆,被鄰居當成奇怪......
在那個理想中,她離得太遠了,"超級我"像一塊冰冷的裹屍布一樣壓在她的頭上。
人與家務的關系是與現實世界關系的反映。
傑西告訴他的母親,這些東西像管家一樣放在房間裡
在電影中,家務勞動是為了給傑西一種控制感。
在這個房子裡,傑西比他的母親塞爾瑪擁有更多的控制權。傑西熟悉房間的每個角落,這部電影有很多關于設計的細節。
她知道房子裡的燈什麼時候準時亮起,她母親的園藝手套在哪裡,以及洗衣機,膠帶,滑鼠夾,垃圾袋等所有細節。
她就像管家一樣對媽媽要注意事情,跟媽媽一起巡視房間,步伐穩健,表達自信,根本就不肯交代自己自殺後的事情,而是做一個出發前的轉機。
影片在這裡呈現,似乎不是因為生病,傑西不能出去工作選擇家務,但她可以把工作做好,她有完全的控制權。
她選擇自己能控制的東西,不是房子外面的世界,而是家務,好像她要選擇死亡。
04 家務,河床上的母女關系
傑西告訴母親自殺後她應該怎麼做
這一夜母女在家務活中來到我身邊,呈現出多年來母女關系的縮影。
影片中家務的設計大多涉及母女,角色非常明确。
做家務的母親,看起來更像是一個頑皮的孩子:
從市場回來後,把袋子和鞋子扔下來,迫不及待地想去櫥櫃翻找糖果,糖吞下一個粉紅色的球狀零食,椰子絲屑掉在地上,傑西想過來跟她說話,她已經消失了,傑西默默地收拾了地上的食物殘渣, 然後去接媽媽剛丢了鞋子和包。
在卧室裡,媽媽脫掉了衣服,摘下了眼鏡、項鍊、用過的紙巾都留得到處都是,像個被寵壞的小女孩,不用擔心整潔,會有母親或仆人來收拾,當然,在這部電影裡,是傑西把一切都收拾幹淨了。
在花園裡,母親找不到園藝手套,像個孩子一樣問浣熊是不是拿走了它們,傑西把幹淨的手套遞給她。媽媽在廚房、衛生間裡什麼都顯得一無所知,不知道肥皂是拿去哪裡洗衣服的,做飯的鍋也沒關系,扔垃圾的時候也需要女兒提醒。
顯然,在生活中,傑西是母親,塞爾瑪是女兒。
最後,當她的母親無奈地自殺時,傑西低聲對她說:"如果有人要問我為什麼這樣做,你說你不知道......"
一個母親,就像一個即将獨自一人在家的孩子,充滿了對被抛棄的恐懼,因為她可以通過母親的安慰來承受即将到來的孤獨。
這時,母女關系颠倒過來,不僅展現在做家務的現實中,也完全暴露在情感關系中。
這一刻是展現傑西内心的時刻,她不是一個陌生的人,她是一個強大的弱者,能給别人安慰,也是自己無力應對的堅持,她終于做出了自己的意志選擇——
離開家務,離開母親。
05 做家務,才是真正的生存情境
"我覺得我被剝削了。
傑西的行為特征在電影中呈現,部分符合抑郁症患者的症狀:抑郁症,低自尊抑郁症,悲觀主義,自殺企圖或行為......
在我看來,這部電影更明确的讨論集中在母女關系和"意志"和"選擇"的哲學命題上,但電影的導演在傑西這個角色的設定中将他定位為一個抑郁的人。隻是創作者選擇不打破這一點點選擇,選擇從頭到尾保持沉默。
是以在劇中,傑西的抑郁變成了房間裡的大象,淹沒在生活的瑣事中,就連相處融洽的母親也對真相視而不見,選擇無視女兒的真實感受。
這與抑郁症患者面臨的現實不被了解的現實,形成了一種反思。有多少精神障礙患者直到生命盡頭才得到家人的了解。
在鄰居和親戚眼裡,傑西是一個奇怪的人。
這兩種視角都隻是他們想看到的傑西,也不是真正的傑西。
真正的傑西需要日複一日地完成家務勞動,看看生命之流之下。
我們隻看過一次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
在擦除過濾器之前,
看到它的樣子,
有機會承認,改變。
(完整)
"情感寫作機智"#影評#
作者注:
第一稿最初于2019年10月10日釋出,第二稿于2020年4月4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