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1級"pgc-h-right-arrow">廣泛的翻新曲調</h1>
< h1級"pgc-h-right-arrow"> - 為"北路鑷子音樂"前奏曲</h1>
<h1級"pgc-h-right-arrow"的>寒意</h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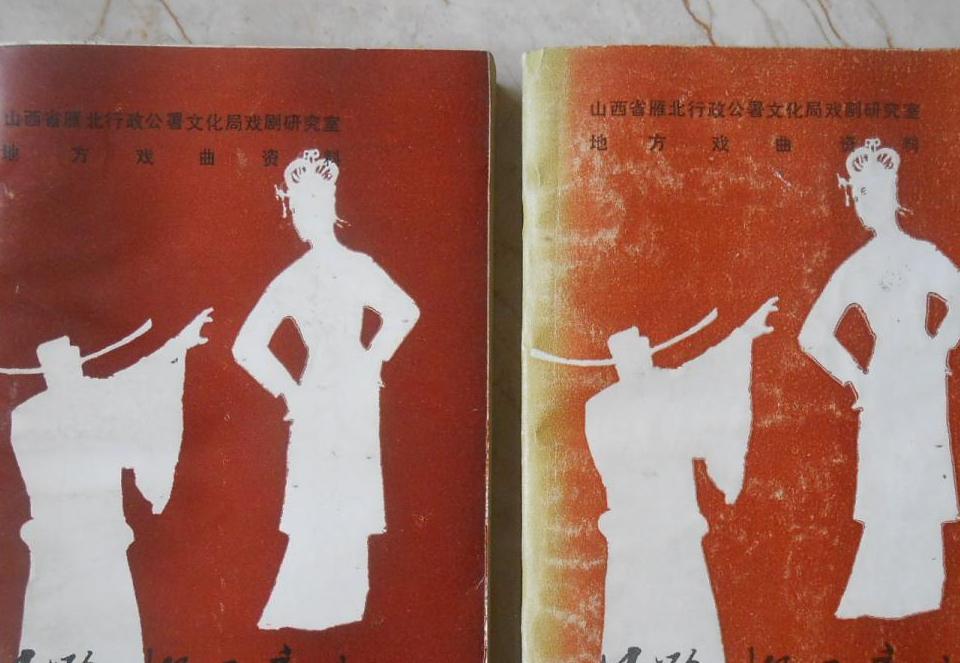
王澤民同志自1964年資訊積累以來,于1982年5月收集編纂了一部《北路騾子音樂》,曆時19年曲折。山西有北路、中路、上黨、浦州四頭騾子,它們與陝西的通州騾子、秦腔以及其他省區有騾子,同樣,都是從山地、陝西、琵三角地區的"山山子子"演變而分化。北路鑷子隻是鑷子大家族的一個分支,但它們在鑷子聲腔的流派中占有重要地位。
衆所周知,中國戲曲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南宋時期的"南戲"和金元時期的"北方戲劇"。當時,歌劇的音樂結構,無論是北方還是南方,都是宮廷曲調的一種插曲。上揚、音色、音樂結構、旋律特征、線條關系和曲調源都非常複雜。既有宮廷歌曲、法式歌曲、鼓、宮曲、文學歌曲,也有各民族和地區的民歌,而且從一開始就是男女同調,沒有性别之間的分歧。進入明代,元戲劇衰落,傳奇戲劇興起,戲曲音樂逐漸實施南北音樂設定和借用宮廷音樂等大膽創新,包括衛良福在昆曲聖蛻變身後,戲曲音樂一直以音樂會體的形式出現在舞台上,戲劇活動到此, 仍然高于社會上層。元朝末期和明朝初期,來自中國北方和南方各地的藝術家,以元劇和南劇的舞台藝術經驗為靈感,用當地民歌、說唱、歌舞等民間藝術形式,開創了勞動群衆可以了解和欣賞的戲劇, 如此豐富多彩的民間歌劇應運而生。藝子劇的前身,山山地區的兩句話"土劇",也是在這一時期問世的,當然也是很原始、庸俗的。從鑷子的角度來看,其實還處于潛伏期,沒有受到上層階級的重視。對中葉嘉靖、萬曆年、社會生活相對穩定、大江南北工商業發展、城市人口增長、勞動群衆對文化生活有較大要求。民間戲劇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逐漸形成了各種初步的"區域"音腔,并在社群中嶄露頭角,充滿活力,各有所顯現。由于當時的曆史和社會原因,也因為上層社會一向重視聲樂戲的習慣力量,曆史記載了南方聲腔的興起。除了最有影響力的海鹽、餘姚、濮陽、昆山四大腔體比賽外,還由魏良福等人加工整理,形成了後來的"水磨坊空腔"昆曲,成為上層社會推廣的一部時髦的"雅部"戲曲,當時時尚時有惠州、穎黃、青陽、四平、樂平、濮陽、義烏等空腔。在北方,有西方的鋼琴(即鋼琴)腔,鋼琴腔和各種當地民歌和戲劇相繼出現。雖然所有這些民歌劇仍然以民歌的作曲或演唱為藍本,但它适應了廣大的村鎮和村莊,迎接神社和下裡巴式的文化生活。至此,歌劇活動從上層社會到民間活動的廣泛活動,已經成為竹子等曆史潮流。随着上述各區域聲腔的形成,同時,以濮州、通州、陝西為中心,陝西、豫三角,以上兩句話結構為主的本土戲劇,也經過一段時間的孵化,以這一地區普遍活躍在民間的新态度。其特色是專業班活動比比皆是,如明家景年代冀縣龍王《重修音樂樓》在《濮州彜和班在本次演出》中的唱片。同期,還有臨沂的勝者班,永樂鎮的仁義班、餘氏班、浦州的永樂班、榮融的新班。據河津小亭村舞台牆介紹,當時新生班有八部戲(河南通州、陝西、河南有記錄,我們還沒有發現)。不管當時叫土戲,還是渣滓,還是一直鑷子戲,總之,它似乎一直是形成初期的"杉山子子",也是今天祐子家族的祖先。山山渝地區,素有中國文化的搖籃之稱。僅從北方戲曲的角度來看,北宋說唱家澤州孔三傳記創作了宮廷曲調的藝術,在此基礎上,晉元時期以平陽為中心創作了元劇,之後元劇進入首都,形成了最初的中國戲曲。從那時起,唱歌和跳舞,旋律和松散的音樂活動在該地區很受歡迎。從目前發現的大量地上戲曲文物來看,這片地區宋、元時期的音樂建築、舞廳、舞台很多。在金元時期,連旋律也被做成陶器,作為喪葬系統,這在當時這個地區的盛行風中可以看到。《花代筆記》如《金源》中戲莫勝,編纂的實名閻,即演員,也是紅朔的男人。"學者們從歌曲中汲取了戲劇的發展,自然趨向于優雅,為廣大勞工難以領略。這一地區,民間藝術也豐富,尤其是當地民歌舞、北方鼓詞和"寶卷"的奇異分支的"宣傳書"。民間叙事說唱藝術和木偶劇,這一領域頗受歡迎,這是兩句話音樂結構的出現鑷子,具有客觀條件。民間藝術家學習舞台藝術的戲劇體驗,使兩句話叙事詩說唱藝術和木偶戲在舞台上表演非常友善。全國各地各種新奇的民間歌劇也利用各種條件,在地區之間傳播和影響。比如昆曲、濮陽空、青陽空等國外劇,當時在山西,尤其是晉南、晉東南地區也相當活躍,它們對劇團的成長有一定的影響,客觀上也有一定的影響。這些都是流行的鑷子可以快速增長的重要原因。從清初康熙中葉到乾隆時期,可能是該劇藝術初功成的時期。康熙46元宵節、著名劇作家孔善仁在劇中《平陽竹枝話》中,有"邋遢的一次薄翠華看"和"最愛葵華小步"的贊美詞,至少要說明,當時該劇不僅有自己的名字,而且在民劇的情況下受到歧視, 可以讓康熙皇帝看到表演,為自己的合法生存權而戰。到了乾隆王朝,騾子炸彈已經遠遠地走出了杉杉寇三角,作為花劇的骨幹,在花藝競賽中,可以與以磨水腔昆曲為代表的亞辛劇展開競争。在那之後,可是一百年後,按照同樣的規律,光緒年,該劇居然進入了它的第一個黃金時代。下面也提到了這一點,這裡不再贅述。叙事詩說唱藝術,追溯到上下兩句話的結構,在我國有着悠久的傳統,遠離秦和漢樂夫,如《上坡》、《十五從軍》、《孔雀東南飛》等叙事詩,也就是為兩句話結構的叙事歌唱藝術奠定了基礎。直到六朝,這種詩句都是五字上下。四川彭山等地發掘出的漢代擁抱鼓說唱,很可能是這種民間叙事詩說唱藝術。此後,曆代統治者雖然廢除了民間文藝體系,但這種叙事詩歌唱藝術形式在民間已經流行起來,并得到了發展。到了唐代,從五字型演變成七字叙事的"文字文字",增加了七字說唱本體的"變奏",宋代之後出現了說唱體《桃真》和《寶卷》,到北方流行變種的"鼓詞"和南方的"子彈字",也是兩句話一句話說唱藝術的繼承和發展, 但風格從七個字演變成"交叉句"而已。這種說唱形式也被木偶劇所吸收,成為一些木偶戲的人聲結構。在杉山琵三角,很自然地受到長安、洛陽和魯良等古老文化的啟發。從戲曲上看,除了北宋、金元劇、松散的音樂影響外,這裡,"吊猴"和"布袋猴"等民間木偶戲和皮影劇音腔結構也是兩句話。我認為在這個地區産生鑷子的胚胎,地球戲劇,很可能是通過木偶,陰影和其他木偶戲的橋梁角色進化而來的。因為這個領域的木偶戲不僅模仿了盛唐、北歌舞和金元劇,松散的音樂條件,而且是一套木偶戲所用的兩句話聲樂藝術。隻要改變一種方式,用"人"來表演,就是一種新的歌劇形式。兩句話的聲腔藝術可以吸收旋律劇和木偶劇音樂早期的闆結構,并有大量的兩句話木偶劇和說唱曲目,便于移植。當你熟悉它時,成為一個易于了解的"地球遊戲"也是合乎邏輯的。福山木偶師王少宇曾經說過:"大戲不大,小戲不小,小戲是大戲的祖先。"所謂"小戲",就是當地的"吊猴"、"布袋猴"、"皮影戲"等各類木偶戲,也就是鑷子戲,這個傳說也是一個值得一看的例子。從"土戲"到"鑷子戲",對于聲腔藝術中藝術實踐的演變仍然是必要的。除了接受"結合"戲劇和打鼓、好書等說唱音樂中間,慢、快、散、堆疊等音樂節奏和速度的變化,逐漸形成自己的一套原創闆、慢闆、二進制性、導引闆、松闆、托盤闆、快闆、滾白等歌唱腔體風格, 這種歌唱腔的風格,也自然而然地符合方言、嗓音和民間音樂的特點,使其融入了本地區民間歌唱藝術中習慣性的高音、調性、旋律性音色關系,在長期演唱中創造自己的聲樂個性。在這個空腔創造的過程中,鑷子戲劇形成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對歌唱腔中"讓闆"的體驗的總結和規範。也就是說,歌手不能在騾子上唱歌,必須讓騾子打開才能打開,稱為"眼闆掉落"。更具體地說,就是慢三隻眼睛向中間睜開眼睛,一眼一眼睜開一個盤子,半拍後有一個無眼的盤子。因為當時的民間藝術家沒有文化,學習唱歌并不靠樂譜,一直采用口頭傳播的方法。是以,"讓闆"在歌手中開口,是一個大問題。然而,從闆的節奏變化到作曲結構,實踐證明,歌手采用"讓闆"為指導,對于闆的轉換,來回,都非常有益,可以無縫處理。為了解決演員唱歌和掌握"舷外"的問題,為了掌握節奏大小,必須有一批比"隔闆"更響亮的節拍樂器。這就是"土方遊戲"中"鑷子"的用法。藝術家對于掌握"讓闆"節奏的能力,看得很重要,是以一直被形容為"鑷子"為"太行山"。闆的大小是否準确,取決于它能否穿越"太行山"這個難度。"杉山土戲"達到了這個水準,聲腔藝術有了質的變化。根據舞台文藝和國術聲音的突出印象,群衆對這部新聲劇有了一個流行而合理的名稱,稱為"祽子劇"或"山山子子"。鑷子形成的另一個特點是,在選擇音樂伴奏和樂器方面沒有舊的方式可走。去過協奏曲的戲劇,多以長笛伴奏為主,或者到歌唱腔,或者弦樂繩演奏音樂。根據杉山峪地區勞動人民的胃口,大量使用當地民間樂器。最突出的是采用弓弦樂器胡琴為主要樂器,然後逐漸形成了一把虎锖、二弦、三弦、四弦(月亮琴),被稱為弦樂四件。然而,從鑷子弦的演變來看,第二根弦實際上從主要管弦樂的地位中退卻了。同時,根據戲劇藝術的需要,讓民間倡導者樂娜搬上舞台,烘烤氣氛。這些樂器演奏的音樂,不僅吸收了協奏曲戲劇的音樂,還大膽地運用了與民間絲綢琴弦卡和卡息息相關的人的作品。還把蜻蜓、馬鑼、鉸孔、手鑼等當地民間色彩的打擊樂運用在舞台劇中,根據劇情的需要和劇的成長過程,逐漸形成了一套特殊的"鑼鼓"。在統治階級和上層階級神職人員眼中,這些确實是偉大殿堂裡沒有的東西。也就是說,就虎琴而言,從唐代一根竹片之間用兩根琴弦摩擦琴弦的發音,演變成後來的馬尾胡琴,在耶魯宮廷中一直沒有它的地位。然而,新民歌《杉杉子子》以它為主奏樂器,民間藝術家娴熟的演奏技巧,聽到了群衆的号召。如清乾隆時期吳太初的《燕蘭小譜》說:"朋友說,新鋼琴腔......它的樂器不用長笛,以胡琴為主,月亮鋼琴付了,尺子就像一個字。"這是《杉杉子子》歌劇史上的又一大創新。"杉杉子子"到青乾隆,嘉慶時期,已經很成熟,很活躍。如前所述,它大舉跳出了杉杉餘三角,在華北各地展開競争,甚至從西夷等地向南延伸,最終使整個子彈成為南方大脈絡。它開始在北京對山藥昆曲産生影響,形成了花彈和山藥昆曲的争議。當然,所謂的花,并不全是鑷子,它是當時民間歌劇的總稱。也就是說,以乾隆吳太初在北京花藝部44段的《燕蘭小譜》進行分析,包括當時12班的規模,來自12個省27縣的演員,證明了花戲的藝術形式相當複雜,即使是一個班級或同一個演員,同時也能掌握幾種演唱形式, 這部劇的界限,沒有現在那麼嚴格。然而,鑷子無論如何都是開花藝術中的主要力量。以四川魏長生為例,據了解,他既唱爆彈,也主要攻擊炸彈。乾隆56年進入北京班"雙清部",當時班不景氣,但魏長生敢說:"讓我進班兩個月不漲價為王,願受懲罰無悔。然後他唱起了《滾塔》的一出戲,而且确實是首都的名字,觀衆人數達到千人,讓其他六個班,突然降色,雙青躍入一等班。後來,他的徒弟陳一納演了一出戲《火》,也是藍。濮州的薛思爾,一時聞名的西丹之最,太原的張連官,陝西的三壽官滿東,以及河南張雪兒、河北的圍棋晚祔等人,也是一瞬間地震的騾子炸彈。
正是因為新戲劇藝術吸引了大批觀衆,是以,即便是當時的亞藝演員,如吳大寶、石玉清、張發正、鄭寨星等,也都學會了玩騾子。包河部原本是一個優雅的團隊,為了赢得觀衆,不得不兼顧炸彈和國術,然後将包河部分為兩部分。燕蘭小譜是"列在正午極限",正午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以上事實說明了19世紀70年代開花究的影響,也說明了基于"兩句話"音樂結構的歌劇聲腔藝術充滿活力的藝術活力和廣闊的群衆基礎。這一時期,《杉山榆子》在晉中和金杯成立了社團,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教學戲劇必須邀請濮州或同一國家教師。設立分班,招收蒲州,同州娃娃為最佳政策。在舞台上必須讀"普白"并唱"普白",以保持與鑷子演奏地的藝術風格的統一。
吳成仁同志在五台縣餘音村西段闆分區上記錄了"大慶嘉慶23日集集、太原縣、太原縣五寨縣、東寨村自成一體的班級"的一面戲牆,據我分析,實際上屬于"杉山玉子"在各個部位的班級期間表現。這一時期所謂山山木子、山西伊子、秦腔等名稱都不同,其實是一種好幾個稱号。在劇作和演戲上最初的一些區域性類型差異,因為白色、歌聲口音濮州、同一狀态的這個三角形聲音等藝術規範,類型之間的差異不大,很容易互相串聯。八十年前的清末,"山山子子"如火如荼,足迹遍布華北和西北部分地區,東北橫跨哈爾濱到伯利和南大上海,都享有很高的聲譽。當時,北京有五大劇院公園,前門有"華樂"、"廣和"、"中性"、"三清",都是恪子劇的主要活動,隻有城市的"吉祥"才是平劇的堅實位置。北京戲劇班培養人才,直到富蓮城藩藩梅蘭芳這一班的培養,還由平劇老師和平劇老師授課。清末,直到民初,才有一大批知名的優秀演員,如侯俊山(13天)、郭寶辰(袁子紅)、油餅丹(西來風)、劉丹、石靈芝、毛毛丹,以及13天徒弟,第一位女演員劉錫奎,都是藍。譚新培是當時著名的平劇,但隻要劉錫奎上市,譚新培就不演了。有時梅蘭芳、譚新培、劉希奎在同一舞台上表演,劉希奎唱壓力軸奏。所有這些都标志着鑷子的黃金時代。這裡用幾句話來辨別小插曲的劃分鑷子劇,也就是以十三天(後君山)的名字為例。有人說他出生在晉南洪東縣周壁村,說自己是浦劇演員,也有人說他九歲就進入太原的一個分支學習藝術,作品是急子劇《花丹》,以為他是山西中路子子的演員,還有人強調他是一個時期在金杯鄉和張家口演完戲後, 甚至在堆箱之後,他回到金杯教戲,也就是在山西北路當演員,一開始有人以為他是張家口的演員,經常是在北京附近成名後,晚年定居下來的,也就是從河北省來的演員也曾被人稱為秦腔。解放前,是以人們認為他也可能是秦腔演員。這似乎有點像希臘史詩歌手荷馬的傳說。荷馬晚年在包括雅典在内的八個主要城市輪流演出,使他因出版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而聞名。結果,八大城市争相說他是荷馬的故鄉。其實,這一時期的"山山木子",甚至在山西,還沒有發展成一種清晰的四種鑷子,包括變化較早、規模較大的上部宮廷曲調,基本上都是姗姗姗來遲的镂子。這一時期的一部電影《維克多唱片》至今仍稱其為《杉杉子子》。十三天這樣可以在各個地方玩,就是要說明單山木子的特點還沒有完全分裂,更不用說,比如十三天出生地的問題,還是有異議的。
該劇不是按照明清時期的行政管轄制作的,而是由說服書、說唱音樂、木偶劇的兩句話音腔結構,結合山山語三角方言聲音的"音片"關系而形成的。随着其類别的增長和流媒體布料範圍的擴大,它也将根據新活動區域的"色調膜"區域進行同化。原山西晉南與陝西關中地區與河南陝西、靈寶地區有着悠久的曆史,有着共同的隸屬關系和地理、交通便利性,使這片大片地區的方言聲音、民俗、人民的生活習慣,形成了幾乎相同的特征,是以在這個地區的人民中形成了共同最愛和新穎獨特的兩句話《杉山戲》和《玉子戲》。起初,這部戲的名字,沒有署名行政區劃,正是這個領域的勞動群衆自己欣賞民間戲曲藝術,它在上層階級眼中并不高,是以一開始就有"大地戲不能尊重上帝"等說法。
戲劇藝術的魔力不是由封建統治階級的意志轉移過來的,如果觀衆歡迎它,階級就會成長,把河湖跑得遠,各地階級隻根據班長的地域名稱的地名,像國騾子、普州騾子,實際隔江而過, 還是一種形式,就連修煉者也是兩個種花去的地方。任何聲腔藝術,當它離開産生它的土壤時,長期傳播到田間,總是受到新的"音膜"區域的同化或變化,這是"音膜"法則限制的另一種表達形式。例如,武安路子向上黨區蔓延生根開花,按照上黨區人民的要求,逐漸成為上黨下台;《山山子子》傳遍山西、晉中、上海、金杯地區方言聲音、民俗風情、民間音樂特點和群衆欣賞的習慣形成的有聲電影的特點,不僅與晉南不同,而且彼此不同。是以,《杉杉子子》在這些領域的音色和彩色電影逐漸同化,開始形成上路音、中路音、下路音(或南路音、西省演奏)和上部黨、國家調等區域流派。特别是辛亥革命後,打破了封建王朝長期以來對民歌的禁令,資産階級的改進之風正在蓬勃發展,各種封建幫派習慣的破産,也影響了濮州,同一國家用藝術家統治舞台的行業習慣,取而代之的是來自各個"音片"地區的本土演員, 雖然也講究白、歌唱雙關語,在聲腔的藝術中,其實是按照自己的"音膜"區域特點進行熔化或同化,也可以說,所有區域都是自發地對鑷子音腔進行轉化。
"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了歌劇界,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鑷子的舞台上也出現了"文明戲劇"(即時尚劇)。昆玉舞台表演,逐年增加,男女同台演出,也促進了地區學校分工的急劇分裂,使他們迅速融入各種獨立的英語劇場。北路鑷子也是從這條路演變而來的。由于上路轉學學校依然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正是在群衆中從上路到北路騾子的真名,也是抗日戰争和解放前後。北路聲腔的藝術,由單山一子上路音色的演變而形成,在花腔的發展和樂卡的使用上具有自己鮮明的特點。滬琴适應了它的高處,也跟中路、普戲不同。當它的音樂個性建立時,它也與其聲音和彩色電影的範圍有關。"音調膠片"有一些局限性。在路曲或北路騾子上,最早活躍在十陵關,在泸縣、陽渠之間,直至内蒙古的標頭湖城。偶爾也去張岐東口,但不是其主流布範圍。這種聲樂藝術,既是戲劇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個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近四五十年來又形成了大北路、小北路兩大流派。這裡所謂大小北路,據了解,沒有貶義,所謂"大北",指的是"北北"的意思,"小北"指的是"近北"。北至内蒙古威猛關,以王玉山(水漂)為代表的大北路聲腔,其特點以音腔音音深洞察,南臨門,以賈桂林(小電燈)為代表的北路小聲腔,使腔體活潑華麗, 委婉而溫柔,兩大流派确實有自己的秋天。另外,河北烏爾州也是一種流派,在戲路有些不同,音腔其實并沒有形成獨特的風格。
王澤民同志收集唱片編纂了北路騾子的音樂,以北路歌唱腔的大小為包容,胸懷開闊,同時也以崇尚音樂的著名音樂家胡錦泉等同志獨特的北路鑷子演奏音樂,也包括在内。全書分為六章50節,其中隻有一張文學音樂卡,共七卷絲串卡,163張;各體裁時演唱樣本摘錄并完整演唱選段,包括王玉山、賈桂林、高玉貴、孔麗珍、二風(姓名)、周成貴、宋玉芬、劉明山、李鼎官、郭占軒、安冰琪、劉正芳、達丹(姓名)等著名演員可以收集歌聲和胡金泉戲劇演奏,共二十段。這本書将近三千字,雖然不完美,但确實是拯救和記錄北路音樂的重要書籍。這本書的出版,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我對這本書的初稿内部印刷感到高興,也為王澤民同志的藝術作品緻敬,因為他在北路的彜子聲腔藝術,提供了豐富的音樂基礎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