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彭姗姗實習生 嚴宏儒
《中國古代禮儀集》是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于1990年至2014年間發表的研究論文集。在他的學生時代,"禮貌"曾經是一個被遺棄的命題,與今天的"熱"完全不同。而在新的時空背景下重新探索禮儀,正是他"摘花"的目的。
楊志剛生于1962年,畢業于複旦大學曆史系大學到博士,1987年任文物博物館系主任,曆任文物博物館司司長、文理系主任、文化史研究所所長、 2014年調到上海博物館,擔任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重點研究基地主任、《文物與考古科學》主編。在他看來,禮儀是中國傳統研究的廣闊和根深蒂固的内容,同時埋藏探索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間的關系,無法回避"硬核"問題;"我們可以忽略它,甚至試圖避免它,但在曆史的某個時刻,問題将再次出現。一旦提出,它就令人興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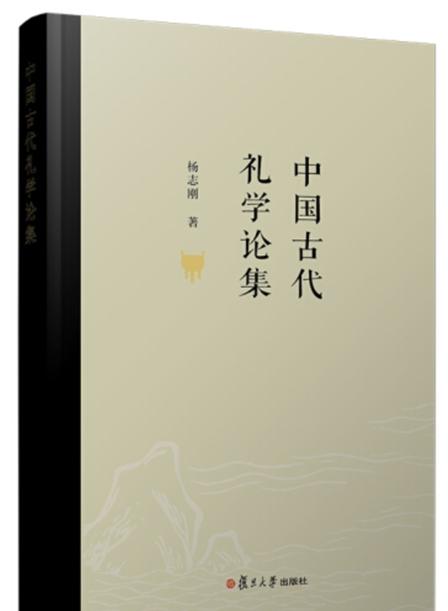
《中國古代禮儀集》,楊志剛著,複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3月
新聞:近十二年來傳統文化的"回歸"引起了廣泛關注,您最近出版的《中國古代禮儀集》的起源是否相關?
楊志剛:"中國古代禮儀集"可以說是"摘花"——這本集子的第一篇文章發表于1990年,至今已跨越30多年。現在"撿起來"的意思是,在這個命題的背後,我仍然關心的是,通俗地說,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雖然這個話題的重要性沒有改變,但寫作背景、關注的焦點也在不斷變化,我們也在思考禮儀的具體問題也在不斷深化。特别是社會生活本身經曆了許多變化,這種研究與社會生活密切相關。
當我在1980年代開始研究時,中國還沒有完全從知識體系的斷裂中恢複過來。有很長一段時間,"禮節""禮"被當成渣滓和枷鎖,《朱子家禮》這樣一本書沒人問過。20世紀下半葉,對朱子嘉的研究首先在中國大陸之外進行;當時,普通公民、媒體、知識界,甚至國家上司人對傳統文化的了解都與現在不同。傳統曾經被視為"對立面",但在過去的40年裡,物質文化和意識形态都經曆了"驚天動地"的變化。這些都是我在編寫本集時需要注意的事情。
新聞:1985年,你的碩士論文被選為"禮物",這是你學習中國古代禮儀的開始。正如你所說,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中,"禮貌"的話題不是主流,你怎麼看?
楊志剛:在複旦學習期間,我有機會接觸到一些新的想法和想法。我們離當時的一些頂尖學者不遠。比如李澤厚先生去研究所學生宿舍跟我們說話。美國曆史學家弗雷德裡克·埃文斯·韋克曼(Frederic Evans Wakeman)喜歡和年輕的學習者聊天。魏飛德知道,當時的中國人普遍認為傳統文化壓制了中國的現代化,是以"罪孽深重",如巴金的《故鄉》《春秋》和曹瑜的《雷雨》都展現了批判的"老禮儀"和"老文化"。魏飛德在和我們聊天時舉了一個非常生動的例子,他說,現在大家都認為英國文化是"現代的",其實兩三百年前并不是今天"溫柔"的外表,而是一個"勇敢兇猛"的民族。但在這兩三百年裡,文化發生了變化。我們可能認為文化是繼承的、不變的,但魏菲爾德認為文化就像一條火車軌道,軌道上有一個可以觸發的觸發器。文化的發展還需要在"軌道"上找到一個"觸發點",之後的發展方向可以改變。是以,可以創造新的文化。我們為什麼要學習傳統?除了探索曆史真相,我也希望進一步反思過去、現在和未來,讓學習能提供更多對社會的洞察。在開辟新視野之後,我們也有望實作傳統文化的"創新轉型"。
新聞:現在"禮貌"重新回到聚光燈下,你認為它的原因是什麼?
楊志剛:我認為"禮貌"是一個"硬核問題",雖然在某一時刻可能不引起注意,甚至故意模糊,但實際上一直存在。當周圍環境發生變化,或者對這方面的意識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它就會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
像朱子家禮,以及其他中國古代禮儀,都為人們的行為提供了一套"儀式",沒有它,就很難說話和社交。這些作品也反映了當時的人們如何生活,如何以社會接受的方式生活。但近代以來,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在很多領域都發展了新的禮儀,但還遠遠不夠。于是有人感歎,缺乏"禮貌"導緻"進退不知所措"。我認為生活的許多方面,如婚姻與喪親之痛,飲食與生活,灑水等等,很多内容都應該重新組合。但這隻是膚淺的,而不是根深蒂固的。我們應該看到的是溝通過程中缺乏規則和規則。
然而,僅僅依靠古老的"禮貌"是不夠的,它應該被用作一種資源,然後融入現代生活的公認規範中。這樣的工作也需要更多的人參與進來。
朱子家禮
新聞:你指出,"朱子家禮"在宋代以後逐漸成為"民間大禮"。"朱子家禮"是在什麼樣的社會背景下,也就是說,社會發展到什麼階段,一般群眾的家庭生活需要"朱子家禮"?
楊志剛:唐歌時代是多變的時代,這種變化在各個方面都是如此。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當時人們的思想和意識與唐代相比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朱覺得"三道"中的古儀式不再适用,是以他想更新和改進它。另一方面,它深受道教和佛教的影響。包括司馬光在内的人也感歎,這已經不再是一種傳統的生活方式了。他們感覺到了變化,是以他們不得不重新制定規則。規則不是複古的,而是遵循一些古老的形式,并且有許多創新。比如,祖先崇拜的功能在本質上并沒有改變,甚至通過朱琦等人的努力,對近代祖先的崇拜對人和家庭行為都變得更加限制。是以在那個瞬息萬變的時代,朱琦用一些古老的形式來表達自己對現在和未來的了解。朱還把社會生活中發生的變化融入到書中,表達了自己對理想人生的了解。
但我認為我們現在需要的肯定不是像朱子家這樣的書。我在書中提到了一些中國古代人對禮儀的看法,如果你今天研究它們,你會發現"禮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我們仍然應該有選擇地将它融入我們的新生活中。
新聞:你還提到,現在我們是"古代禮儀"的追求,比如穿中國服裝、敬禮等,你怎麼看這些現象?
楊志剛:我注意到了這些現象,但我沒有評論它們,比如這些服裝的美麗和醜陋等等。但我認為在這種趨勢下,我們可以抓住一些問題。我不會評論漢裝好看與否,是否符合古籍所描述的風格。但我們可以看到,與30年前不同,傳統與現在"明确分離",它們已經融合在一起。我們已經走出了僵化的思想境地,有了更多的智慧。
也有人在學習和研究朱子家禮,希望能把這套文字記錄的規則原封不動地還原下來。我認為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們可以在不妨礙他人的情況下做到這一點。但是,如果這是前進的道路,我不同意。雖然我對重振格利并不熱衷,但我會把重點放在這些有趣的現象上。在現代社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愛好,如果都遵循公民社會的規則,那是一件好事。我認為,現在将傳統與民間社會的規範相結合,并在社會允許的範圍内發展自己的個人偏好,這并沒有錯。
新聞:在你的書中,你指出這種行為的普遍存在可能是由于對身份的追求。您認為學者和學者應該如何回應這種追求?
楊志剛:我認為學者們應該首先反思價值觀,然後敢于尋找新的可能性。通過這種努力,我們的生活空間确實開放了,這絕對比30或40年前更加開放和豐富。
或者超越"複古",開拓探索。我認為有兩個重要的概念,首先是"文明互鑒",提取全人類最好的東西,走到一起,互相學習。第二個概念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需要在這個共同體上找到人類共同的善良和美麗。例如,我反對"完全複古",把"小鞋子"放在展廳裡,但今天提倡抓腳是倒退了一步。是以我認為首先要做的是專注于價值觀,然後探索可能性。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提到,明清兩代"朱子家"在各個地方的交流和普及差異,比如在福建有很大的影響力,而它屬于江南地區的蘇、浙、上海地區的影響也不同,您認為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是什麼?
楊志剛:粗略地說,這與中國古代的家庭制度有關。在福建,家庭制度非常發達,婚姻喪親和家庭制度是互相制約的,我們常說,福建人再家庭,重家庭。朱子家裡的影響也與朱琦本人的傳播密切相關,比如朱琦出生并活躍于福建,祖籍在惠州、燕西,是以這兩個地方都受到了朱琦思想的極大影響。
新聞:《菊子集》在整個東亞地區有很大的影響力,你考察了《菊子集》在南韓的傳播和影響,指出它"在當代南韓社會并不死"。您認為朱子嘉在當代東亞社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力?
楊志剛:對書的影響有兩種。首先是中國東南沿海漂洋過海将這種禮儀帶到國外,這就是"人類傳播"。二是"文學的傳播",即《朱子家》這本書和朱琦的其他作品,傳播到海外。在宋明時期,南韓和日本接受了許多中國文化。
朱子璇的正統稱李朝持續了五六百年,這使得南韓成為一個非常典型的儒家國家。以朱子家為核心的禮儀在南韓曆史上有着深遠的影響,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今仍留下深深的烙印,如他們的冠禮教育(即成人禮)、喪葬制度等。我對朱子嘉利在南韓的影響很感興趣,但它主要基于文學,沒有人類學的深入調查,有機會這樣做會很有趣。
2009年在南韓與"菊家禮"研究人員一起參觀了桃山書院,第一排右三是楊志剛
新聞:你在書中還提到,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古籍部咨詢郭偉《朱子家麗》青光緒17年镌刻。在那個變遷的時代,一個開眼界、體驗西方文化的晚清,為什麼要去修改朱子的家禮呢?你不在書中,你能在這裡談談嗎?
楊志剛:我想我們可以從郭偉濤身上看到某種時代的悲傷。郭瓦索是英國第一任使節,當時沒人想擔任這個職位,因為很多人對外交事務輕蔑。有人認為,如果一個人一年四季都與外國人接觸,出國多次可能是"美"的。我覺得郭衛濤自己也是沖突的,時代的局限造成了時代的悲哀,個人在時代面前會感到自己的渺小。像郭偉濤這樣的聰明人,見過很多問題,卻找不到更好的解決方案。别人不了解他,是以他選擇做他的學業。郭偉的選擇并不多,但當時,與國内外古今豐富的學術資源不同,他隻能學習自己能讀的書中最有趣的内容。于是他看了《菊子家事》,并進行了修改。
郭偉
新聞:你也參觀了全國各地的寺廟。近代中國孔廟的命運可謂起起伏伏,您認為今天的中國孔廟是什麼樣的空間?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和利用這個空間?
楊志剛:我大概查了全國一半以上的孔廟。這是一個正在改變的空間,孔廟裡還沒有多少人用來祭祀孔福子,但有一個增長的趨勢。一些寺廟是"現場展示",在那裡組織祭祀活動。有些已被改建為博物館展廳或其他開放空間。在我的調查中,我發現有人會在聯考前在孔廟舉行活動。我擔心孔廟對空間的利用,但其實我最想通過孔寺找到的是一種中國文化的"底色"。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寺廟儲存完好,有些不完整,有些隻是翻新的建築。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看到中國文化的"底色",找到合适的文化方向。
曲阜公廟 丹頓寺
負責編輯:韓少華
校對: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