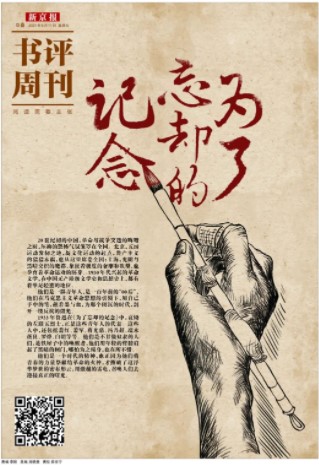
《新京報書評周刊》特刊"為記憶遺忘"。
亂葬坑上的活人為死者挖洞......墓地是一座死城,沒有花,沒有蟲子,即使有花,即使有蟲子,也就是唱着告别歌,伴随着無盡的死寂永久寂寞。
墳墓是地主在貧窮的農民死後給予他們的家園。但是,經常被地主驅逐的活着的農民,背着他們的包,帶着他們的孩子,從破房子到破舊的房子裡。有時他們被帶到馬廄裡睡覺。孩子們在馬廄裡對着他們的母親哭泣。
蕭紅的生死場
1935年,在左翼思想興起的上海,一套包含葉紫短篇小說集《收獲》、蕭軍小說《八月村》和蕭紅小說《生死場》的"奴隸書"在空中飄揚,使蕭紅、蕭軍在上海文壇聲名鵲起。
此時,蕭的家鄉東北,四年前落入了日軍的蹄子之下。在上海,他們既是文學世界的入侵者,也是流亡者。對于當時的上海人來說,小說《第二蕭》除了街頭流行的抗日救援歌曲外,更是東北地區更深刻、更明顯的存在。
"高粱就像要倒置折疊,地球盡頭的桉樹正在呼嘯而起,有點像金屬的聲音,為原來的閃光,突然赤身裸體,突然又埋了下來。
《生死之地》中對風暴的這種描述,就像是小紅和蕭軍這兩個在東北大地長大的戀人的寓言。他們之間的束縛,就像這場風暴一樣,在光和電釋放之後,隻有"濕氣味籠罩着人們的頭頂",就像高粱中的"紅色夢"。
編寫|肖淑軒
蕭紅和蕭軍。
愛的萌芽
1932年夏天,蕭軍的"國際會"收到一封女讀者的求助信,說他被軟禁在哈爾濱路外的東興順飯店,因為幾百元的債務無法還清,酒店老闆打算把她賣到"環樓"妓院還清債務, 是以我希望報紙能幫助自己主持正義,把她從危險中拯救出來。
這封信寫得很凄美,在場的報社成員一動不動,編輯老宇(新源)立即與記者舒群等人一起找到了酒店,拜訪了信的讀者張納英,也就是"未來"小紅。蕭紅的實際情況比她在信中寫的還要糟糕,當時她懷孕了,被同居六個月的未婚夫留下,被酒店老闆劫持為人質,住在酒店角落裡一個又冷又潮濕的儲藏室裡,每天隻吃半碗高粱米飯。
知道小紅的處境,老人等人很生氣,也束手無策。直到三天後,蕭紅又寫了一遍,要了幾本文學書送别的時間,老人才讓恰好在附近的蕭軍去旅行。蕭軍回憶起第一次看到蕭紅的場景,幾乎目瞪口呆:"她隻穿了一件藍色的,現在顯得褪色的背心......小腿和腳都光秃秃的,一雙換好的女鞋被拉扯了。令我驚訝的是,她的頭髮中已經有明顯的白髮,在光線下閃爍著,然後她懷孕的身材,似乎很快就要接近出生日期了。"
如果說小紅此時這種悲傷的表象,激起了這種大男子主義,好好打拼參差不齊的蕭軍的無限同情,那麼她就散落在床上的文具上手寫的短詩,無聊的繪畫圖案,這提醒了蕭軍的溫柔愛情:"我想我的思想和感情也變了......出現在我面前的,是我見過的最美麗的女人!......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拯救她,,——!拯救這個美麗的靈魂!"
然而,蕭紅卻被蕭軍的驕傲所鼓舞,當他走進自己發黴的小屋時,他擡起了"隻有當有瘀傷的士兵相遇時才能感受到的喜悅"。對于當時的她來說,小軍是春天,是希望,是全靠。
第二天,蕭軍再次拜訪小紅,兩人在東興順酒店的小房間裡結婚,"所有的愛情之旅都已經結束了。"對于這樣一段風情,蕭軍事後的結論是'不尋常的相遇,平凡的組合!"
隻有小軍自己也登上了小編的家,"除了頭上幾個月沒剪頭發是多餘的",什麼都沒有,根本無法還清小紅的債務。他能做的就是每天走二十英裡去看望小紅,小紅的回報是一首又一首的情詩給他:"你的腰怎麼我擁抱,你的嘴唇怎麼吻,你不敢到我身邊去?詩人,你遲早能逃脫一個女人!"
初戀的日子持續了大半個月,但蕭紅的"入獄期"似乎永無止境。偏頗的是,今年8月,暴雨的日子讓松花江沖破了河岸,淹沒了馬路外的區域,東興順酒店老闆的所有家夥都逃走了,小紅才從她的房間溜了很久,騎着一艘路過的木船碰到了小軍登船的老家。蕭俊和蕭紅,終于在客廳裡老家有了夫妻第一位。
創作的開始
雖然虎口出門危險,但小紅和小軍的臉是可憐的夫妻百事可樂的哀悼——小紅差點出生,由于前一段時間的寒冷饑餓、脫發、頭痛來臨,因為付不起醫院費用,醫生和護士都冷眼看着她,"甚至一端"。蒼蠅也會虐待我",九月份出生的嬰兒也被醫院查獲,被毒品指控抵消,無法識别(據說還有小軍送的);他們甚至失去了他們倒下的客廳。
抱着唯一的行李,拖着虛弱的産後身體,小紅和小軍在哈爾濱商業街周圍找了幾次小屋。蕭俊以免費輔導和教授國術和中文為代價購買了住在這間小屋的權利。有了庇護,食物還是得不到保證,饑餓是這個時代永恒的主題,接下來的面包在他們眼前,"我怕面包,不是我要吃面包,怕面包把我吞下去"(小紅)。
有足夠的水。此時,他們的物質生活稀缺,但精神生活豐富。1932年底,國際協報社召開了新年征文活動,蕭洪在小軍身邊與朋友的鼓勵下開始寫小說,并于次年5月完成了第一部短片《王敖之死》。這部小說,出自小紅小時候目睹的低級農村農民生活,描寫了勤勞善良的寡婦王敖的悲慘命運。從此,農村底層勞動人民的生活幾乎成為小紅一生的創作主題。
除了寫作,蕭紅和蕭軍還經常與白朗、羅偉等共産黨員一起"拿牛房"進行秘密的抗日活動。他們在這裡印制抗日傳單,排練抗日劇,準備救災展覽。
小紅在被流放到東興順飯店之前,對文藝熱衷,曾與同學們結成"野素描俱樂部"作素描師,但也熱衷于"新文學",收集魯迅的《呐喊》和毛敦的《追尋》。在"牛屋"裡,她喜歡魚水,進步很快。曾經拉過"牛屋"的女主人袁世傑說:"女人要翻身,就必須站出來參加革命事業,不是給男人一根'文明棍',不是把男人當成'酒吧狗'。
這種在商業街25号生活的經曆,從此被小紅寫成自傳體散文集《商業街》。據美國漢學家葛浩文介紹,《商街》的文學價值被遠遠低估,而《小紅》一書中生活的"實質""往往通過紙面"。
同樣在市場街的這間小屋裡,小軍收到了《八月的鄉下》一書的寫作材料。在介紹書群之後,蕭軍遇到了中國共産黨的地下黨員傅天飛。918事件後,傅天飛和著名抗日将領楊景宇在吉林岩地區組建了中國第一支抗日遊擊隊。1933年春夏,傅天飛找到了淑群和蕭軍,并談起了一天一夜擴大岩石遊擊隊發展的過程,以防自己犧牲,還留下了兩份"腹稿"。在他的叙述基礎上,蕭軍完成了《八月村》,魯迅稱贊這是"反對日本侵略文學的旗幟"。
但購物中心的甯靜日子并沒有持續太久。"牛屋"的活動最終引起了滿洲國政府的注意,一名成員被捕,蕭軍和蕭紅的姓名和位址也被日本憲兵發現,他們隻能在1934年6月逃離哈爾濱到青島避難。但哈爾濱的白色恐怖再次延續到青島,但肇事者從日本侵略者變成了國民黨反動派,今年11月,第二蕭也不得不再次離家出走上海。
說再見,重聚
上海是蕭紅和蕭軍在文學界真正嶄露頭角的地方。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魯迅成為了自己的文學導師,和生活中的長輩一樣給予了兩個小蕭的關心和幫助。
魯迅一向對人嚴格,他與人密切接觸,除了《第二蕭》之外,很少有人不受其批評或批評。即使他們不了解這個世界,做傻事也不現實,魯迅卻處處關心,跟着好誘惑。在上海的後期,小軍和小紅幹脆把家搬到了魯迅家附近,蕭洪天來訪,或者和徐光平家唠叨幾句話,或者和小海寶貝玩了一會兒遊戲,或者做幾道魯迅愛吃北方菜。
離開青島之前,蕭紅把《生死之地》一書的初稿寄給了魯迅,到了上海和魯迅的第一次見面,蕭軍為魯迅帶來了《八月的村落》副本,對魯迅進行了細緻入微的修改。《八月村》以抗日題材,無法公開發表,而魯迅推薦的《生死戰場》,雙方轉手半年仍未有機會出版。在蕭軍的建議下,在魯迅的同意下,他們與葉紫組成了"奴隸社會",葉紫也無法出版短篇小說集《收獲》,秘密出版了三部《奴隸系列》:《收獲》、《八月國度》和《生死》。本系列的前幾頁印有介紹:我們被困在"奴隸"和"準奴隸"的境地,至少我們也應該做一個小小的奴隸哭泣,盡全力,盡一切耐心......
《八月的村莊》和《生死之地》成為蕭軍、蕭紅的代表作,在上海文壇聲名鵲起。雖然總是比較,但肖軍和蕭紅的寫作技巧和創作才華大相徑庭,蕭軍的寫作立場清晰、深刻,蕭紅的小說雖然結構松散,但細膩、清新、直接打動了人們的心。正如胡楓所說:"小駿很難攀登藝術的巅峰,小紅是以她的天才為本的。"魯迅很高興這兩本書都受到了好評,也坦率地提出了《生死戰場》似乎比《八月國度》更成熟,在以後的寫作中,小紅更有前途。
這種不同的寫作風格,在某種程度上源于小軍和小紅的性格,概念的差異,情感上的差距也随之産生。蕭紅因為過去的不幸,極度需要愛與愛,性格細膩敏感近乎懦弱,軍人出身的蕭軍有着大男子主義的手法,經常無視蕭紅的感受,甚至在人群面前嘲笑蕭紅的寫作。
兩人正式分手後,蕭紅曾向閻吐露:"我愛蕭軍,依然愛着,他是一個優秀的小說家,思想上是同志,在艱難的鬥争中一起過來!但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不知道你男人為什麼這麼大脾氣,為什麼要帶老婆做安全氣囊,為什麼不忠于老婆!"
1936年,兩人的關系幾乎破裂,小軍在蕭紅中,又有一段戀情。但魯迅的猝死給了兩人一個痛苦的打擊,在痛苦之後,他們終于沒有分手。直到上海也陷入白色恐怖危機,二孝跟随胡峰到武漢參加創辦《七月》雜志,并響應李公普邀請山西臨沂到國民革命大學任教。1938年,日軍對山西發動全面進攻,就是要留下來,兩人總是吵架,告别了。
蕭軍有軍氣,依靠自己的堅強,決心留在臨沂參加抗日遊擊隊,蕭紅卻以為是"英雄主義、激進主義",希望自己聯合參加丁靈率領西北野戰兵團,趕往西安。"你要打遊擊隊嗎?"這不比真正的遊擊隊更有價值,以防萬一......犧牲,在你這個年紀,你的生活經曆,你的文學天賦......這種損失不僅僅是你自己的。"
"我們經常這樣做是為了産生分歧,我們讓兩個人不開心,是以他們還是走自己的路比較好......"于是肖軍正式提出分手。
分歧後,蕭紅同同在野戰團末期的木絲相親結婚,調往武漢、重慶、香港等多地,31歲時死于香港貧困,留下了《馬貝勒》、《馬貝勒》《呼蘭河傳記》等作品,以及蕭軍在丁玲的勸說下, 沒有參加抗日遊擊隊,而是離開臨沂前往延安,并在延安遇到了19歲的王德芬,和她一起度過了餘生50年。
資源:
《兩個堅強的靈魂》,明仁,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
《小紅自傳》,肖紅,大象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人與人:蕭軍回憶錄》,肖軍著,中國文化聯盟出版社,2006年6月
《小洪評論》,葛浩文著,北方文藝出版社,1985年3月
《肖軍評論》,王克/徐賽著,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年1月版
作者|肖淑軒
編輯|青子羅東
校對|薛靜甯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