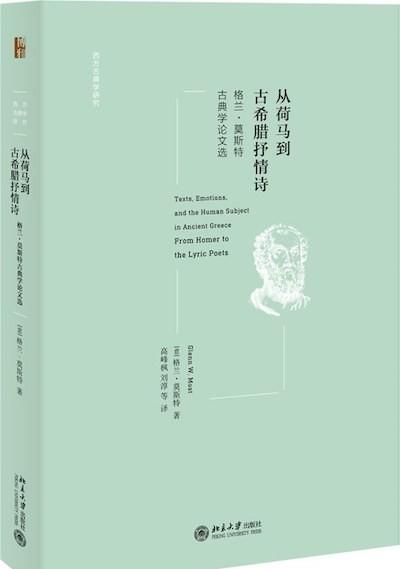
《從荷馬到古希臘抒情詩:格蘭·莫斯特古典學論文選》,[意]格蘭·莫斯特著,高峰楓、劉淳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424頁,75.00元
我第一次接觸到格蘭·莫斯特(Glenn Most)教授是在2018年1月26日晚上,在芝加哥大學的合作書店(Co-op Seminary Bookstores)的一場新書活動上——格蘭·莫斯特與安德列·拉克斯(André Laks)合作編譯的洛布多卷本《早期希臘哲學》(Early Greek Philosophy)——他與芝大已退休的古典學家詹姆斯·雷德菲爾德(James Redfield)就早期希臘哲學問題進行對話。在此之前的白天,芝大的弗蘭克人文研究所(Franke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也舉辦了關于早期希臘哲學的會議。在合作書店舉辦的對話裡,雷德菲爾德說得并不算多,莫斯特則侃侃而談,對學術史問題如數家珍。其中,讓我印象最深的兩處。一是莫斯特有非常全球化的視野,他特别提了,由于一些早期希臘哲學殘篇隻以叙利亞文和阿拉伯文翻譯形式保留下來,莫斯特計劃用叙利亞/阿拉伯文-英文對照的形式出版,但這一計劃遭到洛布叢書主編反對。因為洛布從來沒有處理過希臘、拉丁以外的文獻,主編認為遇到這些殘篇,隻需英語翻譯,原文處空白;在莫斯特的強烈要求下,主編最終答應将叙利亞和阿拉伯原文錄入。二是在問答環節,有芝大的老師提問,“前蘇格拉底哲學”這一概念因為帶有強烈目的論色彩而被棄用,改為“早期希臘哲學”,是否類似現在聖經研究裡都不喜歡“舊約”而用“希伯來聖經”這一概念。莫斯特從古典學和聖經學兩方面出發,對各自問題脈絡進行了梳理,認為二者并不一樣。時間過去久了,我已經忘記莫斯特給的具體理由是什麼,但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和莫斯特的互動中,那位老師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學生,而莫斯特像是教授中的教授。四年前的這場講座,仍是我目前聽到的所有講座裡(特别疫情後,得線上學術活動便利,聽了不少中國及歐美各大學的講座)最受震撼的一場,莫斯特在我心中的印象也全由此來。
神學院合作書店活動
之前,在2017年秋季學期的希臘文學史(Survey of Greek Literature)課上,講到品達時,我讀了莫斯特的《贊頌的尺度:品達皮提亞第二頌歌與尼米亞第七頌歌裡的結構與功能》(The Measures of Prais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indar's Second Pythian and Seventh Nemean Odes)裡的一章,印象并不算特别深,這本書總體上是傳統的“國小”研究。《贊頌的尺度》是莫斯特在圖賓根大學的博士論文,雖然用英語重寫了一遍,仍然在德國出版。可以說,這本書并不是一本典型的美式著作,并沒有要建立某種廣闊的研究範式,或者把品達研究帶入某種更重要的理論架構裡。後來也讀了三聯書店出版的《懷疑者多瑪》(Doubting Thomas)一書的中譯本,盡管這書原本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但更像歐洲式的學術随筆,沒有對二手文獻引用的學術腳注,隻在最後提供了一些參考書目,也不是一本非常強調學術規範的美式專著。是以,盡管莫斯特出版了《贊頌的尺度》與《懷疑者多瑪》等多部專著,我們無法像對美國大多數人文學者那樣,用莫斯特的書來建立起對他學術方法和脈絡的判斷。總體上,莫斯特仍然像很多缺少美式“專著”的歐陸國文學家,對各種問題廣泛涉獵,寫有大量文章,而其專著則可以說是超長篇論文。
由高峰楓、劉淳主持編譯的《從荷馬到古希臘抒情詩:格蘭·莫斯特古典學論文選》可以幫助我們一窺莫斯特在古希臘文學領域的研究。我無意為整本論文集寫書評,古希臘文學的研究者更适合做這件事。對我來說,本書收錄的第十二篇論文《西蒙尼德“ 斯科帕斯頌”的語境》(Simonides’ Ode to Scopas in Contexts)裡的一個觀察非常有意思:
如今新曆史主義的熱潮在現代語言文學研究中已達到頂峰,将文化研究的殘骸在美國諸多英語與比較文學系的沙灘上;可以預料它早晚會席卷古典學界,實際上在一些極其有預見性的古典學者的著作中已經出現。在古典學術的現狀下,這不會隻帶來弊端。古典學對于古代文學與古代史關系的認識仍然難以置信地膚淺:前者是語言,後者是實物;前者是個人主體性與詩性雕琢,後者是制度限制與權力的暴行……在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廣泛實行的對古典國文學系與古代史系的機構劃分展現了對弗雷德裡希·奧古斯特·沃爾夫提出的“古代通學”(Altertumswissenschaft)理想的背叛。也許新曆史主義會動搖現狀。(363頁)
莫斯特在這篇最初發表于1994年的文章中對公元前六世紀的古希臘詩人西蒙尼德的一首頌歌進行了解讀,在最後一部分進行了文學研究的方法論反思。莫斯特提到了諸多文學批評方法,比如解構主義、新批評,但莫斯特特别強調了新曆史主義(New Historicism)。首先,從文學理論的角度,莫斯特強調新曆史主義像解構主義取代新批評一樣,進一步擴大了“文學”研究的邊界。但另一面,在上面引述的這一段裡,莫斯特又從古典學的角度強調新曆史主義的獨特意義——可以打破古代史與古典國文學分界,實作Altertumswissenschaft的理想。對于Altertumswissenschaft,譯者沒有将其直接譯為“古代科學”而是更加傳神得翻譯成“古代通學”。用“通”字表現出Altertumswissenschaft傳達出的打通文史哲、将古代研究作為一個整體的理想。
《古風希臘的文化詩學》
讀到這一段時,我感到“相見恨晚”,因為這也是我接觸新曆史主義在古希臘文學裡運用的感受。新曆史主義最早發端于英國文學裡的莎士比亞研究,和傳統的曆史主義解讀方法片面強調文學對曆史背景的反映不同,新曆史主義強調文學本身的意識形态性與文學作為曆史主體參與者的一部分。是以,新曆史主義強調在解讀文學作品時,把曆史背景與文本之間的有機互動勾勒出來。作為古代史學生,我在面對一個文學作品時,會想進行曆史化解讀;但在芝大遇到的古希臘文學學者(不包括莫斯特)都在告誡我,曆史化解讀文學是在限制文學解讀的潛在範圍,這不是最好的文學研究方法。而我的古代史老師也告訴我,曆史學與文學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學科,正如基督徒隻能在東正教、天主教、基督新教裡三選一一樣,古代文明研究者隻能在國文學、古代史和考古學裡三選一。迷茫之下,我遇到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古典學教授萊斯理·刻爾克(Leslie Kurke)1991年出版的關于品達的著作《贊頌裡的交通:品達與社會經濟的詩學》(The Traffic in Praise: Pindar and the Poetics of Social Economy)。這本書讓我眼前一亮,其對品達頌歌與公元前五世紀社會經濟關系的互動做了非常精彩的解讀,展示了橫跨曆史與文學的可能。我讀到這本書的感受與莫斯特的展望一樣,刻爾克展示了Altertumswissenschaft的理想。不過,我當時并沒有意識到,刻爾克就是把新曆史主義代入古典學(尤其古希臘文學)的最重要的學者,而《贊頌裡的交通》是她的第一本著作。
1993年,刻爾克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同門卡洛爾·多爾蒂(Carol Dougherty)出版了《殖民的詩學:古風希臘的城市與文本》(The Poetics of Colonization: From City to Text in Archaic Greece),這本書對古風希臘文學(包括品達)裡呈現出的殖民意識形态進行了梳理。同年,刻爾克與多爾蒂合作主編的論文集《古風希臘的文化詩學:崇拜、表演與政治》(Cultural Poetics in Archaic Greece: Cult, Performance, Politics)則可以看作是新曆史主義的“宣言書”。收入其中的刻爾克的文章《庫多斯的經濟》(The Economy of Kudos)對文化詩學(cultural poetics, 新曆史主義的另一種稱呼)做了如下界定:“(文化詩學)鼓勵我們将‘文本’(text)讀作背景(context),将曆史本身讀作文本。而文本與背景都是在多樣的、有競争的象征性政策與象征性經濟下形成”這不僅僅是對新曆史主義方法從古典學的角度進行了簡明扼要的概括,更可以看作是宣言書裡的宣言書。
《古風希臘的文化詩學》
從學術的角度,刻爾克與多爾蒂在新曆史主義架構下對古希臘文學的研究各有特色,而刻爾克将新曆史主義方法在古典學裡發揚光大做出了更重要的貢獻。多爾蒂任教的衛斯理學院隻提供大學教學而無法培養研究所學生,刻爾克所在的伯克利則是美國研究所學生教育重鎮,在伯克利,刻爾克與研究希臘悲劇的專家馬克·格裡菲斯(Mark Griffith)合作培養了無數希臘文學學者。刻爾克在伯克利最早的學生之一,現任教于多倫多大學的維多利亞·沃爾(Victoria Wohl)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之上于1998年出版了《親密的貿易:希臘悲劇裡的交易、性别與主體性》(Intimate Commerce: Exchange, Gender, and Subjectivity in Greek Tragedy)。這本書在女權主義人類學家加裡·魯賓(Gary Rubin)倡導的要将性别研究裡的人類學路子(以列維-斯特勞斯為代表)與精神分析路子(以弗洛伊德為代表)結合的理論基礎上,以女性作為父權制社會下的交易物為視角,對多部希臘悲劇裡的女性進行了政治經濟學解讀。綜前所述,刻爾克不僅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專著,主編了第一本論文集,還培養了第一位出專著的學生,而三者的共同主題是對古希臘文學進行新曆史主義解讀。
從這個角度,莫斯特這篇大概寫于1987或1988年、最後發表于1994年的文章(根據文章開頭的注釋,這篇文章最早在1988年一次會議上發表)成功地做了某種預言,接下來十年裡,新曆史主義越來越多地進入希臘文學,而這一研究範式也通過研究所學生培養實作了制度化再生産。從研究内容而言,莫斯特也明言:“新曆史主義則進一步囊括了幾乎所有文本,不鄙棄曆史寫作(視其為一種文本)、公共與私人檔案乃至廣告與流行文化創作。”莫斯特在這裡似乎也在為未來新曆史主義下的古典學研究劃定了研究方向。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刻爾克與沃爾之後的著作。在《贊頌裡的交通》之後,刻爾克主要有兩本獨著——《錢币、骨頭、遊戲與黃金:古風希臘的意義政治》(Coins, Bodies, Games, and Gol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in Archaic Greece)與《伊索式對話:流行傳統、文化對話與希臘散文的發明》(Aesopic Conversations: Popular Tradition, Cultural Dialogue, and the Invention of Greek Prose)。這兩本書都像莫斯特強調的那樣,“不鄙棄曆史寫作”,《錢币、骨頭、遊戲與黃金》把希羅多德放到古風時期希臘貴族意識形态與商人意識形态鬥争的背景下進行閱讀。而《伊索式對話》不僅包含了希羅多德與柏拉圖這兩種不同體裁的作品,還借鑒了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潛隐劇本”(hidden transcripts)的概念,強調希羅多德的散文創作與柏拉圖的蘇格拉底對話都包含有伊索傳統這樣的“流行底層”。《伊索式對話》也成為研究古代流行文化非常重要的著作,莫斯特強調的流行文化會成為古典學的研究對象成了事實。
同樣的,沃爾之後的兩本書——《廢墟裡的愛情:古典雅典民主的愛欲》(Love among the Ruins: The Erotics of Democracy in Classical Athens)與《法律的宇宙:雅典法庭演說的司法話語》(Law's Cosmos: Juridical Discourse in Athenian Forensic Oratory)也展現了這一點。這兩本書分别把修昔底德與雅典法律演說詞當作文學作品閱讀,對其進行意識形态分析。而莫斯特說的“公共與私人檔案”會成為新曆史主義下的文學研究對象,則展現在刻爾克另一個學生的研究上,現任教于康奈爾大學的雅典娜·基爾克(Athena Kirk)去年出版了《古希臘名單:各種體裁裡的目錄與清單》(Ancient Greek Lists: Catalogue and Inventory Across Genres),對古希臘文本裡面一種不被重視的現象——名單(比如《伊利亞特》裡面列出的各地區軍隊将領的“荷馬船表”)——進行了文化解讀,揭示這種枯燥的體裁背後的文化邏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爾克非常重視文學裡的名單與銘文裡的名單的互動。古希臘銘文往往隻為曆史學家作為第一手曆史材料而被重視,而基爾克從文學的角度,強調銘文是一種現實中的文化實踐。
如果說刻爾克及她的學生主要将新曆史主義帶入古風古典希臘文學研究的話,這一影響已經波及到古典學的其他領域。在希臘化文學研究領域,刻爾克與哈佛大學的希臘化史專家保羅·科斯敏(Paul Kosmin)合作指導了莫妮卡·樸(Monica Park)關于托勒密詩人卡裡馬庫斯的博士論文《有朽的神聖:卡裡馬庫斯與帝國神學的形成》(The Mortal Divine: Callimachus and the Making of an Imperial Theology)(莫妮卡·樸後在範德堡大學任教,但現在已經離開了學界,這篇博士論文目前仍在封鎖期中,是以我沒有讀到)。2013年紐約巴德學院研究希臘小說的羅伯特·喬非(Robert Cioffi)在其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想象的地域:古代小說的族群性、異域主義與叙事》(Imaginary Lands: Ethnicity, Exoticism, and Narrative in the Ancient Novel)中強調要學習刻爾克在古風古典希臘文學上的方法。而在筆者的閱讀範圍内,有兩部拉丁文學研究著作——菲布·鮑迪奇(Phebe Bowditch)出版于2001年的《賀拉斯與供養的禮物經濟》(Horace and the Gift Economy of Patronage)和尼爾·科菲(Neil Coffe)出版于2009年的《戰争的貿易:拉丁史詩裡的交換與社會秩序》(The Commerce of War: Exchange and Social Order in Latin Epic)都指出要以刻爾克的著作為模闆來解讀拉丁詩歌。在古典學之外,刻爾克的新曆史主義方法也直接影響了中國文學研究。刻爾克在伯克利比較文學系作為主導師指導了現任教于布朗大學的塔馬拉·金(Tamara Chin),塔馬拉·金的《野蠻的交換:漢代帝國主義、中國文學風格與經濟想象》(Savage Exchange: Han Imperialism, Chinese Literary Style, and Economic Imagination)直接将刻爾克的新曆史主義方法帶到早期中國文學研究,這本書在諸多方面都有《錢币、骨頭、遊戲與黃金》的痕迹。
《野蠻的交換》,哈佛大學出版社
莫斯特不僅成功預言了新曆史主義在古典學的興起,還非常有洞見地指出哪些問題會成為研究對象,作為弄潮兒的刻爾克及其學生的實踐則印證了這一判斷。當然,這幾年希臘文學研究也出現回歸“形式主義”(formalism)的風潮。刻爾克在伯克利指導的學生、現任教于哈佛大學的内奧米·韋斯(Naomi Weiss)基于伯克利博士論文的專著《悲劇的音樂:歐裡庇得斯式劇院裡的表演與想象》(The Music of Tragedy: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 in Euripidean Theater)就是純形式主義文學分析。而沃爾也開始自我批評,她在2015年出版的《歐裡庇得斯與形式的政治》(Euripides and the Politics of Form)裡指出,如果新曆史主義路徑學者将古希臘悲劇與古希臘官方檔案都隻看作是某種意識形态的展現,那悲劇作為一種文學體裁的意義在哪裡?這無疑是在反思自己早年的希臘悲劇研究。是以,沃爾強調,如果要對文學作品進行曆史主義解讀,不考慮其文學體裁等形式主義特征,就不是完全的曆史主義。雖然沃爾是在借助形式主義來彌補曆史主義的不足,這無疑也是某種形式主義的回歸。而現在任教于伯克利、之前在比薩高等師範學院受教于莫斯特的馬裡奧·泰洛(Mario Telò)在最近出版的《檔案感覺:一種關于希臘悲劇的理論》(Archive Feelings: A Theory of Greek Tragedy)裡一開始就認為要在曆史主義已經在希臘文學占主導的情況下尋找新路子,泰洛這學期也在伯克利開設“激進形式主義”(Radical Formalisms)研讨課,以回應回歸形式主義潮流。我們可以觀察,在作為新曆史主義希臘文學研究的大學營的伯克利,未來是否會有新的變動。
最後,包括莫斯特、刻爾克在内的當今英美古典學界重量級學者多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嶄露頭角,莫斯特與刻爾克都是研究品達出身。在此之外,現任教于芝加哥大學的古希臘經濟史專家阿蘭·布赫松(Alain Bresson)也是研究品達出身。他在1979年出版的博士論文《神話與沖突:對品達第七頌歌的分析》(Mythe et contradiction: analyse de la VIIe Olimpique de Pindare)對品達關于羅德島的頌歌進行了結構主義解讀,有非常深的時代印迹。除了古希臘經濟史,羅德島銘文學也是布赫松的研究專長之一,雖然這有他早年研究品達羅德島頌歌的痕迹,但與那時的研究風格大不相同。此外,現為牛津大學希臘史講席教授的尼諾盧拉吉(Nino Luraghi)在1994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論文《古風時期西西裡與大希臘的僭主:從利奧提尼的帕奈提奧到德諾梅尼德斯的卡杜塔》(Tirannidi arcaiche in Sicilia e Magna Grecia: Da Panezio di Leontini alla caduta dei Dinomenidi)。由于品達有相當一部分頌歌是寫給西西裡地區的僭主和貴族,是以品達頌歌是盧拉吉研究西西裡的重要史料。同時,盧拉吉在這本書裡也引用刻爾克關于品達的書,可以看作是刻爾克的著作在歐陸學術界最早的影響之一。不過,盧拉吉後來的興趣也不在西西裡曆史上,是以也離開了品達。可以說,刻爾克雖然不是“刺猬”式的學匠,與莫斯特、布赫松和盧拉吉這樣不斷遊移到其他領域的“狐狸”相比,刻爾克總體還是恪守在古風古典希臘文學領域,特别是她最近與芝加哥大學希臘藝術史專家理查德·尼爾(Richard Neer,尼爾也是刻爾克在伯克利之前的學生)合作的《品達、歌曲與空間:通向一種詩詞考古學》(Pindar, Song, and Space: Towards a Lyric Archaeology)一書又回到了品達。品達似乎也在某種程度成為了幾位風格迥異的古典學家的交彙點與分水嶺。
在将近三十年後再來讀莫斯特這篇1994年的文章,除了在西蒙尼德研究方面的貢獻外,更重要的是其中對新曆史主義的反思及預言記載了某個學術史時刻。是以将包含這篇文章在内的《從荷馬到古希臘抒情詩》翻譯介紹到漢語語境無疑會産生獨特價值,為我們一瞥近三十年來歐美古典學界的風雲變幻提供了友善法門。莫斯特曾經成功預言了新曆史主義對古典學的影響話,他現在積極從事比較古典學工作,尤其重視與中國學者和漢學家合作,盡管這一取向在目前歐美古典學家裡還是少數,再過數十年後,我們也許會像讀莫斯特關于新曆史主義的反思一樣,明白這又是一大“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