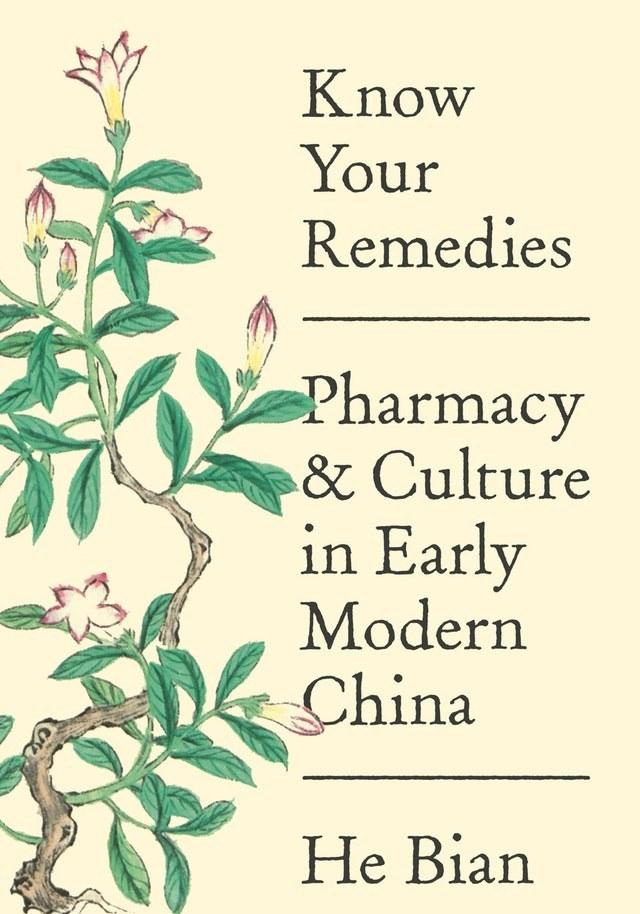
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by He Bi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pril 2020, 264pp
藥之為物,各有形性氣質。其入諸經,有因形相類者,有因性相從者,有因氣相求者,有因質相同者。自然之理,可以意得。
——汪昂:《本草備要》,1683年
藥之為物,大部取材于不完全之藥用植物,僅采撷其有效之一部分,供于治療,如草根樹皮之類是也……一入藥市,萬彙雜陳,如盲目者之不辨黑白,欲加整理,大有望洋興歎之感矣。故藥材之科學研究,鑒定為至難之第一問題也。
——趙燏黃:《祁州藥志》,1936年
“藥”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物”呢?從上述引文中或可看出些許端倪。汪昂讨論的是解釋治療效力的“藥性”,趙燏黃觀察的則是流通中的“藥材”。藥之為物,可以簡單地二分為治療屬性和物質(自然)屬性嗎?到底通過哪種方式才能了解“藥”這種普遍而特殊的存在呢?傳統士人汪昂強調 “自然之理”可運用于藥性的推演,而受過現代科學訓練的趙燏黃則希望通過研究多變與龐雜的藥材建構起科學的生藥學體系。二人從不同的視角觀察藥物,固然與其所處的曆史與文化環境密切相關,但相似的是,兩人都認為了解“藥之為物”的關鍵在某種更廣闊的知識體系。如果采用傳統儒家“格物緻知”的說法,通過研究藥這種“物”能帶給我們怎樣的“知”呢?
普林斯頓大學副教授邊和的新著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便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觀察藥物與知識文化的視角。該書一經出版便在海内外醫療史、科學史以及東亞史領域廣受贊譽。近來此書又榮獲2022年度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列文森中國研究著作提名獎(Honorable Mention),更顯示出其在中國史領域的重要貢獻。作者将中文标題暫拟為《藥之為物:明清的本草與知識文化》,其意大概有二。首先,此書提出的核心概念“pharmaceutical objecthood”指涉藥作為物的存在形式,可以當作“藥之為物”的對譯;其次,對“知識文化”的強調則道出了作者更加廣闊的視野。本書并非僅僅是在明清醫療文化背景下讨論藥學史的問題,而是試圖通過本草與藥物來觀察明清知識與認知領域的重大變遷,其貢獻不僅僅在于藥學史這專門的研究領域,更對明清時期中國知識版圖與認知世界進行了深入描繪。
該書主體分為六章,以明清易代為界分為兩部分。雖然章節組織大緻符合時間順序,但主要還是以特定主題組織起來的。我們當然也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看待全書的結構:前兩章講述了本草編纂與藥物知識從中央到地方的轉移過程,中間兩章考察了明末清初的文人群體對藥物知識的重構,最後兩章轉而讨論藥材市場與奇珍異藥對建構藥物知識的意義。總體而言,該書一以貫之的主題便是去中心化與多元化的知識生産過程。在這篇小文中,筆者分三個方面來介紹《藥之為物》對本草與明清知識文化的主要觀點,并在最後探讨該著對明清自然知識史的啟發。
藥之書:明清本草的出版與流傳
1505年,主持編纂《本草品彙精要》的醫官因弘治皇帝之死獲罪,中國古代史上最後一部官修本草就此藏于深宮,不為外人所知。然而十六世紀中國蓬勃的出版市場上卻出現了形形色色稱之為“本草”的書籍,其中當然也包括廣為人知的《本草綱目》。《藥之為物》從此出發,講述了一段與傳統本草史的主流叙事不同的故事。寫作明清時代的本草史或藥學史,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總是難以繞開的一部巨著。李約瑟(Joseph Needham)将李時珍稱作中國博物學的“無冕之王”。如今大概很難想象一部沒有李時珍與《本草綱目》的中國藥學史了。然而回到曆史現場,《本草綱目》的出版并不順利,李時珍生前都沒能看到這部嘔心瀝血之作最終出版。
中國曆史上的本草編纂,向來以《神農本草經》為起點,後世多次增修、擴充與校訂,經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以及唐宋諸多官修本草,至李時珍《本草綱目》集曆代本草之大成,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則為其餘緒。這便是中國本草史上所謂的“正統”與“主流”。就筆者所見,此說于二十世紀早期見于日本學者白井光太郎的作品,并由生藥學家趙燏黃首次譯為中文發表。日本醫史學者岡西為人有“主流本草系統”的提法。李約瑟、文樹德(Paul U. Unschuld)相關作品采用了“本草主流傳統”的觀點。中國本草史研究的代表性學者尚志鈞與鄭金生亦使用“本草主流”“本草旁支”的說法,不過其“主流”的含義更為豐富,不僅指主流譜系,也包含一個時代本草編纂的主流風格。這一“主流”在現代本草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一斑。但這種研究思路下所強調的往往是綜合性本草及其内容的增長與體例的創新,是以明清本草書籍的定位就成了棘手的問題。白井氏的譜系直接把明清大部分本草書籍列為正統之外的“旁支”。李約瑟感歎《本草綱目》之後中國博物學傳統的衰落,這與他對中國科學史的總體認識是一脈相承的,那便是十六世紀以後中國科學發展開始落後于西方。這一類觀點大多從現代科學出發,視本草為博物學或植物學作品,因而基于自然屬性的分類體系和基原鑒别知識最為關鍵,這些内容在大部分明清本草書中是缺乏的。
自十六世紀開始,官方編輯綜合性本草的傳統式微,本草的編輯、出版與诠釋轉入文人和出版商之手。《藥之為物》一方面從書籍史的角度考察明清本草書籍的出版與接受史,另一方面則從更長時段的曆史發展看待這一本草編纂的去中心化趨勢。首先,作者認為從十一世紀開始,宋代中央政權對本草知識的控制已經有所松動,各類地方官員和文人對官方本草的傳播、再版與修訂可被視為明清本草編纂去中心化的先聲,中央與地方文本生産的邊界也在逐漸消解。其次,金元醫家對藥物的興趣從廣博的綜合性知識轉向了在五運六氣指導下的藥理探索,這也對明清本草産生了深遠影響。這兩種趨勢共同促成了明清本草出版與風格的轉型。
作者在第一章主要考察了以下幾種明清本草類型:節要類本草、食療類本草以及炮制類本草。這幾類本草皆因其商業出版上的成功得以廣泛流行。以《本草集要》《本草蒙荃》為代表的節要類本草在大型綜合性本草與藥性歌訣類書籍之間探索了一條寫作本草的中間道路,兼具學術性與實用性。而後兩類本草則迎合了明代文人和士商群體中興起的養生風氣,是以也吸引了醫學領域之外更多元的讀者群。由此作者重新審視《本草綱目》的出版之路,雖然李時珍希冀自己的作品能夠得到朝廷的認可、接續宋代綜合性本草的統緒,但此書的最終流行卻得益于商業和地方性的出版事業。
本草史研究的前輩們雖然多集中于“主流”的叙述,但對明清本草诠釋也頗具洞見。岡西為人将明清本草分為三大類:實用性本草、藥理性本草和《神農本草經》複原本。鄭金生将明清本草學風分為臨床研究和尊經之風。這些以内容為主的分類卻較少将明清本草逐漸擴大的作者和讀者群考慮在内。《藥之為物》為我們展示一種看待明清本草書籍的另類方式,不再以内容為本探讨“主流”或“旁支”,而是将“本草”這一文類本身問題化。是以需要解決的問題不再是明清本草在總體本草史中的定位和評價,而是這一時期的作者與讀者群對“本草”的态度産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對本草知識和編纂方式進行了何種重構。當然,取得商業性成功的本草隻是明清本草編纂中的一個面向,文人群體也并非僅僅是本草的讀者,明清本草的另一個重要特征便是對藥性的關注,而這與文人儒士的思想和學術風氣是分不開的。接下來筆者将要介紹的便是《藥之為物》中呈現的“藥”與“理”的世界。
藥之理:文人趣味與專業技藝
《藥之為物》對本草的出版史有着細緻入微的體察,但它也沒有忽視對具體内容的關注和細讀。該書第三、四章提供了觀察本草知識變化的視角,用一個問題意識概括便是:本草之學到底是醫者的專業技藝還是儒者格物之一端?在十七世紀,本草的主流學風幾經變化,但這并不單純是認識論與思想層面的變遷,也與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緊密相關。提到藥之理,不得不提金元時期本草風格的轉變,在岡西為人和鄭金生的研究中皆将金元本草特征概括為對藥理的探索,而這受到宋代以來理學興起的影響。《藥之為物》第三章簡要回顧了自朱熹開始的諸多理學思想家們對“性”與“理”的探讨,以“藥”為代表的“物”在其中顯示了突出的地位,格物緻知成為文人對自然之理探求的重要方式。
明末江南活躍着諸多對藥學知識感興趣的文人社群,同時這裡也是東林黨人講學議政之地,這兩組看似不相關的群體卻産生了令人意外的交集。雖然以往的研究多關注東林黨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動,但他們對醫藥的興趣卻也難以令人忽略。他們的交往圈中活躍着一位“神醫”缪希雍,他們共同探讨時事與醫理、搜集藥方。缪氏的《神農本草經疏》不僅挪用了儒家“疏”的文體,其中關于藥性的探讨也與宋代以來的性理之學關系密切。盡管東林黨人在明熹宗朝遭遇迫害與打壓,但缪希雍探索藥性的方式卻在江南文人之間生根。在明朝最後的二三十年間,本草與藥學知識成為江南文人中的時髦話題,湧現了各種相關的文人社群與講學活動,對藥性的探索被視作儒者對自然之理探索的重要方式。本草書籍的出版也空前興盛,李時珍及其《本草綱目》正是在這一時期成為出版市場的寵兒,甚至出現了假托李時珍之名的作品。
文人對本草的探索塑造了儒者對于藥學知識的權威身份,但不同的聲音同樣存在。第四章将視點轉向明清鼎革之後,雖然明末具有強烈文人趣味的本草書籍在清初多有再版,但專業醫者重塑“醫學正統”的聲音漸漸凸顯。除了醫者的聲音,作者還考察了清代官方的三項文化工程——《古今圖書內建》《醫宗金鑒》與《四庫全書》的編纂——中的本草知識定位。這些類書或叢書反應了與明末不同的認識論取向,本草再次被定位為醫者的專業技藝,反而與儒者格物之學的邊界日益增強。在此,《藥之為物》展現了清初本草領域的重要轉向,原本統一的本草知識日益分為兩種邊界清晰的學問:儒者的格物之學與醫者的治療技藝。
在此不得不提中國科學史中的一個關鍵問題:為何中國的博物學傳統在《本草綱目》之後走向衰落?這一問題從近代早期西方科學觀念來反溯中國科學的發展,認為明清本草學由博物之學轉向了臨床治療之學。邊和雖然也使用了博物學(natural history)的表述方式,但她卻試圖超越這種“博物”與“臨床”的現代二進制劃分,以中國本身的知識分類來探讨認識論的轉向。在此儒者的格物之學不隻包括《本草綱目》一類的綜合性本草,也包括缪希雍《神農本草經疏》這類以儒家性理之學探讨藥性的著作,而後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多從屬于“臨床本草”類作品。是以,在儒者博物興趣與醫學專業技藝的讨論中,關鍵不再是關注藥物自然形态與分類還是重視治療效用,而是儒者與醫者對于藥學知識權威的拉扯。
作者還提到了列文森提出的“literati amateurism”,或可暫譯為“文人的去專業主義”。在這種立場下,明清文人将“醫蔔星曆”乃至繪畫等專業技能視作儒者格物之學的一部分。他們貶斥掌握有專門技藝的“工”(醫工、畫工等),強調儒學在解讀專業知識中的權威地位。《藥之為物》對晚明階段的叙述确實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這種“去專業主義”,但作者反對将這種文人理想本質化。與其說這是明清精英文化的内在特征,不如說是晚明特殊政治社會環境的産物。“儒”與“醫”的分分合合也對明清“儒醫”問題的探索有所推進,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醫者社會身份,而作者在本草知識和認識論層面的闡釋更為細緻地呈現了兩者關系的分合。明清本草世界的變化不止于書籍與藥理,文人與醫者的知識權威也越來越受到來自另一層面的影響與挑戰:那便是日漸興盛的藥材市場與來自遐方遠邑的藥材。
藥之材:從貢賦到商品
讓我們從文本與知識轉向具體的藥材。除了醫學與本草書籍,另一種常見記載藥物的文獻便是地方志的“物産”部分。地方官和文人出于何種原因記錄或修訂物産中的“藥材”呢?我們該如何了解這部分的藥材記錄?它又反應了怎樣的知識文化?《藥之為物》在第二章考察了作為土貢的藥材及其在明代财政改革中的角色。在唐宋官修本草中,藥材便關聯于出産的“州土”,地方貢賦也象征着中央對其疆土的控制。藥材在明朝仍然是中央向地方征收的“物料”之一,但貢賦來源與邏輯有了重大變化:一者明朝藥料來源主要轉到了南方,二者額定稅賦比唐宋時期大幅增長,且征收更具強制性。這一方面引起了士人對稅賦合理性的探讨,另一方面也迫使地方逐漸變通對藥料的征收方式。由于各級攤派的額征藥料與地方實際出産不符,很多地方不得不以折銀的方式征收,再從市場采買相應藥材上交。這種變化在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改革之前便已出現,從這個角度看,十六世紀明朝的稅制改革也有着自下而上的動因。這種變化代表着對藥物知識的掌控也逐漸從中央轉到了地方,地方官一方面推動着地方志物産記錄的更新,另一方面以一種更為積極的态度宣示地方物産之豐饒。
賦稅的貨币化也進一步推動了跨區域的藥材貿易,徐大椿“醫不備藥”的感歎昭示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商業化的程序更深刻地影響了十七世紀後的藥物知識文化版圖。第五章作者細緻描繪了藥物商業化的兩面:十六世紀末,江西樟樹鎮成為藥材的集散中心,全國跨區域藥材貿易體系初步成型;城市藥鋪逐漸取代了小型的私人藥室,醫藥分業趨勢漸顯。藥材貿易促進了“道地”觀念的出現,來自遐方遠邑的藥材得到市場追捧。藥鋪的經營者逐漸與醫者的身份分道揚镳,轉而強調自身對于藥材道地與制藥的專業知識。
市場與貿易對藥物知識的影響在第六章得到了更深入的描繪。作者通過對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的細讀,揭示了在主流本草之外的另類知識生産場域。《拾遺》中記錄了大量來自山野、邊地與異域的奇珍異藥,而這些藥物知識往往來源于“山民”、“土人”、屠戶、獵戶、漁民、行商、“番民”、流寓幕客等等。趙學敏的流寓生涯也讓他有更多機會接觸到這些民間藥物與相關知識。“野生”成為藥材品質的象征,但“野”同樣也暗含着未知的風險與不确定性。消費者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嘗試各種方式處理與服用這些遠方珍奇,這也進一步消解了食物與藥物的邊界。與本草中已經确立的藥物知識體系不同,這些知識在非正式的網絡中流動,并在不斷成型與轉變中形塑了民間社會更具實用性與具身性的藥物知識文化。
明清社會的商業發展及其帶來的社會文化變遷已在明清史領域有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藥之為物》從藥材出發,深刻讨論了市場與金錢在知識領域帶來的變革。藥材貿易的興盛消解了中央政權、文人與醫者對藥物知識的權威,把我們帶到了更為地方性、實踐性與民間性的知識領域。近來科學史研究的趨勢之一便是關注非精英群體對自然事物與知識的探求,此種取向将科學研究了解為實踐性活動,知識的生産場域也從學者的書齋和實驗室轉向田野、市場與手工作坊。對中國科學史研究者而言,探索非精英群體的知識傳統不得不面對資料的限制。中國傳統時期留存下來的“科技”文獻大多出自精英之手,這便要求研究者或擴充搜集資料的視野、或更新閱讀傳統文獻的方式。近來宋安德(Andrew Schonebaum)的研究展示了手抄本醫書、通俗小說與戲劇中豐富的民間醫療知識,而邊和則通過細讀傳統“精英”文獻發掘出精英與非精英知識傳統之間的互動與張力。這要求研究者更具理論自覺和敏銳的眼光,對兩種知識傳統不做預設性的價值判斷,從具體的實踐活動中去體察知識建構過程。
餘論:明清自然知識的文化版圖
《藥之為物》在結語中引用了清代“藥戲”《藥會圖》裡的一段話,“縱不日用乎活藥,亦豈肯忘情于活藥,鼓舞歡誦,則人人知其藥,亦即人人知其性。”書名Know Your Remedies或許就來自于其中的“知其藥”。“知”一方面表達的是知識,另一方面則是對藥物的認知與探求知識的實踐。本書從本草與藥物出發,落腳點卻在明清知識文化的變遷。通讀全書,市場與金錢的力量一直在形塑物質的流通與知識的生産,作者對民間性與地方性的知識生産有着一以貫之的關注。前文筆者已經說明了《藥之為物》在藥學史、醫學史領域的創新,在此便簡要談一談它對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啟發與相關思考。
如今科學史界對于“科學”的了解日趨多元,它不再是嚴格西方意義上的“science”,而是不同社會與文化中對自然知識了解與探索的實踐行為(也就是複數的“科學”sciences)。在此背景下,“李約瑟問題”或許顯得過時了,但中國科學史要超越“李約瑟問題”确實還有很多的路要走。如何擺脫西方科學革命的論述架構,重構中國科技自身的演進曆程與“範式轉移”?這是擺在研究者面前的難題。那葭(Carla Nappi)對《本草綱目》的研究、薛鳳(Dagmar Sch fer)對《天工開物》的研究都從各自的專業/技術性文本中發掘出中國思想與文化對自然物和技術的獨特思維與認知模式。《藥之為物》為我們示範了另一種可能性。傳統本草與藥物知識并不僅僅關乎治療,它也是不同群體探索自然事物及其與人、與宇宙關聯的學問與實踐。我們或許可以将這種取向稱之為“博物學”(natural history),但不必以歐洲博物學的标準來評價中國本草的發展與興衰。作者從本土的思想資源出發,探讨“儒者格物之學”與“醫者專業技藝”兩種知識範式的競争與拉扯,而這兩者又同時受到來自市場與民間領域實踐性知識的影響與挑戰。中國本草傳統并沒有在李時珍之後走向衰落,而是經曆了另一番深刻的認知變革。這種變革對中國自身“科學”傳統的意義何在?這仍是研究者需要繼續探索的問題。
當然,講述中國科學自身的演進并不意味着忽視比較性和全球性的視野。作為全球史的一部分,明清中國的曆史既受外部因素影響,又形塑了同時期的全球史程序。近二十年來,海外中國史研究者一直緻力于将明清史放到更廣泛的“早期現代性”(early modernity)中思考。《藥之為物》以“早期現代”(early modern,也有“近代早期”的譯法)指稱明末清初(十六至十八世紀)這一時段或可展現出她更廣泛的學術關懷。如何定義中國的“早期現代性”與回應“李約瑟問題”也是一體兩面的,都關涉中國曆史的分期問題。邊和在本草研究中展現了明清知識文化變遷承前啟後的意義,她更傾向于從中國自身的曆史程序定義早期現代性。由此出發,下一步或許需要繼續讨論這段曆史在全球科學史中的定位,明清中國知識世界的變革是否如經濟社會領域一樣深刻卷入到了全球早期現代的曆史中呢?
除了宏觀層面的方法論意義,我最後還想提出兩點具體研究層面的思考。首先,作者通過本草文獻的研究給我們帶來了非常不一樣的曆史叙述,這提示我們要轉變對傳統科技類文獻的解讀和認識方式。文本内容的細讀固然重要,但對作者身份與意圖、編纂模式、文本類型、出版與流傳等方面的探索同樣不可忽視。換句話說,就是要把文本置于它所形成與傳播的實踐過程中去了解。其次,精英與非精英的知識傳統并不截然對立,兩者往往處在互動當中,并不斷重塑着明清自然知識的文化版圖。在中國社會史、曆史人類學領域,對所謂“大傳統”與“小傳統”已有深入探索,民間社會和大衆文化研究也蔚為大觀。相對而言,我們對中國曆史上非精英群體的自然知識與技術傳統仍知之甚少,對其曆史意義的挖掘仍不充分。《藥之為物》針對此問題展現了敏銳的洞察力,但受限于資料性質,對地方性與民間性知識文化探讨的廣度和深度仍顯不足。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大衆文化》英文初版三十餘年後,這部開創性論文集的中譯本終于問世,但其中并沒有涉及自然知識與技術方面的讨論。不過三十餘年來明清大衆與民間文化的研究發掘了大量民間文獻,其中不乏與科技、醫療有關的内容。科技史的研究者或可借鑒相關的文獻解讀與研究方法,補足這一傳統知識文化版圖中缺失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