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芯智駕──集萃産學研企名家觀點,全面剖析AI晶片、第三代半導體等在汽車“大變形”時代的機會與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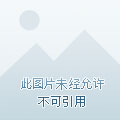
集微網報道,缺芯短缺仍在全球汽車業蔓延,近期的俄烏沖突又進一步給供應鍊危機蒙上一層陰影。
通用、福特、豐田、大衆等全球各大車企在供應鍊短缺中“掙紮”着度過2021年,使出渾身解數交出了還算過得去的業績。可以說,缺芯迫使這些百年老店們使出“創新大招”——傳遞缺少部分零部件的車型(Drop features)、轉移晶片庫存到更高利潤的車型上(Divert chips),以及保守戰略(Build-Shy strategy)——為了工廠不停産而繼續生産半成品汽車,然後暫放一邊等待晶片等零部件到位後繼續生産。
例如,寶馬和雷諾銷售的某些車型沒有數位螢幕,而日産和福特也在銷售沒有導航系統的車型。通用、福特等車企還采用保守戰略繼續生産汽車不讓工廠停工,這在短期内是有用的,因為它能保持汽車工廠營運(因為停工的成本同樣不菲),但不能保證汽車什麼時候完成生産。據華爾街日報此前報道,截至去年3月底,在福特的停車場内就停放了超過2萬輛等待晶片的半成品汽車。
晶片短缺之苦何時緩解成為2022年被繼續追問的話題。長期來看,是否也預示着汽車産業鍊以及商業模式需要更深遠的改變?如何變才能真正解決缺芯問題?車企以及産業鍊上下遊各自需要怎麼做?
供應鍊危機繼續蔓延 車企如何繼續創新應對?
德勤近期釋出的報告預計,晶片短缺情況預計将會在2022年持續,晶片交貨期将拖延約10至20周,到2023年初情況才能得到緩解。
過去一兩年,疫情的蔓延以及地緣政治等因素的影響,讓包括汽車在内的大部分産業都意識到供應鍊危機将是需要長期應對的問題。近期的俄烏沖突帶來的供應鍊不确定性再度印證了這一點。事實上,不少晶片大廠已感受到俄烏沖突所帶來的供應鍊危機。在晶片制造過程中需要使用氖、氪和氙等多種特種氣體,烏克蘭是世界上最大的氖氣生産國之一。富國銀行的資料顯示,烏克蘭主要供應的氖氣和氪氣都可用于KrF(248nm準分子雷射)鐳射,該工藝主要用于8英寸晶圓250nm-130nm成熟制程,制程産品包括PMIC、MEMS及MOSFET元件、IGBT等功率半導體元件。
雖然去年以來全球的IDM和晶圓代工廠努力擴充産能,采取了包括開設新廠,擴充現有晶圓産線,和提高生産率等措施,但是2022年能夠增加的供給仍然十分有限。
從總體供需趨勢來看,Gartner研究副總裁盛陵海分析認為,随着晶圓廠的擴産調整以及庫存需求的減少,整個半導體市場預計今年下半年會恢複正常,“但所謂的‘正常’是指大部分的半導體器件不再會有嚴重短缺問題。”他指出,由于目前全球主要晶圓廠的擴産多集中在5nm、28nm和40nm以及第三代半導體産線上,而8英寸産線的産品以及12/14/16nm制程的投入相對有限,這意味着相關的半導體産品或仍面臨短缺問題,主要涉及一些模拟晶片、工業晶片、通信晶片等。在MCU方面接下去缺貨情況會有所緩解,但在一些工業領域尤其是車規級MCU方面,預計到今年下半年供應依然緊張。
對于汽車産業而言,供應鍊危機幾乎已成為持久戰。顯然,前文提到的車企“創新”之舉僅僅是短期的緩兵之計,要長期解決問題則需要從根源上着手處理。
一來,汽車廠商開始思考,單純依靠晶片廠擴大産能是否能完全解決問題?更何況這需要時間。其次,更重要的是,汽車産業鍊的深層次結構正在從外部和内部被打破。這種變化在幾年前就已經開始,而疫情等危機帶來的晶片短缺或将加速變革的程序。
從“供應鍊”到“供應圈” 金字塔狀垂直體系正在内外瓦解
汽車制造商與汽車零部件企業百年以來形成的金字塔狀的緊密垂直體系,正從外部和内部被打破。
而過去幾十年一直被汽車産業界奉為經典的“just-in-time”模式——晶片等零部件直接到達汽車組裝工廠的生産線,車企由此可以實作元器件零庫存,這可以幫助車企有效降低庫存成本并保持工廠高效運轉。這一次疫情等外部因素帶來的嚴重晶片缺貨危機,讓産業鍊意識到是時候做出一些底層的改變了。
在外部,全球汽車企業洗牌,帶動了新興零部件企業發展。比如,特斯拉上海工廠不斷提升在中國市場的本土化率,此前宣稱2021年底達到90%,近期又計劃提升到100%。特斯拉并不拘泥傳統車企的供應商稽核體系,主要以配合度、響應速度、研發實力為标準選擇供應商。
在内部,電動化、智能化帶來了汽車本身構造的變革以及生産方式的轉變,水準分工的模式已經悄然興起,或将在不久的将來徹底颠覆目前的垂直體系。
純電動車零部件數量比燃油車減少一半,并且各零部件通用性變強,是以,整車企業通過掌控軟體來協調不同零部件的性能,并持續更新軟體提升車輛品質,硬體産品子產品則轉為委托外部企業生産。
比如,手機代工巨頭鴻海集團正在深入布局電動汽車代工業務。鴻海于兩年前正式公開了旗下MIH電動汽車平台,目标在電動汽車領域提供包括零配件、設計、完整方案及組裝和制造的全面服務。如今該平台的成員已達2249個,覆寫整條産業鍊上下遊。在電動汽車的新業務上,鴻海已經制定明确的營運目标:預計到 2025 年純電動汽車占其制造營收比重達5%,營收規模目标300億美元,其中40%的零配件由鴻海集團自制。另一消費電子産業鍊頭部企業立訊精密近日也宣布将涉足代工電動汽車。立訊精密公告稱,其與奇瑞集團共同簽署戰略合作協定架構,以百億元入股奇瑞集團,并與奇瑞新能源拟共同組建合資公司,專業從事新能源汽車的整車研發及制造。
對此,瑞銀中國汽車行業分析主管鞏旻對集微網表示,這種汽車産業鍊的重構的确已經在幾年前就開始發生。“我們2018年拆解特斯拉汽車的時候,就發現特斯拉絕大部分的零部件都來自其自研,同時它也引入了很多更小的、更罕見的供應商,它們并不是傳統汽車供應鍊的廠商。”他指出,回顧整個2021年,在缺芯過程中,特斯拉的銷量卻再創新高,足以看到這種産業鍊的颠覆帶來的供應鍊韌性,“燃油車向電動汽車的轉變,帶來了更多對電子元器件、晶片的需求,電子産業鍊和汽車産業鍊某種程度上界限已經模糊,産業鍊的重構必然發生。”
對于傳統汽車行業的供應鍊變革問題,博世(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執行副總裁徐大全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強調,“供應鍊”這個詞在未來應該變成“供應圈”。他指出,打造智能汽車的硬體、軟體和生态,将需要多方的合作和配合。比如智能座艙開發的時候,常常是三方、四方和主機廠的共同合作。因而,他認為,供應體系将不再是垂直的供應鍊,而是一個合作供應的生态圈。
從“全球化”到“區域化” 增加供應鍊“可見度”
越來越多的晶片、電子元器件進入汽車供應鍊體系,本身增加了供應鍊管理的複雜度,疫情、地緣政治等大環境則給供應鍊體系添加了更多不确定因素。供應鍊戰略也必須發生轉變。
“全世界的企業管理者都在問自己一個問題,在經曆一場可怕的疫情後,要怎麼度過下一場未知的風險。供應鍊如何變得有彈性?變得靈活?如何抵抗下一次風險?這都将影響設計和管理供應鍊的諸多方面。”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名譽教授Morris A. Cohen博士近日對集微網指出。
事實上,汽車産業的這種供應鍊風險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顯現。Cohen教授舉例,在2011年日本發生地震時,半導體廠商瑞薩電子的工廠受到嚴重波及,當時世界上所有的汽車制造商都受到了影響。瑞薩是全球主要的汽車半導體供應商之一,但當時大多數車企卻都不清楚瑞薩是它們的Tier 1的供應商,很多車企在初期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已經身處供應鍊風險中。“我們從中可以學到的教訓是,整個端到端的供應鍊體系必須有更多的可見性,不僅要知道自己直接合作夥伴的情況,還應該明确它們上遊供應商的情況。這樣才能對整個供應鍊做出及時的判斷。”
盛陵海也強調,對于包括汽車制造商在内的終端廠商而言,增加整個供應鍊可見度是接下去保障晶片供應鍊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這意味着,終端廠商需要更進一步去了解他們合作夥伴的上遊,乃至上遊的上遊廠商的各種動态,甚至包括上遊的晶圓廠、封裝廠、材料和裝置廠商等。”
此外,鑒于目前的産業大環境,Cohen博士還指出,如今對全世界的企業而言,建立一個完全全球化的供應鍊戰略受到了挑戰,許多企業都開始轉向“區域”供應鍊戰略,而不是全球化戰略。
(校對/Ji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