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文旅類話題】
李蘭頌:《首漂大界河——探秘黑龍江》
第二章:白夜中追尋北極光
我最早讀到的有關于北極村即漠河鄉的文學作品,是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出自散文家雷加手筆的散文。雷加是我父親李又然在延安時代的戰友,我由雷加而認識被叫做“北極村”的漠河鄉及其那裡的白夜現象。與此同時,還為此多讀了幾遍法蘭西梅裡美的小說《卡爾曼》和《高龍巴》。
中國首漂黑龍江文化考察體育探險隊并電視專題片攝制組,由洛古河村下水,第一站到達就是漠河鄉,淩晨5時整,在這裡上的黑龍江南岸。漠河鄉在洛古河下遊的64公裡處,在此以北黑龍江主航道即北緯53 °30′處為中國版圖的最北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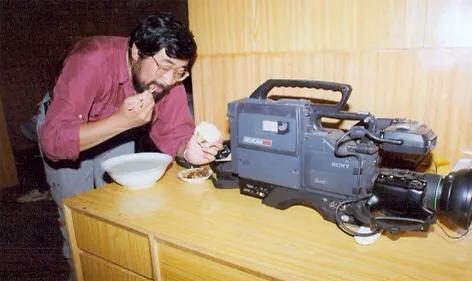
首漂隊并攝制組到的時候正好是6月22日。就在此時,用張子揚的話說——
漠河有一個獨特的現象:幾乎是白夜,晚上21時多,根本用不着路燈,他們集會、扭秧歌等,搞一個夏至節,每年這一天,這兒都會有一個奇特的自然景觀叫北極光出現。
當時我們去也就想追尋這個、拍成這個,想把這一集取個名字叫《尋找北極光》,但很可惜,沒有拍成,據說明年有(明年我還想去)。當時也很好玩,我們拍了當地人,問他們北極光、白夜的情況,他們講這也是中國一絕,當地于夏至前後每天晚上連一場露天電影都放不完天就亮了。是以當時拍攝就比較有意思、比較生動了。
與此同時,張子揚繼續說——
我們拍了金礦。當地淘金盛行,中國采金業是從這裡開始的(最興盛的時候是清朝)。黑龍江的資源:森林,礦(包括金),我們現在的開采是第二次或第三次,第一次是清朝,然後是沙俄、日本,是以現在雖然還很富有,但比那時差了很多。
我們去拍了“胭脂溝”,胭脂溝是慈禧太後給賜的名。有個故事說,當時這個地方很荒涼,有個人到這作道台(縣長),他有個好朋友,是個獵人,總到他家給他送東西,有一次這個獵人打了兩隻雁就給他送來,他不在,他夫人破腸開肚時,就發現雁肚裡有許多金粒,就問獵人是在哪兒打的,後來,就從這是開始開采,開采就開始進貢。慈禧太後非常高興,就說,你這一個地兒開采的黃金,我皇宮中所有女性的一年的胭脂錢,你一個地兒就全包了,是以就賜名為胭脂溝。
俄國人過來強行開采過。之後,還有日本人到東北,專在漠河地區畫一個十字鎬,标明這裡有黃金。這個我們也采訪了當地人。
這些事情,我就覺得,直到後來我們去拍這些,才跟了一些記者團,這些題材也沒有真正熱起來。是以我想,叫“探密黑龍江”也好,或叫“發現黑龍江”,都不失為過,因為有許多東西,大家都覺得很熟,黑格爾說“熟知的東西并不一定是真知”。我是通過這次漂流和考察,體會到了。
史料早有明确記載:1882年,也就是清光緒八年,鄂倫春人在日勒特河谷“掘穴得金數粒”。俄國人很快就越界盜釆。第二年,采金者“約計人數在7000人左右”。第三年,“聚集10000餘人”。因“領袖繁多,不能統一”,遂組織“會所”。據趙春芳的《邊防采集報告書》稱,光緒九年秋即1883年農曆七月;黑龍江将軍恭镗派旗兵百名,鄂倫春騎兵40名到漠河,“遣漢人楊才、勝玉珍入溝,勸說解散會所”。清政府又同俄國駐華使臣進行交涉,俄人理虧,退出了日勒特河谷,被他們操縱的“會所”亦宣告瓦解。為“杜患防邊”,清政府決定自辦漠河金礦,至光緒十四年(1888年)成立漠河金礦局,委任李金镛為總辦。當地的西林集,是鄂倫春人與他族交易的場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對于金礦的描寫的大作品——電影劇情片和長篇連載小說,都還是早就有了的。比如,李克異編劇、李俊導演、楊光遠攝影、寇洪烈美術、李偉才作曲、趙爾康和斯琴高娃主演的《歸心似箭》,描寫的就是這一地區抗聯戰士與百姓婦女的故事,金礦和煤窯的背景增加了光影的魅力;而劇作家孟烈創作的《老金溝尋夢》,我在主編《哈爾濱城鄉時報》松花江文藝副刊時,将其連載,反響不小,僅看個故事梗概也是起伏跌宕的,這是迄今最直接描寫老金溝的大部頭創作,完全可以拍出新的電影劇情片來,因為,孟烈可還是電影劇情片《俠女十三妹》、電視連續劇《雪城》的編劇呀。同時,也可以想見和證明,這裡絕非文學藝術創作的處女地,多少大師在此動過心思和筆頭啊!
更精确些說,北極村是指漠河村,漠河村為漠河鄉人民政府所在地,鄉以上還有縣叫漠河縣。《黑龍江政區沿革紀略》中稱:漠河縣。明朝隸木河衛。木河衛以河得名。木河,《龍沙紀略·山川》作“末河”;《黑龍江外紀》卷一作“墨河”;《黑龍江述略》卷一作“墨河”,卷四又作“黑河”;《水道提綱》作“謀河”;《漠礦錄》卷一“礦山”雲“内府圖作漠河”。
上述名稱皆為當地土人的“音譯之轉”(《黑龍江将軍衙門檔》)。“漠河,自内興安嶺山陰發源,流入黑龍江。起源在(黑龍江)城北1250裡”(《黑龍江通省輿圖》)。
漠河縣漠河鄉漠河村,是以中國的“北極村”與“白夜現象”而馳名世界的。就說現在的漠河村吧,由于遠方的客人越來越多,村裡的路旁也蓋起了紅磚樓,有招待所、儲蓄所、飯館和商店,鄉人民政府也是這樣的二層樓建築。當然,平日裡,小村甯靜如初,并非能夠輕易染上城鎮的喧嚣乃至噪聲。
在包括港澳等境外遊客的眼裡,他們卻如是說:所謂“時空熱點”,也是國小校放學時,紅領巾跳着橡皮筋;不時由中巴送來的旅遊團或零散客,像給村民送來他鄉異地的電視現場直播節目一樣,圖像是通過衛星輸的,聲音是海底光纜傳的,都像是從天而降的,顯然都在村民的關注和打聽之中,諸如國際啦、民主啦;還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民是乘坐馬車下地去的,“北極市場”上賣魚蛋和販蔬菜的攤主本質上也是勤勞的中國農民,他們互相唠着閑嗑,等待生意。
早在1981年5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決定:“設立漠河縣。将原呼瑪縣北部的漠河、興安兩個公社和阿木爾、圖強、古蓮3個區劃為漠河縣,縣址設在西林吉。漠河縣由大興安嶺地區行署上司。”
這裡要說,名副其實的漠河縣漠河鄉漠河村與世界相連被全球所知的事情還有一件,這就是中國參加全球氣象情報交換的台站之一——漠河縣氣象站設在此地——北極村邊。漠河縣氣象站的從業人員常年負責監視儀器儀表、抄錄有關資料。1969年2月13日夜間氣溫竟為-5﹒3℃,是已知的中國境内曆史有記載以來的最低氣溫,一般的冬季北極村則為-42℃。這裡,一年四季,暖和的日子,隻占三分之一。其餘時間都是挺冷或特冷的天氣。
“查了許多資料才知道黑龍江屬于‘寬淺’河的水系,流速也比較緩慢(4—8米/1分鐘),而且沒有大的落差,這樣呢,刺激性就比較少,在探險方面,就覺得色彩差了一點兒。同時也感覺到,像漂這件事,不論是好、是壞都有個結果,這個結果,有時也許是個壞的結果,但也許對個人的一生來說是最輝煌,最永恒的。當然,我們要漂黑龍江時也想到了危險,但客觀地說,我們也已經了解到這條江在探險方面與黃河、長江就不一樣了。”這番話是張子揚經過深思熟慮後說的。這位大胡子隊長兼導演發出指令并作出分析:“修艇,艇再慢撒氣,也要繼續漂!”
他果斷地指出:“6月23日至24日這一宿沒白漂,但以後不宜夜漂了,還要避開沿江的那些大張網,咱們再下水幹脆漂二流航道,看來,早漂,早睡才有效率。”按照這意思走,就是英國笛福《魯濱遜漂流記》的風格了,這又與我先前所說的梅裡美筆法大為不同,而北極村的自然現象尤其是白夜現象更為叫絕,那種神奇和夢幻簡直非科幻巨匠凡爾納才能寫得了似的!漠河縣漠河鄉漠河村無疑是總給人以震撼的北極村!
說起北極村的大自然現象,我想到了凡爾納、笛福、梅裡美的寫作;真正動筆向世界揭示這裡奧秘的除雷加外,當然還有許多作家、詩人、歌手、記者,其中突出的一個是從這裡走出去的女作家遲子建。首漂隊并攝制組是在夏至的第二天抵達這裡的,從一上岸,就對“北極村地理”、“白夜現象”、“遲子建童話”發生興趣,要将這些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聯系在一起拍成錄像。
通路了女作家遲子建的祖母,這似乎是一件必須又做起來很輕松的事;可是,要抓拍“白夜現象”中的北極光可就難了。漠河縣漠河鄉漠河村的夏季晝長夜短,首漂隊并攝制組抵達的夏至時分,正是白夜現象最為明顯的幾天,整日裡太陽似乎總不離去,即使是黑夜,也呈現白光,對面相逢可見人的。
“遲子建童話”、“白夜現象”、“北極村地理”就是在如此的自然環境與人文氛圍中發生的。外來的人們很難想像這裡的冬季出現最低氣溫時那種異常寒冷的情形,因為眼前夏天的悠長的傍晚乃至深夜,那似乎整夜都不會遠走的太陽,灑落給大地金光璀璨的萬道霞光,就是北極村的暮色和夜色的主基調,而這與清新的晨霧的彌漫還有所不同,這是令所有人都會激動不已和徹夜難免的景象。
一位由昆明老家來這裡當水兵又複員到黑龍江省旅遊局工作的同志,是這樣記錄他水兵生涯中最難忘的一幕的:
——太陽放射出的強大的帶電微粒子流,在地球磁場作用下,急速地向南北兩極集中,與高空大氣層發生猛烈撞擊與摩擦,便産生了五彩缤紛的北極光。
——那年夏至,是一個風輕月柔的夜晚,戰友們航行一天後都已入睡。我站頭班崗,忽然發現,在太陽遠走的方向上空,出現了一條多彩的光束。我向艇長報告,艇長當即決定集合了全艇官兵監視異情,甚至有人懷疑是外星來客了。
——啊,是美麗的北極光!我們為之歡呼雀躍。那五彩光帶,照亮了天空,映紅了大地,像雨後的彩虹橫跨天際⋯⋯微紫色、深橘色、玫瑰色、橙紅色、金黃色、銀白色的光,集中到一起,壯觀又瑰麗。
——不一會兒,光帶疏散,空中出現一個碩大無朋的光環,幾乎占去了整個漠河的天!又過了20分鐘,光帶與光環融為一體,是任何語言都難以描述的奇特風緻果真出現在我們眼前……我還意外地發現,江水中的北極光,别有一番景色在召喚着和感動着你⋯⋯
凡爾納、笛福、梅裡美⋯⋯
雷加、遲子建⋯⋯
水兵⋯⋯
我們,首漂隊及攝制組,在現今中國版圖最北端小村落裡所能感受和領略到的一切,都是極為珍貴的,因為,這裡的一切,漠河縣漠河真漠河村的一切,都與世界相連被全球所知,這裡的一切神奇又公開!
如果說上一章講到首漂隊及攝制組通路遊壽先生是從曆史和文化方面考慮,那麼這一章側重說遲子建小姐是想證明北極村對一個寫作者而言确有其大自然的靈氣。
大約是在一個穿着冬裝的月份,黑龍江廣播電視報社邀請了十幾位文化人,绐過他們文字上支援的撰稿者或批評家。先不開會,先不吃飯,而是看内部錄像,是美國奧利安公司1988年出品,根據米蘭·昆德拉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譯制劇情片《布拉格的春天》(又譯《布拉格之戀》、《沉重浮生》)。在一個小型審片室内,一排排沙發,一排排茶幾;沙發上坐滿我們這些被邀請來的客人;茶幾上呢,有香蕉、橘子、蘋果等,還有茶水以及可樂。這時,一個頭頂好似八角兒帽或博士帽或導演帽的女孩兒,扁扁的幅檐兒下那黑黑的大眼睛加之翹起嘴角兒的無盡笑意,那伸過來的修長胳膊一并顯示着頗帶時尚的格呢短大衣……我是由低向高先看見锃亮的高筒皮靴,才又發現沖我講話的她那洋溢青春活力的外在别緻整體形象的。
“你是李蘭頌?”她問;“我是遲子建。”又答。
我們握手。間隔一個沙發落座,沒講幾句話就看起片來。看了3個多小時。下樓,步行;在過了飯口兒的時間去飯店吃飯,連吃帶喝還唱之後散夥;印象中我給她個名片,她給我個電話号碼,在告别時。
我不知道她是如何知道我的;我知道她是在幾個特定場合才知道的。先是幾個新畢業配置設定到編輯部的女大學生在一旁議論她。“我看了Cí zhǐ jìan的小說,真棒!” C、Z、S,ch、zh、sh,弄不清就容易這樣說——茨芷建——實際應該讀Chí(遲)Zǐ(子) jìan (建)。這印象使我夠深刻的。但那時我隻膚淺地得知,北極村童話中有個女孩兒,她是以寫北極村童話而知名的遲子建。
她的處女作《沉睡的大固其固》發表于《北方文學》月刊,時間大約是在1985年初,所謂“大固其固”為鄂倫春語——出大馬哈魚的地方。這是一篇小說,講述了黑龍江大流域類似悲歡離合的民間愛情故事。北極村的姑娘寫小說,被城裡的作家們感覺到是大事情了,而作為讀者,也就是說在大衆眼裡,誰能寫誰就是寫家——詩人或歌者;就小說來講,坐在哈爾濱想寫北極村是困難的,你必須有北極村那童話般的生活,才有可能寫出或寫好北極村童話。于是,北極村童話中有個女孩兒——遲子建,帶着她的小說,來到了哈爾濱,參加了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在華夏才女蕭紅故鄉呼蘭河畔開辦的小說創作班。那是個春天。她也正是春天般的年齡,2l歲。
大水是因大山而發端和奔湧的。童話般的漠河縣漠河鄉漠河村的吸引力恰是如此。說這裡封閉、僵化、禁锢、愚昧的人是一種無知,就在遲子建成名的同時,有關該地地磁研究開始構築——中國北極村第一樓建立。距漠河縣漠河鄉漠河村向北一些約3公裡處,于1988年建立了中國科學院地球實體研究所的漠河地磁台。大水是黑龍江,大山是興安嶺;北極村呢,地磁台呢——位于北緯53°29′20″,東經122°20′30″。可想此地引人注目的程度應該說有多大?北京、三亞、漠河,中國境内設有3個地磁台;中國境外呢,在南極的長城站和中山站,中科院還設有2個地磁台⋯⋯
遲子建正是在這東亞地磁台鍊最北端骨幹點建立的區域内,在大江川和大山脈的或雪白或翠綠的時序輪回中,寫就一篇又一篇童話的。例如,中篇小說集《向着白夜旅行》、短篇小說集《白雪的墓園》、散文集《傷懷之美》等等,都不能排除她在北極村确立的生活根基,都具有如地磁台所研究的那般磁性魅力。難怪在中國首漂黑龍江文化考察體育探險隊并首漂大界河電視專題片攝制組下榻哈爾濱馬疊爾飯店時,遲子建曾前來通路,那天大胡子隊長兼導演接待了她,而我正好沒有在場,我隻看到了她留下的簽了自己名字的集子,是小說還是散文我倒忘了。正因為這一次我們失之交臂沒有見着,才有了我在本文前邊提及的不期而遇。
我最深刻地感受到丹納《藝術哲學》的博大也正是在這一點上。黑水和黑土文化,山野、平原以及都市文化,是在物質和精神互相融彙和反映中,再由專門的人才通過特别的媒介來予以揭示和傳播的。漠河地磁台從業人員的任務就是:記錄地球磁場在不同時期的細微變化,向中科院提供諸如太陽活動峰年、黑子增多引起高空電磁和地球磁場變化的資料,為空間實體和地球實體學科的研究服務,使飛彈發射、衛星升空、無線通信、地震預報、礦藏勘探保持國際領先地位。
遲子建卻用不着那些精度極高的太陽能觀測儀,她的職業是以自己的眼睛和心靈感悟這裡的人文與自然,領略和反映曆史與現實、民俗與風情,由小村落走進大都市至多也隻是把手中的筆換成電腦,而文化的積澱和文明的創造是始終由其個性包括内涵決定的。
她那樣地憤怒過,提起訴訟,走進法庭,保衛自己的審美真誠,狀告沈陽出版社庸俗包裝了她的長篇小說《晨鐘響徹黃昏》。她終于勝訴,抵制了對于自身純正樸素聲譽的亵渎和玷污,又絕非偶然。因為,她是北極村童話中那個女孩兒。
這無疑是大都市裡的污濁、恥辱,與遲子建生活過的小村落的恬靜、安甯,形成的又一種審美落差。而從幼年時就離開了父母,長期生活在外祖母旁側的她,最早是帶着黑水和黑土的芬芳寫就的《初升》《花神》《外婆》等小說,寫出了依戀的童真和深愛的親朋;至出版了跨世紀文叢個人專集《逝川》時,在這樣一個大跨度中間,如此10年裡,她所填充的所有空白,依然是積蓄在山野和都市括号裡的必然觀照,總不會脫離黑水和黑土的涵蓋,文學就是這樣不得了。
當初是作文,現在是作品;她被保送西北大學作家班就讀,繼爾又進入北京師範大學與魯迅文學院合辦的研究所學生班深造;終于成為專業作家,被評聘為一級作家。
我們等于不認識。她的作品我也讀得很少,我基本沒什麼理由寫她。我們唯一的那次見面,光在黑暗中看電視以及喧嚣中瞎應酬了,她留給我個電話号碼早已忘卻,我給她個名片,竟也換過幾回地方全無用處⋯⋯然而,我寫這部文稿的前邊部分則不能不寫北極村,寫北極村又不能不寫遲子建——她就是生長在有永遠也離不開黑水與黑土的人。
她畢竟在我們剛由撫遠傳回哈爾濱下榻馬疊爾飯店時主動來探訪過,而且在我并不認識她的情況下,她爽快熱情地向我打過招呼,我又覺得很有理由寫點對她的印象了。重要的是,我不知道,北極村屬于她的參照物呢,還是她屬于北極村的注腳;她的北極村童話一并系列小說是都市文化給予山野文化的标志性廣泛傳播呢,還是山野文化天然就是注入都市文化的新鮮血液?⋯⋯
從批評家們的态度上看,總潛移默化地帶有城市中心論的味道。其實,北極村就是個中心,否則那裡就不會建立地磁台了。物質論,辯證法,都證明了這觀點。物質文明和公德心的對等和貫通就在這裡。漠河地磁台的3名工作者,為防噪聲、以保恒溫,長年在地下作業,整日裡監測地磁偏角、水準強度等七大要素,再計算出日和月的平均值報至中科院,無任何節假日。再來看遲子建的勞作,她栖息在大都市的水泥森林裡,寫着永遠帶有北極村童話傾向的文字;她的封閉在于抗幹擾,她绐你的電話号碼總是找不到人,她抗幹擾時又不斷有新一篇力作得以發表。
兩廂對照,我開始意識到遲子建的得力點從未偏移過。文字是思維的符号,她以不停進步的優秀創作,在始終堅持自己美學認識以及哲學觀點的同時,将大都市人們的視線猶如地磁般吸引到了北極村一邊。同樣是北極村,漠河地磁台将吸引200餘位科學家前來觀測日全食現象,由中國科學院召開大型國際學術會議。遲子建的創作呢,被書刊報連續而大量地印刷出版發行,不僅有中文版,還有英文版和德文版,介評文字難以計數。
北極村童話中有個女孩兒,就是以寫北極村童話而知名的遲子建。她由外祖母啟蒙,帶着黑水與黑土的靈秀及玄秘,猶如地磁般吸引着大都市裡的人們,更為山野、平原和都市文明的融彙貫通做出了超然不群的特别奉獻,把審美的中心确立在了荒寂與繁華的多側面和多觸角上,讓不同的人們有了溝通的機緣和共識的可能。
把靜谧了解為空寂是缺乏想像;山野的人文與自然的詩篇,都市的崛起與時尚的交響,需要科學和文學搭建。與我們通路的遊壽先生從時間隧道和曆史時空走來的那種厚度形成對比,并非是淺顯卻不見得一定要有多少積澱的北極村童話中那個女孩兒,是小村落和大都市路橋相通的最直接受益者與見證者!這個人當然是首漂隊并攝制組專門要通路的遲子建了。
大興安嶺地區森林特大火災,發生在1987年5月6日,至6月2日,大火才算被徹底撲滅。從當時拍攝的衛星影像圖來看,森林過火面積大得驚人,無疑是一場新中國成立以來毀林面積最大、傷亡人數最多的火災。
那時候,我對于大興安嶺地區和黑河地區的轄縣情況不甚了解。當報告文學作家賈宏圖接到稿約而不能前往火場,要我推薦熟悉那裡狀況的作者時,我竟介紹了一位在黑河當過多年解放軍團政委的大秀才,畢竟沒能去解燃眉之急或者捉刀代筆。
我當時所在的哈爾濱日報太陽島副刊特約王忠瑜、劉子成二位作家寫了長篇連載報告文學《火的戰争》,他們随寫,我們随發。王忠瑜老先生不辭辛苦,騎自行車三兩天送一次稿;個别情節涉及省政府某部門,幾方人士展開舌戰,劉子成表現出雄辯乃至詭辯的才能,總将對方質問得啞口無言。
中國首漂黑龍江文化考察體育探險隊并首漂大界河電視專題片攝制組,始發地和大走向就是大興安嶺地區的轄縣漠河、塔河、呼瑪,而在這廣大的區域裡,昔有老金溝,今有大火災,都是知名的,令人難忘的!
在林區生活的老人都知道,林子着火,從來不燒住家戶。
但是,1987年那場森林大火,卻将漠河縣城暨西林吉鎮、圖強林業局、阿木爾林業局所在地全部燒毀。那年的6月初,森林大火剛被撲滅。國務院就決定成立了災區恢複生産重建家園上司小組及其指揮郜。
幾年來,就在首漂隊以及撮制組抵達的1993年6月26日,照相機和錄像機所能拍撮的鏡頭,已經是徹底擺脫掉火災導緻大悲慘的情境了,眼前一派嶄新畫面,失去家園的大興安嶺人民早就從痛苦中無畏地站立了起來。
漠河縣轄西林吉、圖強、勁濤三鎮,漠河、興安二鄉。境内有西林吉、圖強、阿木爾三個林業局。在當時和當地,接待首漂隊及攝制組的,與其說是旅遊局,不如說是林業局,這裡以林為主,真可謂林老大。
西林吉也叫西林集,後者為原來的稱謂。據說,西林集為鄂倫春人與他族進行貿易的場所,而西林就是指鄂倫春人。“鄂倫春實亦索倫之别部,其族皆散處内興安嶺山中,以捕獵為業。元時稱為林木中百姓,國初謂樹中人。”這是《東三省政略》所記。再以後,“樹中人”演化為“栖林人”,也還有麒麟、乞林、齊淩等叫法。所有這些都足以說明在當地人心目中林的重要,林就是人,人等于林!誰能想到,漠河縣城西林吉鎮方圓數十裡的森林都被大火燒光了。
救命河!這真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圖強鎮南有一條不知道流淌了多少年的阿木爾河,現在被當地人稱為救命河了!都說水火無情,可是,1987年5月6日至7日,這條阿木爾河,這剛從凍土狀态中蘇醒的河床、淺灘、坡坎,幾乎救了全圖強人的命!
萬餘名圖強人都集中在這裡避大火,有的是一家人,有的并不知道自己能否再見到親人?饑餓,寒冷,人們在夜色中看着沖天的火光,盼天明更盼着火快滅⋯⋯以後,每年的5月7日,圖強人都會到這裡來,向阿木爾河裡,向這救命河裡,投食品,作祭奠,還要照幾張像⋯⋯小橋上,大壩上,都是不約而同前來祭奠的圖強人。
大火中有210人被燒死,卻在25天裡,也有34個嬰兒剛好降生,這些孩子又都取了同樣的名字:火生。這是難得的,更是難忘的,每一個小火生都有着各自在大火中誕生的傳奇故事。他,大名劉然,小名火生,名字就是由一名記者給取的,而這孩子無論如何也難以記起火生的艱辛甚至恐怖。那殘垣斷壁,那焦土枯木,絕不是常人所能想像到的,僅僅是一個火星,一個煙頭。大森林頃刻間會出現如此的窘迫狀,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在勁濤鎮,中學女教師徐廣輝分娩,生下了兒子郭火生。母子倆是在大火中被送進停電的醫院的,助産士甯玉宴正當班,用她的話說,當時真是—手托着兩個生命,即使大火加停電也絲毫輕率不得。甯玉宴和另幾個人擡着在危急中的徐廣輝,迅疾地奔跑在醫院的樓梯上不慎将腰部扭傷,直到今天落下終身殘疾,住樓房三伏天也必須睡火炕。顯然,當地人現在的居住條件普遍比以前好多了,但這又是多麼巨大的代價換取的呢。人們甯可不住或者更晚一些住磚房以及樓廈,也絕不願意用森林大火來作更新緣起。
火災起火點揭示牌上寫着民工汪玉峰的名字。這好像是一個恥辱柱。正是這個大森林中的違法吸煙者,成為發生特大火災的一個罪魁禍首。他被判處了有期徒刑8年,要知道啊,大興安嶺的哪一棵樹,從幼苗長成材需要80年呢!
這是悲劇,這悲劇令人痛心疾首。我們把這火災起火點揭示牌多懸挂一些地方吧,以向那些損人不利已的吸煙者——時時、處處敲響警鐘。汪玉峰的一個煙頭,一個煙頭呀,竟成為這特大火災的幾個起火點之一,而由此導緻森林大火燒毀的直接或者間接的損失該如何同記得精确呢?!
大界河第一災。有備而來的首漂隊及攝制組成員還是在“五六” 火災紀念館内外驚呆了。正是那一次震驚中外的森林大火,燒毀了大興安嶺地區近五分之一的有林地,40萬公頃重度過火林地的森林,一時間在地球上化為烏有了。
1987年5月6日,漠河和塔河兩線驟然起火。西部的漠河,大風足有8級以上,7日晚,5個小時内火頭推進100公裡,公路、鐵道、橋梁、河流,乃至于500公尺寬的防火隔離帶,這一切的一切,都阻擋不住火勢的擴充。
西林吉、圖強、阿木爾林業局所在地以及9個林場、4個半貯木場,僅在十幾個小時内就被大火完全吞噬。東部的塔河,也有盤古林場火勢迅猛異常。至8日,從西部的漠河到東部的塔河,在如此之大的跨度間,巳經形成幾十萬公頃面積的火海,而且此後火勢仍在不停蔓延,直到6月2日,前後25天了,大火才被徹底撲滅。
下列數字可以證明,這場森林大火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毀林面積最大、傷亡人數最多的一次。據權威部門統計,直接損失為:過火面積10l萬公頃,其中有林面積70萬公頃;燒毀貯木場存材85萬立方米;房屋61.4萬平方米,其中民房40萬平方米;受災群衆的10807戶、56092人;死亡210人,受傷266人,野生動物資源損失20%。
無頭的樹杆,焦糊的樹樁。連小鳥都不屑一顧的枯枝敗葉朽木死樹,加之沒能及時運走的大量木材腐爛報廢,⋯⋯這凄涼的景象真比看統計數字還要令人寒心!
“眼前這片荒山秃嶺在大火災沒發生時是一片挺拔的林木。那時候在咱這山溝裡風很小,你再看現在這大風,都說明生态平衡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這是大自然的無情報複呀!⋯⋯”任何一個大興安嶺人都能夠對來訪者講出這番話的。
我們很難知道這片土地是在什麼時候有的大森林。1965年,大陸政府決定正式開發大興安嶺。這裡是大陸最重要的木材生産基地,盛産落葉松、樟子松、白桦等木材林。在這裡,一棵小樹要生長50多年才能基本成材,可見生産周期之漫長。“綠色明珠”、“綠色寶石”,是文學家贊美大興安嶺林區的比喻,這比喻在100多萬公頃的土地上,一瞬間成為了無盡的火海。
以漠河鄉北極村為标志,在現行中國版圖上這裡顯然是最北端,且年年平均氣溫最低,無霜期很短暫,而黑龍江北岸則是現在的俄羅斯聯邦共和國了。距漠河縣城17公裡處圖強林業局所在地圖強鎮北面山坡,在大火災之前,人們的視野内全是碗口粗胸徑、兩三層樓高樹杆的樟子松林,就在漠河縣城被大火燒毀的幾十分鐘以後,大火把圖強鎮北面山坡上的森林也很快燒光了,可是,人們竟發現山頂上有一塊與衆不同的大石頭。
據林業專家分析,從類似樹木的紋絡來看,很像現在的木材,假如這些石塊是古化石,則證明大興安嶺在遠古時代氣溫是較高的,滿山長着别的植物或者高大的樹木,由于地殼變遷,在第幾個冰河時期,使得刺的植物或者樹木死亡了,又由于沉積或者其他原因變成了化石,是以我們判斷,整個大興安嶺在遠古時期應該是比較好的氣候環境,不過,這一判斷有待得到驗證。
這裡在遠古時是否曆盡滄桑尚待考證,讓今天的火災區重穿綠裝卻是當務之急。大興安嶺地區過去是一片天然的原始森林,很多樹木能夠在這裡生生不息,靠的是樹木自身的繁殖能力。也就是說,每到秋天樹木的果實可以随着風飄到任何一個地方,在來年的春天生根發芽。
大火災後,大興安嶺地區許多地方遭到毀滅性破壞,在很大的範圍内連一棵結果實的母樹都看不到,那麼,怎樣才能找到适應樹種,盡快地恢複森林面積,人工造林就是一個根本的辦法。大興安嶺人開始把營林擺在了基礎地位上,加大了管林工作的力度,一改過去重采輕育錯誤做法,盡快搞好恢複火災區森林資源的工作。
從1965年開發大興安嶺至今,這裡的木材總采伐量已經十分有限,人們的衣食住行等經濟來源都和木材緊密相關。大火災後,人們對森林資源的認識觀念大有變化,當時的直接經濟損失為人民币5億元,而生态系統的被破壞是無法用數字統計的。從以采伐為主的林場場長到以栽種為主的管林局長,幾個類似的大興安嶺的硬漢表示,過去伐倒了多少棵樹現在栽種它多少棵樹!
“碧洲苗圃”,看啊,雙雙奉獻,苦苦奮鬥,張美鈞和林淑雲夫婦,為了解決大興安嶺樹種比較少的問題,讓西伯利亞優質紅松落戶大興安嶺,現在終于有了挺大盼頭兒。1965年,與大興安嶺開發時間相同的這一對山東農學院林學系畢業生,在這裡深深紮下了根,為了讓大興安嶺閑置荒地以及過火林地都能生長林木,他們二人發明的三防造地法和雪藏苗木過冬法,巳經在大興安嶺所有林業局推廣使用。
即使是勞作在國境線上、大界河旁,張美鈞隻出過一次國,是去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西伯利亞。他從那裡背回了1500棵西伯利亞優質紅松樹苗,為了讓這批樹苗在大興安嶺生根,長成參天大樹,他們情願獻出畢生精力,退休以後也繼續幹。
空前的劫難,空前的搶救。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大興安嶺森林資源的保護與再生,明确提出要用8至9年的時間完成火燒迹地森林資源的恢複事宜。大興安嶺人向林海腹地發出挑戰。他們為了不辱使命,以最新組建的營林大軍開赴深山,春植、夏育、秋整、冬清,在寒溫帶人工造林無法成活的禁區;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迹。
恢複森林資源,首先要有苗木,從漠河到塔河的4個林業局陸續擴建了130.2公頃的育苗基地,興辦起ll處林間苗圃以及68處家庭苗圃,進而使總育苗面積達189.2公頃,可年産上山苗14067萬株。于是,我們看到,大大燒不去的綠色風景,是那樣的神奇和壯美,充滿着希望!
以更新合格率92.4%的紀錄,在營造森林資源964329公頃的同時,大興安嶺人的眼界和心境也随之更為開闊了。
我們沒有把火災發生時人們慘痛悲壯的故事一個一個地翻出來再作叙述的那種必要,卻實在應該将火災之後恢複生産重建家園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例編輯成特寫集出版發行。首漂隊,攝制組,再次把鏡頭拉回到建于漠河縣城的“五六”火災紀念館:燒壞的縫紉機、燒化的玻璃、燒變形的高壓鍋、燒毀的汽車⋯⋯
張子揚針對這裡的情形發表了如下感言,他這樣講道:
漠河還有一件世界出名的事,就是前幾年大興安嶺發生的大火災。1987年5月6日那場大火,可以說,把這個地方最古老的東西部給燒沒了。這也是一種思考,古老的東西,不光是一種自然景觀,或我們看到的人文景觀,還有一種我們看不到的某些觀念的東西。
是以,采訪時特别有意思,他們那個副縣長就說:大火把我們這兒的女人都燒“浪”了,把男人燒“胖”了,小城呢,越燒越漂亮了。為什麼呢,這是因為,經過一場生死劫難,人們都想明白了,錢不能存。女的呢,有錢就穿起來;男的呢,有錢就該吃該喝;再有就是舊的景觀一切皆無,重造新的,整個城市的規化也比較好了。
我們就拍一些小城的風貌和“五六”火災紀念館。我覺得很有意義,它講了毀滅資源、傷亡人數等,看起來很恐怖。中國本來自然資源就不是很多,生态平衡幾經破壞,再加上人為的因素很多,反正這個片子帶有些憂患意識。我們到他們公園裡看到松樹苗隻有半尺左右,松樹真正長成需要60年,要成大材得近百年,人的一生也不過就80年至多90年這麼長。剛好,公園湖裡有小孩劃船玩,我們就現場采坊,問當時“你在哪兒呀”“你看沒有看展覽呀”,小孩很小,他回答說,當時被解放軍救走了,但一看照片什麼的都很難過,小孩很自然的哽咽的說一些事情。
我覺得呢,這些東西記錄下來,如果能編好,我覺得它還是很真實的,人本能地對一些災難的畏懼、恐怖,這也是對我們自身的一種警醒。這是在小城拍的一些情況。
是的,一個城鎮的毀滅可以在幾小時内發生,在當今中國一個城鎮的重建也并非難上加難。然而,在當年3500多戶西林吉鎮居民的心中,一根火柴,一個煙頭,都意味着是重大隐患,是以,每個公民于心靈深處的那種覺醒和自律就比任何毀滅和重建都罕見了。
1987年5月7日18時,漠河縣城西林吉鎮火燒連營,一切的一切都燃燒着,能着的都着了,鋼筋水泥不易燃也被燒酥了、熔化了,更有貯木場、木闆柈棚助燃,大火過後全城建築十之有九變成度墟,據說,隻有11幢樓房還算保留住個模樣,大片民宅都被燒得剩下個影孤形單的煙囪了,一個個煙囪林立着,甚是恐怖。
恢複生産重建家園就在這廢墟上,幾年的光景,漠河縣城西林吉鎮樓廈群起,道橋通暢,在建立的52.4萬平方米的房舍中,有民宅41.3萬平方米,每戶居民平均足有50平方來的住房。
可是,大興安嶺人,尤其包括親曆過大火災的漠河人和塔河人,他們絕不滿足于自己小家的安居,而一定要在這一代人手中重新營造起大森林,哪怕還隻是幼苗,還須在50年甚至100年後成材,也要恢複,也要重建,因為,這是,大火燒不去的綠色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