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下半年,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意蔓延,正當人們不斷為疫情受到的影響和限制而苦惱之際,一個帶着科技神話性質的新事物“元宇宙”橫空出世。這個超越于現實世界,又與現實世界平行的虛拟新世界“元宇宙”的誕生,讓一年多來精神上倍感壓抑和煩躁的全球網民為之振奮。
元宇宙(Metaverse),是出自尼爾 斯蒂芬森1992年的科幻小說《雪崩》裡的一個名詞,其實它本身不是一項新科技,而是一個概念或者理念。是一個整合了人工智能、數字孿生、區塊鍊、雲計算、拓展現實、機器人、腦機接口、5G等多種技術于一身的平台。它無限開放,特别強調虛實相融,具有沉浸式體驗、虛拟化分身、開放式創造、強社交屬性等基本特征,是一個巨大的技術彙集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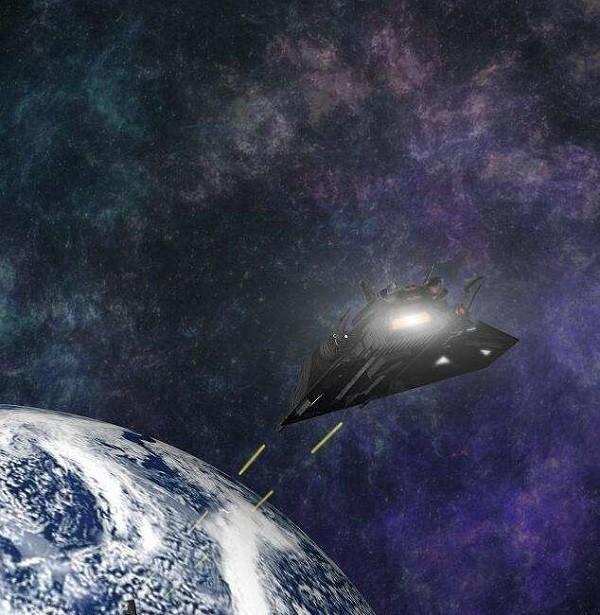
2021年10月,随着Facebook正式更名為Meta,并宣稱将在五年内轉型成為“元宇宙(Metaverse)”公司,由此引發全球強烈震動。元宇宙成為繼NFT藝術之後,2021年下半年各大媒體與社會各界最為高頻和熱點的話題。對于元宇宙的未來,以及它對人類的影響和意義至今尚無定論,也未達成共識。盡管衆說紛纭,但有一個現實已經不容置疑地擺在我們所有人的面前。那就是以元宇宙為代表的新科學、新技術、新材料和新動力正在成為人類生命的體外延伸,将以不可思議的廣度、深度和速度改變人類文明的程序。
應當說,科學與藝術是人類創造性地把握世界的兩種方式。通常來說,科學是理性的,以尋求真理,提煉客觀規律見長;而藝術則是感性的,以追求真善美為精神宗旨,不斷開拓人類的思維疆域。但無論是科學發明還是藝術創造,他們彼此之間可以互相激發。在人類發展史上,科學發現、方法和知識等經常會對藝術産生影響,而藝術的想象力與創造力反過來也對科學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是以,盡管元宇宙目前尚處在初始階段,但VR藝術、遊戲美術、AI藝術、沉浸式藝術和NFT藝術等與元宇宙相關的各種新潮藝術如雨後春筍,紛紛湧現。尤其是以數字藝術為基礎的NFT藝術,眼下正在成為炙手可熱的藝術和資本的新寵。
事實上,回看曆史,不難發現,新技術與藝術之間有着一種複雜關聯。然而,在相當長時間裡,技術對藝術的影響是十分有限的。比如文藝複興時期,由于透視法、光影和解剖等科學技術的運用,使得西方繪畫形成了一整套觀察自然和構造畫面的規則與方法,建立了西方繪畫的古典語言體系。但無論是透視法,還是光影和解剖,它們的技術性都消融在繪畫中,并不與繪畫藝術形成緊張與沖突。不過,從攝影與電影開始,現代技術成為藝術中的關鍵性成分,并使藝術呈現出與原有藝術形态不同的特征。比如,攝影術曾經催生出印象派;計算機的出現和消費主義的盛行讓波普藝術走向世界舞台;網際網路的大規模普及直接帶來了網絡藝術的興起,讓數字藝術、影像裝置藝術成為當代藝術的主流。
在技術越來越占據支配地位的今天,人的生命經驗和感受方式都将被重新塑造。眼下,技術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文化的主體,集合了多種技術的元宇宙能量更為巨大,具有某種壓倒性優勢的力量,它正在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表征。那麼,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藝術是技術的同道還是抵抗?
技術決定論的代表人物阿諾德·蓋倫認為,人類通過技術而彌補了自身直覺的缺陷,因而技術成為了人的器官的延長和替代,實作了人的自然本性的可塑性。但實際上,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傾向于漠視人的身體,退化人的感覺,讓人的自然能力加速下降。比如随着智能化技術的提高與普及,我們從當初的敲擊鍵盤,到如今的點選滑鼠或觸摸螢幕,到以後的隻需要大腦發指令,身體機能的使用越來越少。應當說,元宇宙時代,過份依重人的智力,嚴重忽視人的身體機能和各種感官,對于人的全面發展和存在狀态而言,那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全面的,更是不健康的。藝術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在于恢複人的感覺,以及感覺與感覺之間的關聯性,并充分發揮人的直覺、靈感和想象。
心理學家謝裡·特爾克說“科技是人類的‘第二自我’”。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是人的延伸。他指出了媒介對于日常生活的改變與塑造作用,并強調真正發揮作用的因素并非媒介所傳播的内容,而是媒介的技術形式,正是後者塑造了人類感覺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随着技術本身的加速度更新換代,它對于社會和文化形态的改變和塑造也在以更為深刻和隐秘的方式展開。尼爾·波茲曼說:“在觀念的殘垣斷壁之中,隻剩下一個可以相信的東西——技術”。對此,麥克盧漢指出,要與媒介保持距離。他提醒人們在最初的接觸之時就要注意技術的誘惑,以防陷入“自戀昏迷狀态”。那麼我們能否獲得麥克盧漢所謂的“預見和控制媒介”的能力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為我們每個人并不是都可以做到如此理性地看待媒介,而不被卷入其中。唯一的希望也許就是藝術,因為前衛的藝術實踐從一開始就是超越目的性的“遊戲”,是超越功能和功利的。藝術需要激情,更重要深度的反思,而敢于去探索和開拓新的文化,正是當代藝術的精神底色。
海德格爾曾說:“盲目拒斥現代技術是愚蠢的,而是要改變和現代技術的關系。”他認為要進行一種“現象學懸置”。即改變主體性,泰然任之,既不是主動也不是被動,采取與意志無關的态度,同時對現代技術要說“是”與“不是”,“是”需要使用現代技術,但“不是”被現代技術所獨占。的确,元宇宙是一個中介,一個平台。如果說元宇宙是無法阻擋的曆史趨勢,那麼對于藝術創作而言,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種媒介,一種手段,進而助力各種新媒體藝術開拓出一個新的表現領域。
誠然,面對新技術的誘惑,很多當代藝術家的态度是樂觀而積極的,他們熱情地接受新的技術手段,并用于新的藝術實踐。但我們也清楚地看到,由于受到技術決定論的影響,以及遊戲的思維狀态,他們的藝術創作很可能發展成一種精緻的形式主義。如果當代藝術的實踐變成了藝術的娛樂,作品和展覽就變成了追求感官刺激的遊樂設施和娛樂場。更有甚者,精緻的形式主義變成了功利的形式主義,除了日益追求更加亂真和整體性的感官刺激之外,并沒有提供新的思想,不過是把新技術當作一種政策,作為作品華麗的包裝。毋庸諱言,這種狀況,在如今很多打着互動與沉浸式體驗口号的新媒體藝術展上,比比皆是。
元宇宙帶來的沖擊是全方位的。比如說,無論是杜尚,還是博伊斯,他們對藝術史的功績主要在于極大地擴充了藝術的概念,把藝術從少數幾種材料中解放出來,成為綜合材料的藝術,總體的藝術。但元宇宙,又讓人類退回到主要靠數字這樣單一媒介的時代。并且,人和萬物一樣,都簡化為一種數字化的存在。流量為王,資料成為唯一的考量依據,成為技術時代的縮影。這就意味着,在數字技術面前,我們每個人都是同質化的個體,真正成了馬爾庫塞所謂的那種“單面人”。于是乎,凡是非主流的邊緣性思想精神和文化藝術都将失去生存的空間與機會。而精神一旦成為單次元的東西,人類就會喪失精神的多元度和豐富性,世界就會不可避免地走向貧乏,走向同質化和平庸化。
當下,藝術的使命在于抵禦平庸,抵抗貧乏,因為藝術是一種異質性的力量。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當代藝術是對技術時代的一種修正和糾偏。阿多諾說,隻能通過抵抗社會,藝術才能獲得生命。博伊斯說,藝術不隻是抵抗,而是重塑和改造社會的力量。基弗說,“抵抗”是普遍性的。的确,世界處處有抵抗,人生處處要抵抗。(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