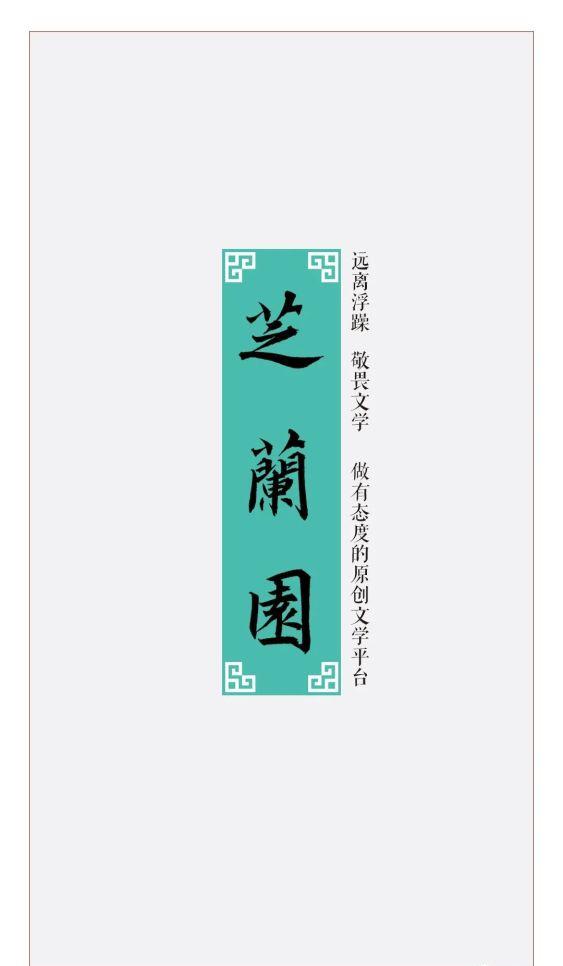
原創首發 侵權必究
元宵節憶燈
□劉甯/ 文
元宵節是我們國人曆來非常重視的傳統節日,除了吃元宵,節日的重點主要在觀燈。
古人在描述元宵節時,不僅有“元宵争看采蓮船,寶馬香車拾墜钿”的繁華熱鬧,有“缛彩遙分地,繁光遠綴天”的光怪陸離,也有“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美好恬靜,更有“衆裡尋他千百度,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小歡喜。從這些詩句中來看,元宵節似乎更是一個狂歡的節日,一個釋放的節日,一個“情人節”。
作為現代人的我們,雖不能身臨其境感受古人過節的熱鬧氣息,但在傳統文化的濡染下,一樣沐浴着節日的福澤。即使是在條件較為艱難的80年代初,地處豫北平原的安陽百姓也絲毫不會拉下這個重要節日。那會國家的經濟基礎還較為薄弱,買糧要有糧票,買肉要有肉票,買布得有布票,買煤要有煤票。小孩子平時吃不着好吃的,自然眼巴巴盼着過年,才有糖吃、有肉吃、有新衣新鞋子穿。我家在偏僻的農村,條件也不好。新衣新鞋買不起,母親就買了布料給我們做;再割二斤肉,肥肉用來炸油,瘦肉用來包餃子,于我家已算是好生活了。
到了正月十五元宵節鬧花燈的夜晚,本是日落而息、倒頭酣睡的時候,但元宵之時,人們卻有不眠不休的興緻。天剛擦黑,前街後院處處洋溢着小孩子玩“燈籠會”的歡笑聲。囿于家庭貧困,印象中母親也曾買過兩回很廉價的紙燈籠,當我們姐妹稍稍長大點,打燈籠就與我們無緣了。那時候,我大概上國小二年級了,特别豔羨鄰居小姐妹擁有的漂亮彩燈籠。可是家貧沒錢買,怎麼辦?我隻好從一堆白菜中挑選最大個的白菜根,切下來後挖空根的中間部分。先得尋個粗點的棉線擱到蠟油正中當燈芯,再慢慢滴上八分滿的蠟燭油。随後,又從犄角旮旯裡找來一根粗鐵絲,懸挂在白菜根的兩側,挑選一根半米長的趁手小木棍,用細鐵絲綁定後就可以點燃棉燈芯當燈籠了。在村裡的主街上,我挑着自己的DIY作品,屁颠屁颠地跟在小夥伴們五彩燈籠後邊跑呀鬧呀,雖然它不是最好看的,但得到的歡樂是一樣的。小夥伴也有攀比心,誰家的燈籠美觀,也會羨慕半天。有些調皮的孩子,甚至故意用自家的燈籠和别家小孩子的燈籠“單挑”,“哄”一聲,倆燈籠被引燃了,剩下一群孩子的歡笑蕩漾在夜的海洋裡。“燈籠會燈籠會,燈籠滅了回家睡。”直到油盡燈滅,小夥伴們才戀戀不舍地各自回家。
再大點,城裡就相繼建起好多工廠。有造紙廠、電筒廠、紗廠、織染廠、啤酒廠、火柴廠、煙廠、地毯廠等。日子好些了,老百姓過元宵節就不止于玩小孩子的“燈籠會”了。印象中,我随母親還特意跑到南關體育廠那條路上,看全市各企事機關精心準備的“燈籠展會”了:有跑旱船的,有演農村老頭老太反串節目的,有演豬八戒的,有擡花轎的,有擡閣,也有背閣。最引人注目的,是各工廠制作的形态各異的大燈籠。燈籠都在木制的車上裝着,車上鋪着紅紅綠綠的綢子,燈籠樣式繁多,令人耳目一新。多少年過去了,已過四十不惑的我,想到那時盛況空前的場面,一樣心潮澎湃,燈會如在昨天。幾乎全城的老百姓傾城出動,全都來看花燈了,用摩肩接踵、水洩不通來比喻也絲毫不誇張。
多年後,在市場經濟浪潮下,不少工廠相繼倒閉了。取而代之的是電商和微商的快速崛起。前幾年元宵節,我陸續給外甥女買了各式各樣的燈籠,除了傳統的方燈籠、圓燈籠外,還增加了芭比娃娃燈籠、電子音樂燈籠等等。随着生活條件的好轉,花樣翻新的燈籠讓人目不暇接。想購買什麼樣的燈籠,鬧市上買不到的網上可以訂購。燈籠樣式越發多了,但生活中的“燈籠會”卻不見了蹤影。現在的小朋友更多是在家關了電燈後,體驗元宵節“燈籠會”的樂趣。令人欣慰的是,城區主幹道的樹上和網紅街總會懸挂很多古樸雅緻的大紅燈籠,在清冷寂靜的冬夜總那麼撩人。因為有了這些“不忘初心”“中國夢”的心形、圓形燈籠而令行人心生溫暖,感受到了元宵節的濃濃年味。
元宵節燈籠的變化,是時代發展的縮影,映照着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變遷的步伐和脈絡。年味雖然淡了,但生活條件着實變好了。以前想要的物品,小到一個紙糊的燈籠,也隻有等到新年才可能滿足願望,但随着網際網路和快遞行業的迅速發展,讓夢想變得觸手可及。
記得陳之藩在《劍橋倒影》中說:“許多許多的曆史,才可以培養一點點傳統,許多許多的傳統,才可以培養一點點文化。”真的要感謝傳統文化,讓我們所眷念的人間溫情,不僅可在古代詩詞中領略,更可在煙火塵世裡體悟。也不得不感謝燈籠、燈展,是它讓黑暗的夜有了光明和希望,讓傳統節日更加多姿多彩,讓生活更加活色生香,也讓我們的回憶與愛戀有所寄托。
此刻,熱氣騰騰的元宵正在鍋裡沸騰着,廣播、電視裡各地鬧元宵的聲音不斷傳來,我被這份節日歡樂的氛圍濡染着,被疫情消散後人們複工複産的速度驚豔着,為燈籠會的變遷欣喜着。有幸生于和平昌盛的年代,體驗這來之不易的幸福,年味雖淡,但暖在心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