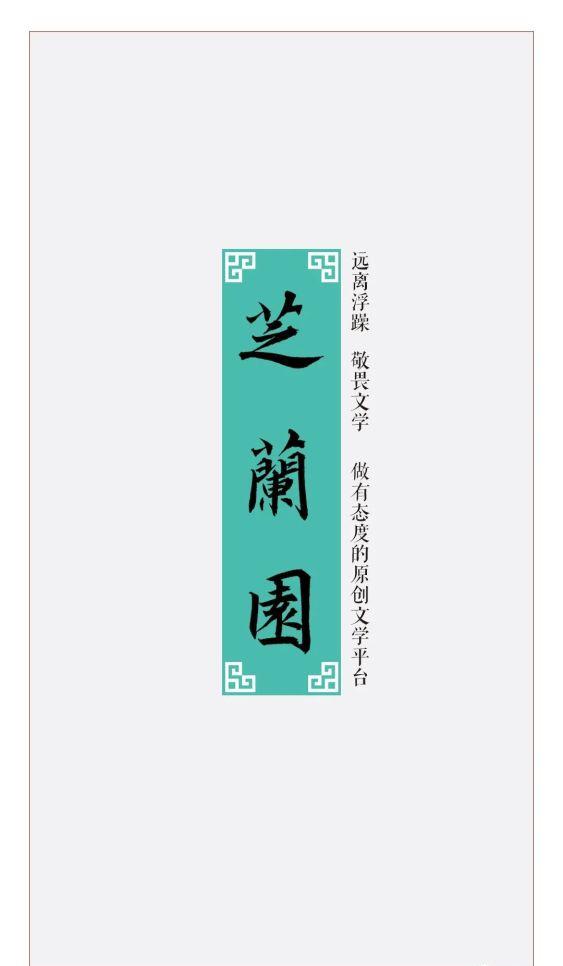
原创首发 侵权必究
元宵节忆灯
□刘宁/ 文
元宵节是我们国人历来非常重视的传统节日,除了吃元宵,节日的重点主要在观灯。
古人在描述元宵节时,不仅有“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的繁华热闹,有“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的光怪陆离,也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美好恬静,更有“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小欢喜。从这些诗句中来看,元宵节似乎更是一个狂欢的节日,一个释放的节日,一个“情人节”。
作为现代人的我们,虽不能身临其境感受古人过节的热闹气息,但在传统文化的濡染下,一样沐浴着节日的福泽。即使是在条件较为艰难的80年代初,地处豫北平原的安阳百姓也丝毫不会拉下这个重要节日。那会国家的经济基础还较为薄弱,买粮要有粮票,买肉要有肉票,买布得有布票,买煤要有煤票。小孩子平时吃不着好吃的,自然眼巴巴盼着过年,才有糖吃、有肉吃、有新衣新鞋子穿。我家在偏僻的农村,条件也不好。新衣新鞋买不起,母亲就买了布料给我们做;再割二斤肉,肥肉用来炸油,瘦肉用来包饺子,于我家已算是好生活了。
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闹花灯的夜晚,本是日落而息、倒头酣睡的时候,但元宵之时,人们却有不眠不休的兴致。天刚擦黑,前街后院处处洋溢着小孩子玩“灯笼会”的欢笑声。囿于家庭贫困,印象中母亲也曾买过两回很廉价的纸灯笼,当我们姐妹稍稍长大点,打灯笼就与我们无缘了。那时候,我大概上小学二年级了,特别艳羡邻居小姐妹拥有的漂亮彩灯笼。可是家贫没钱买,怎么办?我只好从一堆白菜中挑选最大个的白菜根,切下来后挖空根的中间部分。先得寻个粗点的棉线搁到蜡油正中当灯芯,再慢慢滴上八分满的蜡烛油。随后,又从犄角旮旯里找来一根粗铁丝,悬挂在白菜根的两侧,挑选一根半米长的趁手小木棍,用细铁丝绑定后就可以点燃棉灯芯当灯笼了。在村里的主街上,我挑着自己的DIY作品,屁颠屁颠地跟在小伙伴们五彩灯笼后边跑呀闹呀,虽然它不是最好看的,但得到的欢乐是一样的。小伙伴也有攀比心,谁家的灯笼美观,也会羡慕半天。有些调皮的孩子,甚至故意用自家的灯笼和别家小孩子的灯笼“单挑”,“哄”一声,俩灯笼被引燃了,剩下一群孩子的欢笑荡漾在夜的海洋里。“灯笼会灯笼会,灯笼灭了回家睡。”直到油尽灯灭,小伙伴们才恋恋不舍地各自回家。
再大点,城里就相继建起好多工厂。有造纸厂、电筒厂、纱厂、织染厂、啤酒厂、火柴厂、烟厂、地毯厂等。日子好些了,老百姓过元宵节就不止于玩小孩子的“灯笼会”了。印象中,我随母亲还特意跑到南关体育厂那条路上,看全市各企事单位精心准备的“灯笼展会”了:有跑旱船的,有演农村老头老太反串节目的,有演猪八戒的,有抬花轿的,有抬阁,也有背阁。最引人注目的,是各工厂制作的形态各异的大灯笼。灯笼都在木制的车上装着,车上铺着红红绿绿的绸子,灯笼样式繁多,令人耳目一新。多少年过去了,已过四十不惑的我,想到那时盛况空前的场面,一样心潮澎湃,灯会如在昨天。几乎全城的老百姓倾城出动,全都来看花灯了,用摩肩接踵、水泄不通来比喻也丝毫不夸张。
多年后,在市场经济浪潮下,不少工厂相继倒闭了。取而代之的是电商和微商的快速崛起。前几年元宵节,我陆续给外甥女买了各式各样的灯笼,除了传统的方灯笼、圆灯笼外,还增加了芭比娃娃灯笼、电子音乐灯笼等等。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花样翻新的灯笼让人目不暇接。想购买什么样的灯笼,闹市上买不到的网上可以订购。灯笼样式越发多了,但生活中的“灯笼会”却不见了踪影。现在的小朋友更多是在家关了电灯后,体验元宵节“灯笼会”的乐趣。令人欣慰的是,城区主干道的树上和网红街总会悬挂很多古朴雅致的大红灯笼,在清冷寂静的冬夜总那么撩人。因为有了这些“不忘初心”“中国梦”的心形、圆形灯笼而令行人心生温暖,感受到了元宵节的浓浓年味。
元宵节灯笼的变化,是时代发展的缩影,映照着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变迁的步伐和脉络。年味虽然淡了,但生活条件着实变好了。以前想要的物品,小到一个纸糊的灯笼,也只有等到新年才可能满足愿望,但随着互联网和快递行业的迅速发展,让梦想变得触手可及。
记得陈之藩在《剑桥倒影》中说:“许多许多的历史,才可以培养一点点传统,许多许多的传统,才可以培养一点点文化。”真的要感谢传统文化,让我们所眷念的人间温情,不仅可在古代诗词中领略,更可在烟火尘世里体悟。也不得不感谢灯笼、灯展,是它让黑暗的夜有了光明和希望,让传统节日更加多姿多彩,让生活更加活色生香,也让我们的回忆与爱恋有所寄托。
此刻,热气腾腾的元宵正在锅里沸腾着,广播、电视里各地闹元宵的声音不断传来,我被这份节日欢乐的氛围濡染着,被疫情消散后人们复工复产的速度惊艳着,为灯笼会的变迁欣喜着。有幸生于和平昌盛的年代,体验这来之不易的幸福,年味虽淡,但暖在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