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鵬
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傅偉芬
上海市進階人民法院幹部
要目
一、問題的提出
二、兜底條款與類推适用
三、預重整規範、指引的類型劃分與适用
結論
企業進入預重整程式後,雖存在着解除财産保全和中止執行程式的實際需求,但現行法律與司法解釋尚未對此進行直接和明确的規定,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雖設有兜底條款,但不能适用在預重整程式中。法律未對解除财産保全或中止執行程式在預重整中的适用進行規定,并不意味着存在法律漏洞,不宜類推适用破産法中的相關條文作為法律依據。依據法院是否應當在預重整程式中解除财産保全和中止執行程式,可将地方法院關于預重整的規範或指引分為剛性和柔性兩類。剛性的規範或指引明确規定了法院應當在預重整程式中解除财産保全和中止執行程式;柔性的規範或指引賦予了當事人和解和談判的空間,将和解或執行和解作為财産保全解除和執行中止的依據。如以立法法作為衡量的标尺,柔性的規範或指引更為可取,剛性的規範或指引可能會違反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在适用剛性的規範或指引時,可在财産保全解除和執行中止前,促使當事人達成和解或執行和解,充分發揮法院的協調能力以及府院關聯的效果,以市場化的預重整制度為路徑,把規範或指引真正地當成“指引”而不是法律來适用,這既有助于法院做出的裁定具有更加紮實的法律依據,亦能降低規範、指引的相關條款違反立法法第8條的風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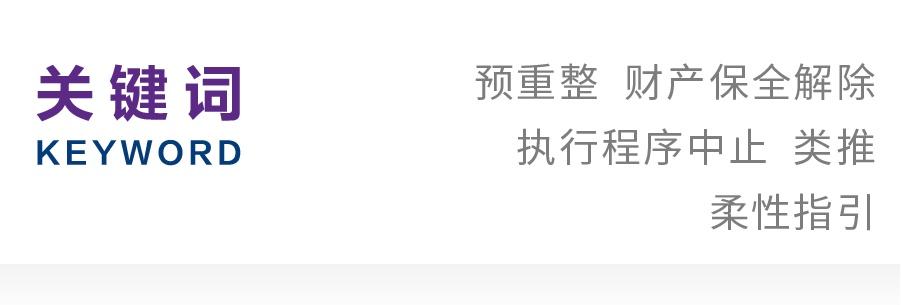
預重整程式,系指在申請重整之前,債務人與債權人通過法庭外協商制定重整計劃,并獲得多數債權人同意後,借助重整程式使重整計劃發生限制全體債權人的效力,早日實作債務人複興的一種拯救機制。依據這一機制和程式,債務人和債權人在重整程式前,就已經通過預先的協商,制定了未來的重整計劃,一旦進入重整程式,法院隻需要準許重整計劃,債務人就能進入到重整計劃的執行階段。預重整制度具有節省重整成本、確定更真實呈現企業價值、提升重整程式品質,以及盡早開展企業拯救的功能。
對于希望通過預重整制度保護自己的債務人,如果已具備了重整原因,常常已被官司纏身,随之而來的财産保全和強制執行,都可能成為壓垮債務人的最後一根稻草。胡利玲教授指出,債務人具備重整原因,系具備啟動預重整程式的标準之一。大陸企業破産法對于重整原因的界定已足夠寬泛,預重整的原因不必再放寬,直接依照現行的重整原因即可。已具備重整原因的債務人,利用重整程式化解财産保全和執行風險的需求同樣存在。例如,在溫州吉爾達鞋業有限公司預重整案中,債務人由于擔保問題陸續被多家銀行起訴,導緻銀行賬戶、固定資産被法院查封、當機,如法院繼續執行,将導緻吉爾達公司無法正常生産經營,使債權人利益得不到最大化,也将使得重整工作無法進行。
此外,預重整制度可以克服破産重整制度與法庭外重組制度各自的不足,是一種兼具非司法和司法拯救内容的混合型拯救程式。對于法庭外重組而言,債務人仍會面臨着财産被查封或執行的風險。如果希望預重整程式發揮出法庭外重組不具備的功能,就必須去面對和解決預重整程式中存在的财産保全和執行問題。
對于預重整程式中财産保全解除和執行程式中止,學界有一說認為:财産保全解除和執行程式中止隻有在正式的破産程式中才具有效力。但是,先行研究針對現行法律、司法解釋,以及各地法院關于預重整制度的規範或指引的解釋論研究,尚未充分展開。從解釋論的角度來考察,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
第一,在預重整實務中,《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民訴法解釋)第166條、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訴法)第256條關于解除财産保全、中止執行程式的兜底條款,是否可以作為法院解除财産保全和中止執行程式的依據?第二,是否可以類推适用企業破産法(以下簡稱破産法)第19條之規定,在預重整程式中解除财産保全和中止執行程式?第三,地方法院制定的破産案件審理規範或指引中,關于财産保全解除和執行程式中止的規定,存在着不同的類型。如以立法法作為标尺與紅線,應如何評價和适用這些規範和指引?
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從解釋論的角度,借助法學方法論作為主要分析工具,對預重整程式中的财産保全解除和執行程式中止的适用問題進行分析,以期對預重整制度相關的理論研究與實務應用有所助益。
兜底條款的解釋與适用
在預重整程式中,法院是否可以或應當解除财産保全,現行法律與法規并沒有明确規定。民訴法解釋第166條規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作出解除保全裁定:(一)保全錯誤的;(二)申請人撤回保全申請的;(三)申請人的起訴或者訴訟請求被生效裁判駁回的;(四)人民法院認為應當解除保全的其他情形。解除以登記方式實施的保全措施的,應當向登記機關發出協助執行通知書”。除民訴法解釋之外,企業破産法第19條和破産法解釋(二)第6條規定了在法院受理破産申請後,法院應當解除對債務人采取的财産保全措施。但在實務中,此處的“受理”并不是法院接受了破産申請的材料,而是指法院作出了受理破産申請的裁定。隻有在進入到破産程式後,法院才能依據企業破産法與破産法司法解釋(二)來解除财産保全措施。
對于預重整程式中的财産保全解除問題,如果現行法律與司法解釋沒有直接規定,我們是否能在現行法律與司法解釋架構下,找到法院解除财産保全的依據?民訴法解釋第166條第1款第1項到第3項無法直接适用在預重整程式中,第1款第4項雖規定了“人民法院認為應當解除保全的其他情形”,但這一條款是否可以直接适用到預重整中?對此,最高人民法院編著的《最高院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了解與适用(上)》列舉了這個兜底條款的适用類型:第一,申請人沒有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起訴或申請仲裁。第二,申請人在訴訟過程中已申請撤訴并經法院裁定準許。第三,對案外人善意取得的與案件有關的财産,一般不得采取保全措施,如采取,應當解除。第四,當事人雙方同意和解的。第五,法院确認被申請人申請複議意見成立,做出裁定,撤銷原保全裁定的。預重整程式中對财産保全的解除,并未包括在最高院列舉的五種情形之中。是以,預重整程式中,法院是否應當解除對債務人(被申請人)的财産保全,在現行法律體系下并沒有明确的依據,雖然民訴法解釋第166條第1款第4項規定了“人民法院認為應當解除保全的其他情形”這一兜底性條款,但這一兜底條款并沒有将預重整的情形涵蓋在内。
在預重整程式中,法院是否應當中止執行重整,現行法律與司法解釋同樣沒有明确規定。民訴法第256條規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中止執行:(一)申請人表示可以延期執行的;(二)案外人對執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異議的;(三)作為一方當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繼承人繼承權利或者承擔義務的;(四)作為一方當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終止,尚未确定權利義務承受人的;(五)人民法院認為應當中止執行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幹問題的規定(試行)》(以下簡稱執行規定)第102條對于“法院認為應當中止的其他情形”這一兜底條款進行了列舉,包括:“(一)人民法院已受理以被執行人為債務人的破産申請的;(二)被執行人确無财産可供執行的;(三)執行的标的物是其他法院或仲裁機構正在審理的案件争議标的物,需要等待該案件審理完畢确定權屬的;(四)一方當事人申請執行仲裁裁決,另一方當事人申請撤銷仲裁裁決的;(五)仲裁裁決的被申請執行人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17條第2款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不予執行請求,并提供适當擔保的。”故而,單從民訴法及其相關司法解釋來看,同樣無法找到預重整程式中中止執行的依據。
綜上所述,最高院系民訴法解釋和執行規定的制定者,其針對民訴法解釋與執行規定的解釋,是準确适用關于中止執行程式的規定和解除财産保全的規定的主要依據。雖然民訴法解釋第166條規定了解除财産保全的兜底條款,民訴法亦在第256條設定了中止執行程式的兜底條款,但最高院并沒有把預重整程式中的适用,納入以上兩則兜底條款的适用射程之内。如果以兜底條款為預重整程式中的财産保全解除和執行程式中止打開通道,恐違背最高院在民訴法解釋和執行規定中設立兜底條款的規範意旨。
類推的前提與适用
相較而言,破産重整程式,企業破産法第19條、民訴法解釋第515條以及執行規定第102條倒是有明确規定,這些規定均要求法院對已進入破産程式的被執行人中止執行。但是,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釋明确地規定了其适用場景僅在破産程式中。不論預重整如何定義,預重整程式隻是作用于破産程式之前的一種特别制度,這也是其被稱作“預”重整的原因。也就是說,預重整程式無法适用破産法第19條的規定,預重整本身不能産生中止執行的效果。如果立法對于預重整程式中的财産保全解除與執行中止沒有規定,法院在個案中是否可以在債務人申請時,通過類推适用破産法第19條,在個案中做出解除财産保全和中止執行的裁定?對此,我們需要從法學方法論的角度,對類推适用的前提進行分析。
類推适用的前提是:法律有“漏洞”。隻有當法律對其規整範圍中的特定案件類型缺乏适當的規則,換言之,在法律對此保持“沉默時”,法律漏洞才存在。如果立法者有意對某些事項不予以規定,即保持“有意義的沉默時”,漏洞便不存在。如果從可能的文義範圍内解釋法律,該法律“違反計劃”地遺漏一個規定,“而從整體上來看,法秩序需要這個規定”,漏洞才得以成立。換言之,在可能的文義範圍内,法律制度有違反計劃的不完整性時,漏洞才存在。所謂的“違反計劃性”,需要從現行有效的法秩序中推導而出,這需要源自對現行法進行的目的性的整體觀察,不能源于對将來法的願望。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法律對于預重整程式中沒有規定财産保全的解除,也沒有規定執行程式的中止,對于是否存在法律漏洞而言,我們應回顧并檢視立法者的規定意向、目标和規範想法。但“立法者”究竟為何人?“立法者的意志”是什麼?是必須要回應的問題。拉倫茨指出:“立法者的意志”即是各部會中負責起草法案之公務員的規範想法,或者是提出法律案或參與法律文字形成之國會議員的想法”。由于我們沒有可供分析的立法理由書,如果希望探究“立法者”如何認定“設立擔保的行為”,本文選取了以下兩本人大法工委研究室部分成員參與編寫的法律釋義作為分析對象。其中,吳高盛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産法〉條文釋義與适用》指出,“破産财産應當面對所有債權人進行配置設定。是以,為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在人民法院受理破産申請後,保全措施應當解除,執行措施應當中止”。另一本釋義為安建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産法釋義》,這本釋義在說明破産程式中解除财産保全的理由時指出:“從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來看,對債務人财産的保全措施,其目的在于保證判決的執行,即為了保證個别清償的實作,這與破産法所要實作的概括式公平清償目的不符。是以,在人民法院受理破産申請後,有關債務人财産的保全措施應當中止。”該釋義在說明中止執行程式的理由時亦指出:“與财産保全措施的目的相一緻,執行程式的目的同樣是為了實作個别清償,與破産法所要實作的概括式公平清償的目的不符。是以,人民法院受理破産申請後,有關債務人财産的執行程式應當中止。”兩本釋義書中,都明确指出,第19條中規定的财産保全解除與執行程式的中止,在于確定破産程式中的概括式公平清償。如果從這個角度推斷立法者的意圖,可認為:針對破産程式做出的财産保全解除與執行程式中止的特别規定,是立法者有意為之,之是以在企業破産法中作出特别規定,就是為了展現出破産程式的概括式公平清償的特征,并将其與非破産程式相差別。故而,立法者對于這一規定的“有意為之”,不能被認作法律漏洞。從另一個角度看,非破産程式中,财産保全不能解除、執行程式無法中止,在現行有效的法秩序中,也沒有所謂的“違反計劃性”。
因為,源自對現行法進行目的性的整體觀察,破産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確定概括性式的集體受償程式。我們将來可能會以立法的方式解決預重整中的财産保全和執行問題,但如果隻是對将來法的願望,在現行法中還沒有依據,就不存在“違法計劃性”。
綜上所述,預重整程式中,沒有解除财産保全和中止執行的規定,并不是法律的漏洞,不能類推适用企業破産法第19條的規定。
從比較法的角度來看,美國的預重整中,系通過當事人協商來限制執行行為的開始與執行,美國破産法僅對預重整進行了原則性、概括性的規定,法院在這一過程中僅僅起到協調、引導而非主導和介入的作用。英國的預重整模式下,雖然法院介入的程度較低,但對于執行中止而言,在原則上仍要求主要債權人的一緻同意。南韓雖然在債務人重整與破産清算相關法律第223條中規定了預重整程式的相關規則,但這些規則主要針對的是在重整案件正式受理前,當事人基于協商而制定的重組方案的制定與提出等問題,并沒有對财産保全和執行程式中止問題進行規定。以及大陸的司法實踐中,由于法律規範的缺失,面對解除财産保全和中止執行的實際需求,部分地方法院在預重整相關的規範、指引中對解除财産保全和中止執行進行了規定,本文選取了10家法院關于預重整的相關規範、指引,其中有部分規範、指引明确規定了預重整程式中的解除财産保全和中止執行制度,另有部分規範、指引并未明确規定。有些法院的規定較為“剛性”,明确規定了法院應當解除保全或中止執行程式;有些法院的規定較為“柔性”,并沒有規定法院應當除保全或中止執行程式,賦予了當事人談判的空間,具體如下表所示:
表1
上表中列舉的法院規範、指引或規範的模式并不統一。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都明确規定了在預重整程式中,執行程式應當中止,可謂“剛性”規定的代表。
另一類型的規定與“剛性”規定相比,更強調通過商榷的方式,促進執行部門推動中止執行或者暫緩執行,這與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及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做法有所差異,四川天府新區人民法院的預重整案件審理指引,便是這種具有“彈性”規定的代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和北海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規定中,對于财産保全和執行程式,隻是規定了管理人“應當”向法院申請或通知中止或解除,并沒有規定法院是否“應當”中止和解除。是以,以上三家法院的規定,實質上仍歸為柔性類型。
韓長印教授指出,法院如把中止執行的效果提前到預重整程式中,會出現如下弊端:第一,司法公權力的過度幹預,造成“談判”雙方自然難謂平等,自主協商難以存在,且交易成本會随之增加。第二,可能會成為債務人逃債的工具。如在預重整程式中承認中止執行的效力,相當于變相延長了中止執行的期間。王欣新教授認為,預重整作為當事人之間進行的庭外重組,不具有中止對債務人财産的執行、解除其财産保全措施、停止計算債權利息、中止訴訟等隻有在破産程式啟動後才可能具有的法律效力,但債權人等自行協商同意接受相關限制的除外。
值得注意的是,立法法第8條之規定,訴訟和仲裁制度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來制定,故而,在法律沒有對預重整程式中的财産保全解除和執行程式中止予以規定之前,如直接把以上規範、指引當作“法律”來适用,可能會出現違反立法法的問題。如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在表1中列舉的規範、指引中,以當事人協商與合意為基礎,通過“柔性”的方式解除财産保全和中止執行程式,更為可取。
因為,基于商榷或協商來完成的财産保全解除和執行程式中止,在現行法律體系可以找到合法的依據,也能避免規範、指引制定違反立法法的風險。韓長印教授提出,可通過預重整參與人在自主協商的基礎上達成“訴權契約”,為法院中止執行和解除财産保全提供合法的依據。“訴權契約”的理論,在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的體系下,可以找到法律依據。例如:民訴法解釋第166條中有一處解除财産保全的兜底規定,即:“人民法院認為應當解除保全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編著的《最高院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了解與适用(上)》專門解釋了兜底條款的适用情形,其中包括:“當事人雙方同意和解的。”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溫州吉爾達鞋業有限公司預重整案中就是采用了執行和解來解決中止執行的問題。如果當事人雙方達成和解,那麼解除财産保全就可以依據民訴法解釋第166條來進行,法院在作出裁定時便有法可依。同理,通過商榷和協商的方式,也可以促成當事人之間達成執行和解,依據民訴法第230條關于執行和解的規定與第256條關于執行中止的規定,同樣可以達到中止執行的效果,而且這種方式也依然在現行法律的體系和架構内。
綜上所述,如法院協助當事人達成訴訟中的和解或執行和解,再以此為基礎來解決财産保全解除和執行中止問題,把“規範、指引”真正地當成“指引”而不是法律來用,可以確定在沒有法律依據時,規範、指引的内容不會越過立法法第8條劃定的界限。
首先,在民訴法、企業破産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條文中,沒有在預重整程式中解除财産保全和中止執行程式的直接依據。其次,從法學方法論的角度來看,亦無法類推适用破産法第19條關于解除财産保全和中止執行的規定。再次,從立法法的角度來看,如果在規範、指引中直接規定法院應當解除保全和中止執行,可能會違背立法法第8條之規定。
本文建議,在法律沒有明确規定的前提下,規範、指引不宜突破立法法,直接規定法院應當裁定解除财産保全和中止執行程式。在面對預重整程式中的财産保全和執行的需求時,建議法院采用柔性的模式,賦予當事人和解和談判的空間。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法院的協調能力以及府院關聯的效果,以市場化的預重整制度為路徑,将和解或執行和解作為财産保全解除和執行中止的合法依據。對于已在規範、指引中明确規定應當解除保全和中止執行的法院,在适用這一剛性規範、指引前,建議采用和解和執行和解先行的模式,把“規範、指引”真正地當成“指引”而不是法律規範來适用,既能確定法院做出的裁定具有紮實的法律依據,亦能確定規範、指引的内容不會越過立法法第8條劃定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