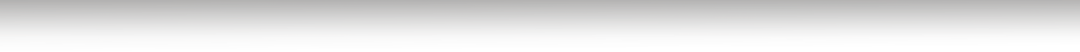
第32章 問罪
梁雙樹兩口和王大奎都沒追上梁香梅。
梁香梅一眨眼就沒了影兒。
梁香梅跑到哪兒去了呢?
梁香梅哪兒都沒去,她轉過巷道,跑到跟她相好的瑞子家,梳了頭,洗了臉,騎上瑞子家的自行車,向王家窯去了。她要當面向王全天問清楚,為啥要寫紙條?王全天到底是咋想的?
就在梁香梅騎着自行車往王全天家趕的時候,田彩雲正在王全天家裡忙碌着。從王全天被打之後,田彩雲除過忙自家地裡的活外,還要忙王全天家地裡的活,還要照料王全天的日常起居,人家娃是為了她的家事挨了打,自己豈能看着不管?
在田彩雲精心照料下,王全天身上的瘀傷平複了,腳腕上的紅腫消了,也能下炕了,簡單的活兒也能幹了,可就是不能用力,稍不注意,裆裡的那件物就怪不拉叽的抽着疼,特别是尿尿的時候,疼得王全天兩手捂着裆裡,額頭上就冒汗。
開始的時候,王全天盡量隐忍着,不想讓田彩雲知道。他想,一個男子漢,讓田彩雲知道自己的“難言之隐”,實在是丢人害臊得很。可是後來,還是被田彩雲發現了。
田彩雲悄聲問:“咋回事?看你難受得很?”
王全天有些害羞,含含糊糊地說:“老不舒服,尿時疼!”
田彩雲有點怕了,悄悄找了娘家當過赤腳醫生的劉拐子,把王全天裆裡疼的症狀詳說了一遍,劉拐子聽說是讓人拿腳踢的疼,也不敢大意,然後跟田彩雲到王全天家仔細看了王全天的傷,當着王全天的面,說是不要緊,吃些止疼片就好了,可是背過王全天,卻對田彩雲說,這病很麻煩,傷了根部的神經,恐怕要影響到性功能了。田彩雲急了,問劉拐子有啥辦法,劉拐子說,也沒啥好辦法,隻能先開些中藥調理着,養着,看情況再說。
其實,劉拐子不說,王全天也能感覺到自己裆裡的疼,有些古怪,最明顯的就是那物件,不論怎麼逗弄,都像死老鼠一樣,沒一點感覺。王全天很憋氣也很恐慌,這些天來,越來越覺得自己已經廢了,是以,在痛恨黃料科的同時,也對梁香梅有了看法,明明跟自己談戀愛,卻又跟黃料科攪在一起,弄得自己跟八竿子打不着的黃料科成了怨家對頭,這麼些天了,連個影子也不見!王全天憑空猜疑梁香梅是腳踏兩隻船,是以,當王大奎讓他寫不再糾纏梁香梅的保證書時,他也帶有跟梁香梅賭氣的意思,三兩下就寫了。寫罷,也覺得不妥,可是也沒再深思,因為隻要裆裡一疼,王全天覺得世間啥事都不重要了,随她去罷,愛弄成啥是啥!
可是田彩雲覺得這事麻達了!田彩雲是過來人,知道男人裆裡的物件對一個男人的重要性,王全天“小弟弟”萬一治不好,成了廢人,他還娶不娶媳婦?他将過怎樣的生活?自己如何面對?田彩雲開始後悔讓王全天去缑家灣給豬配豬娃去了,自己真是,唉,弄得啥事麼!上次王尚世回來,得知王全天被黃料科打了的事,當面沒說啥,可從看他的那神情裡,分明能看到一絲不滿。她不怪老漢,誰家娃為别人家的事讓人打了,當家長的都會不滿的。田彩雲在愧疚之餘,暗暗打定主意,無論花多少錢,用啥辦法,都要把王全天的病看好,隻有這樣,她才能心安。是以,天天起來,她的第一件事就是給王全天做飯,洗衣服,熬中藥,然後才是忙自己家裡的事,晚上,也是看着王全天吃了飯,喝了中藥,這才回到自己家裡去。
這期間,沒下巴房甯娃也擰來擰去,跟在她尻子後頭,攆到王全天家裡谝閑話,她知道,房甯娃肯定是對她和王全天的關系起疑了,可是,她有什麼辦法能撇清呢!田彩雲的确為此苦惱過幾天,後來,她想通了,人的嘴是圓的,舌頭是扁的,誰愛咋說咋說去,她不能丢下王全天不管,如果那樣做了,還能是人嗎!
和田彩雲一樣,王全天心裡也重得跟壓了一塊子石頭一樣。他本來想把黃料科打他的真實原因說給田彩雲,又怕田彩雲輕看了他,或者認為他是為了減輕她的思想負擔才這樣說,是以就一直憋着。後來,他想把王大奎遊說放棄和梁香梅談戀愛的事告訴田彩雲,讓田彩雲知道王大奎回來又不見她後,不知道又要惹出什麼事來,是以就來了個悶不做聲。可又擔心萬一田彩雲知道王大奎回來過,問為啥不告訴她,怎麼辦呢?一時又想不出自圓其說的辦法。想來想去,隻好把這些麻纏事憋在了肚子裡。
肚子裡是擱飯馍的地方,擱了事就飯吃不進去了。田彩雲把做的飯端到炕邊,王全天沒有食欲,沒動筷子就端回去了。田彩雲的肚子裡也愁成了一疙瘩,同樣沒有擱飯馍的地方。做好的飯菜擱涼了,第二頓又不想熱着吃,給兩頭母豬弄了個好事。
這天,田彩雲剛剛給豬喂了食,騰出手來在院子給王全天洗衣服,梁香梅推着自行車進門了。
梁香梅剛進門,看見田彩雲,不好意思地說:“走錯門了。”調轉自行車頭往外走。
“你尋誰?”田彩雲問。
“我找王全天。”走到門道的梁香梅說。
“沒走錯門。這就是王全天的家。”田彩雲說。
梁香梅心裡納悶:王全天說,家裡隻有父子兩個人,啥時多了一個女人?又扭過自行車頭,問:“你是王全天他啥?”
田彩雲甩甩手裡擰幹的内褲,搭在鐵絲繩上,不自然地說:“我……我不是他啥,你進來,王全天在房子裡。”
梁香梅把自行車靠在院子的樹上,走了進去。
一進腰門,梁香梅用眼睛打量了一下,是兩對沿的四間低矮的廈子房,一邊是兩個房子,房子的門窗漆皮斑駁,露出淺灰色木質顔色,門扇有些翹了。糊着窗的報紙發黃,有幾個窟窿。一邊空着的廈房下,堆放着幾件農用家具。天庭沿上壓着幾個青石條,椽碼眼處有兩個幹馬蜂窩。這一切,都銘刻着艱辛歲月的痕迹,窮的程度和王全天說的對上号了,可哪裡來的這個當王全天後媽年齡偏小,當王全天媳婦年齡偏大的女人?梁香梅滿心疑惑走進了房子。
躺着的王全天聽見說話聲,坐了起來,還沒來得及把自己這一向的疲倦、邋遢、狼狽相整理好,梁香梅進房子了。
王全天掙紮着坐起,有點吃驚地說:“是你?”
一股中藥味撲鼻而來,梁香梅扇扇鼻子,幾乎驚訝地叫出了聲:我的媽呀,這不是我見過的王全天,這分明是從監獄裡跑出來的犯人,頭發蓬亂,衣領敞開,萎靡不振,炕上的被子窩成一疙瘩。
梁香梅驚疑不安地問:“你這是咋咧些?咋成這樣子啦?”說着,在炕牆邊的凳子上坐下來。
田彩雲笑着端進來兩杯水,擱在桌子上,說:“你兩個坐,我出去一下。”
田彩雲出了房子門,王全天和梁香梅大眼對小眼,悶坐了好一會,王全天才望了一眼冒着熱氣的杯子,說:“你喝水。”
梁香梅沒有去端杯子,問:“剛才那個女人是誰?”
王全天知道梁香梅誤會了,連忙說:“我嫂子。”
“你嫂子?”梁香梅奇怪地問:“你咋沒說過,哪來的嫂子?”
王全天埋在心裡的對梁香梅的不滿忽而冒了出來,不耐煩地回了一句:“我堂嫂。你沒見過。”
梁香梅有些敏感,語氣怪怪地,看着王全天說:“堂嫂?對你挺親的嘛,連給你把内褲都洗了。”
王全天回避着梁香梅的目光,不吭聲。
梁香梅頓了頓,把茶水杯子端給王全天,軟聲問:“你咋成這樣了?發生啥事了?”
王全天不接話,視若無睹,抿着嘴,想了想,恨恨地說:“還不是着了你的禍!”
梁香梅奇怪了,放下茶杯,秀眉緊蹙:“着了我的禍?”
王全天從梁香梅的表情中看出,梁香梅至今還蒙在鼓裡,就忍不住把在種豬場裡發生的事原原本本的給梁香梅叙說了一遍。梁香梅就像聽驚悚故事一樣,聽得心驚肉跳,目瞪口呆。自己這一段忙養豬場的事,再加上金杏的事,身忙心累,正準備這一段忙過了,好好和王全天商量一下,盡快按鄉俗把婚事定下來。沒想到這期間竟然發生了這麼多事,而且件件與自己有關!梁香梅被黃料科的兇殘手段吓住了,原以為黃料科是個不識進退的憨貨,黃料科的父親黃西亮做事有些霸道,萬萬沒想到這父子倆竟然軟硬兼施,就像死蛇一樣,硬要纏到自己這棵樹上來。是以,聽了王全天的叙說,半天說不出話來。
王全天見梁香梅不說話,以為梁香梅腳踩兩條船,現在兩條船硬碰硬,一條船把另一條船碰爛了,沒法收場了。是以,又惱洶洶地質問梁香梅說:“原先我問你,你追過别人沒有,你說沒有。我還問你,别人追過你沒有?你一口咬定說沒有。可是你看,黃料科說你大媽接了他家的四樣禮,說我成了攪事的……”
梁香梅急忙辯解,說:“黃料科是個癞皮狗,是他死皮賴臉地糾纏我,我從來沒應過他一句話!”
王全天不認同,說:“你沒答應,你大媽收了四樣禮,就等于你預設了!”
王全天說的是實情,按鄉俗女方接了男方的禮,就是認了親事。梁香梅泛不上話,心裡發虛泛潮,她努力鎮靜自己的情緒,說:“我大媽是我大媽,我是我,我從來沒答應,永遠也不會答應!”
王全天眼盯着頂棚,不吭聲。
梁香梅不甘心地說:“你也應該先問問我呀!連我面都沒見,就……”
王全天猛地情緒激動起來:“又是捶頭又是拍腳,不寫,連命都保不住!我在哪兒去見你?就這,還把我打得連尿尿都疼得不行!”
梁香梅看到,都是因為自己,把王全天弄成現在這樣子。她覺得王全天真冤枉,黃料科真可惡,一口惡氣堵在喉嚨咽不下去,憋得心怒神慌,說:“是我對不起你,把事沒處理好。你放心,我一定還你個公道!我就不信了,他黃料科還敢把我搶到他屋裡去!”
王全天聽梁香梅如是說,知道梁香梅心沒變,心裡稍微平順些,但又想到梁雙樹兩口的态度,還有黃料科的不擇手段,心裡忐忑不安,半天,才說:“咱兩個的事,我不為難你了,算了吧!”
梁香梅沒有意識到到事情這麼複雜,黃料科這麼下作,覺得自己成了惡狗嘴裡的一塊肉,越想越憤怒,顧不得禮貌和形象,跟王全天說了句“你甭管!好好養你的傷!有我哩!”就紅着眼,旋風般跑出房子,推上自行車朝外走,和進前門的田彩雲碰了個滿懷,兩人都幾乎摔倒。田彩雲在攔與不攔的猶豫間,梁香梅出了門,跨上了自行車。
眼看着梁香梅騎上車子走遠了,田彩雲這才跑進房子,看見氣得嗷嗷的王全天,滿懷心思地說:“剛才那女娃,是不是你對象?”
王全天沮喪地說:“是的。”
田彩雲有點擔心地猜測着說:“你對象哭着走了,你倆吵嘴了,是不是因為她看見我給你洗衣服?”
王全天硬氣地說:“嫂子,這不關你的事。”
田彩雲搖搖頭,說:“這梁香梅我聽人說過,性子烈得很,敢當女骟匠,是個厲害下家。”
王全天扭着脖子,不說話。
第33章 退禮
梁香梅從王全天家門出來,偏腿跷上自行車,穆桂英踏營一般,沖出巷道,向缑家灣飛去。耳邊風聲呼呼,腦子裡就像有千軍萬馬在馳騁,各種聲音,各種念頭交疊起伏,一時間隻覺得頭要爆炸似的。
梁香梅一進家門,把自行車一扔,跑進房子,爬在炕上嗚嗚地哭。梁雙樹兩口聞聲跑進房子,沒有問為啥哭,隻是站在一邊唉聲歎氣。
就在梁香梅走後不久,鄰家張蘭就進了門,張蘭說:“黃西亮說,天下無媒不成婚,叫我給兩個娃娃跑個腿。他叔,他嬸,娃小不懂啥胡說,大人可别胡說,你老兩口把黃料科家的彩禮接了那麼長時間,突然說不願意就不願意了?你老兩口說是娃不願意,拿不住娃的事就不接彩禮麼!人前一句話,屙出來還能煨進去?你家連個豬圈都沒紮,憑啥領養豬補貼?你不願意把女許給人家,憑啥吸人家的煙,喝人家的酒?就這還沒結婚,結了婚,兩家變成一家,你家再不會過窮抽筋的日子……”
張蘭把梁雙樹兩口連諷刺帶挖苦地訴說了一頓,梁雙樹兩口臉燒的像是沾了屎的鞋底打了。心裡想着,女兒回來後,一定要商量個了結的辦法。梁香梅回來了,隻是個哭着,哭得梁雙樹兩口心裡發毛,啥話都沒法出口。前面給金杏招女婿,招出一大攤子事,剛剛了結,過了沒幾天安生日子,梁香梅這兒又亂鼓咚咚,唉,這家裡成了亂事堂了!
梁香梅哭夠了,哭累了,也哭出辦法來了。梁香梅起來,擦把臉,喝口水,簡潔扼要地給父母把黃料科的所作所為,還有王全天的現狀,還有自己的主意說了一遍。父母終于明白,這個黃料科是個不能招惹的主兒,把女兒嫁給她,不是給打死,就是被怕死!于是,一家人重新算計,如何湊錢,如何退禮,如何應對黃料科和黃西亮,一直弄到半夜,才把一切想清楚,弄妥當了。
過了幾天,把錢湊夠了,梁雙樹有意識在黃西亮家門前轉悠了幾回,看黃西亮回來了沒有,回來了就把錢退給他。黃西亮沒有回來。在轉悠的時候,被剛從黃西亮家出來的張蘭看見了,張蘭把梁雙樹拉到一邊,滿臉堆笑說:“胡轉悠啥哩?直接進去說就對了,黃西亮不在谷雨在,正等你的話哩,順手把你女兒的生辰八字給了,讓你未來的親家把兩個娃辦喜事的日子一定,我這媒人的臉上多風光的。”
梁雙樹冷着臉,快步走了。張蘭臉上的笑容凝固了。
梁雙樹擔心把事再擱出事,第二天一大早,就搭公共汽車,上縣去找黃西亮退彩禮了。
車的最後排隻有一個空座位,梁雙樹仄楞着身子,兩手捂着挎在胸前的布袋,走了過去。剛坐下,把布袋擱在大腿上,掏錢準備買票,摸遍了身上的幾個衣兜,沒有找到零錢。梁雙樹估摸老婆可能把零錢和彩禮錢都裝進布袋裡了。他解開布袋口取錢,拿出一個手帕裹着的小包,裡面是彩禮錢,一塌子零錢用繩子和小包纏在一起。坐在前排的一個留着小胡子的小夥,裝作無意的樣子注視着梁雙樹的舉動,給梁雙樹右邊的一個中年婦女說:“阿姨,咱兩個換個座位,我跟這位大叔谝一谝。”說着順手要過梁雙樹手裡的錢,朝前面喊:“給這位大叔買票。”
梁雙樹接過車票和找的零錢,給小胡子笑。
小胡子貼緊梁雙樹坐下。梁雙樹覺得有些擠,挪了挪身子。小胡子掏出兩根煙,一根給梁雙樹,一根自己拿着。掏出打火機要給梁雙樹點煙,梁雙樹說:“車上吸煙沒地方彈煙灰,不吸。”要把接到手裡的煙還給小胡子。小胡子說:“你拿着,過會下了車吸,是好煙,硬中華。”梁雙樹把煙夾在了耳朵上。
小胡子問:“大叔,你上縣辦事還是……?”
梁雙樹看了一眼車窗外移動的田野,說:“到縣上找個人。”
一路上,梁雙樹的心思全在退彩禮上,尋思黃西亮如果答應了結這事,好說,不答應了結呢?對小胡子的問話接一下不接一下,小胡子一看老漢不搭話,也就再不吭聲了。
車經過畜牧局門口,梁雙樹下車,小胡子也跟着下車,一下車,拿出打火機要給梁雙樹點煙,梁雙樹連忙推擋,說:“不吸不吸,你忙你的,我還急着尋人哩。”
梁雙樹來到畜牧局門口,探頭探腦往進走,沒想剛踏進門,就被門衛擋住了:“哎哎,老漢!你找誰?”
“我找黃西亮。”梁雙樹不解地說,“你擋我做啥?”
門衛闆着臉問:“你是黃局長的啥人?”
梁雙樹瞪着眼,說:“一個村裡的,他把我叫哥哩。咋咧?”
門衛笑着說:“不咋不咋,黃局長下鄉去了,事緊不緊?事緊了,我給你打電話聯系。事不緊了,你明天來,他肯定在。”
“事緊。”梁雙樹說。
門衛去辦公室打電話聯系去了。
梁雙樹在畜牧局的院子轉悠,等黃西亮回來。
院子本來不大,辦公大樓正在施工,整個院子變成了一個建築工地。水泥攪拌機轟隆隆,震得人耳朵很不舒服,勞工們戴着着安全帽在忙碌着。梁雙樹看見一個開升降機的勞工在吸煙,想起了自己耳朵上還夾着一根好煙,取下來在鼻子底下聞了聞,走到吸煙的勞工跟前,笑着說:“借個火。”吸煙地勞工把煙遞了,梁雙樹點了煙,把煙還了,深深的吸了一口,吐出煙圈,再深深吸了一口,吸第三口的時候,突然失去知覺,昏倒在了地上。
開升降機的勞工吓了一跳,大聲喊:“快來人,人昏倒了。”周圍正在幹活的勞工聽到喊聲,以為出事故了,撂下手中的工具,跑了過來,一看,不是工隊上的勞工,就問開升降機的勞工咋回事。開升降機的勞工把過程一說,大家一邊把梁雙樹扶起坐在地上,一邊議論這人是不是突發心髒病或腦溢血病,有人急不擇言,喊:“叫獸醫!叫獸醫!”
城關獸醫站和縣畜牧局在一個院子辦公,對面房子的獸醫聽到喊聲來了,問明情況,摸摸脈搏,翻翻眼皮,看看舌苔,說:“不像是得病的樣子。”獸醫過去是人醫改學獸醫的,聞見鼻孔裡的出氣有一種自己曾經做手術用過的麻醉藥味,看見地上還冒着煙的半截香煙,撿起,搭在鼻子上聞了聞,說:“這根煙恐怕有問題。”
獸醫讓勞工們把梁雙樹擡到樹底下,弄了個濕水毛巾給梁雙樹擦額顱,一會會功夫,梁雙樹清醒過來,問這麼多人圍着自己弄啥。獸醫拿着半截煙說:“你剛才突然昏倒在地上了,你吸的這根煙是哪兒來的?”
梁雙樹把煙的來曆說了。
獸醫說:“怪不得哩,這煙絲是用麻醉藥水處理過的,是小偷偷人時用的。”
梁雙樹如夢初醒,找來自己的布袋,布袋底下被割了好幾個口子,好在口子不大,錢包沒有漏出來。梁雙樹出了一身冷汗,如果真的讓小偷得手了,空手見黃西亮,不把人丢大了!
畜牧局院子的一切恢複正常。
黃西亮下鄉回來進局裡大門的時候,當着滿院子的人,拉住梁雙樹的手,笑着說:“是你?走,到我的辦公室。”
黃西亮見了梁雙樹的熱情程度,大大出乎梁雙樹的預料。梁雙樹懸在半空的心落了地。
黃西亮胳膊窩夾着黑色皮夾,領着梁雙樹邊往裡面的三間平房走去,一進辦公室,黃西亮把皮夾往桌子上一扔,把外套脫了,搭在旁邊的衣架上,撣撣褲子上粘的塵土和草葉,在臉盆裡洗了個手,倒茶遞煙。黃西亮指指面前的木凳子,讓梁雙樹坐了,自己坐在了凳子對面辦公桌的沙發上。
辦公桌是寬大氣派的老闆桌,棕紅色桌面,油光發亮。桌面擺放了一沓檔案材料,一部電話,一個進階玻璃茶杯,茶杯裡的茶葉像松針一樣在淡綠色的茶水中漂浮。沙發是棕紅色皮質沙發,黃西亮一坐下,整個身子陷進沙發裡,兩手搭在扶手上,靠背高出人一頭。梁雙樹覺得自己比黃西亮矮了一截,怪不得人都把頭削尖當上司哩,人往這地方一坐,勢多大的,笨狗也變成狼狗了!
黃西亮沒有寒酸一句,單刀直入地問:“咱兩個住在一個村子,隔三見五就能碰上一面,啥事把你急得跑到縣上來找我?”
梁雙樹的手不自覺地在捏弄着布袋,說:“還不是兩個娃的婚事。”
黃西亮說:“兩個娃的婚事好着哩麼,隻等結婚了,還有啥說的?”
黃西亮的口氣,讓梁雙樹突然感覺黃西亮的态度,和剛才在院子見了自己的熱情态度不一樣了,内心一陣恐慌,心裡有點亂了,話說的有些不渾全了:“你的家好……好家,料科也……好娃,如果咱兩家當親,我家肯定不會……不會吃大虧。”一急把“不會吃虧”說成“不會吃大虧”。
黃西亮飄出來一句:“小虧也不會吃。”
“對,沒有吃的虧,隻有沾的光。”
黃西亮話頭一轉,說:“照你這麼說:你是跟我商量兩個娃結婚的事來了?”
梁雙樹滿臉漲紅,說:“我給你回話來了,退彩禮來了。”說着從包裡掏出手帕包裹的錢,擱在桌子上,接着說:“這總共是三千二百元,兩千元的彩禮、煙酒折算的錢,領的養豬補貼,全都算在裡頭了,如果不夠,我再想辦法。”
黃西亮的眼睛盯着梁雙樹的眼睛,一句話也不說。
梁雙樹說:“為這事的,女兒哭鬧,老婆憋氣,我左右為難,家都不像家的樣子了。你就看在咱兩個從小穿開裆褲一起長大的份上,饒了我吧,接了我退的彩禮,權當沒有這回事。”
黃西亮半天沒說話,眼珠子盯着梁雙樹亂轉。過了半支煙功夫,才哼哼着,沉聲說道:“強扭的瓜不甜,實在不行就算了。我倒無所謂,就怕我兒子狗東西不聽我的。”
梁雙樹聽了,急切地說:“那咋辦?”
黃西亮陰陰地一笑,說:“還能咋辦?我給他做工作麼。”說着走到辦公室門口,探身門外,兩邊望了望,把門關了,示意梁雙樹過來。
梁雙樹走到黃西亮跟前。
黃西亮說:“有人舉報我給你家發養豬補貼的事,縣紀檢委要派人調查,你幫我個忙。”
梁雙樹不解地問:“我把領的養豬補貼退給你,你退回去,不就完了?我能幫你啥忙?”
黃西亮說:“事情沒有你想得那麼簡單。”黃西亮打着手勢,嘴搭在梁雙樹的耳朵上,嘀嘀咕咕了一陣。
梁雙樹聽了難為情地說:“這能把人哄過去?”
“這你就不用管了,你按我說的來就行。我給你說的這事,你不能給任何人說,包括你老婆和你女兒,說了傳出去,我落個對抗組織調查名,丢了烏紗帽,你也說不過去。”
梁雙樹眼瞪大了,還想争辯。
黃西亮說:“這事又不花你一分錢,下個苦的事,有啥難為情的?”
梁雙樹擦擦額頭上的虛汗,說:“不難為情,不難為情。”
第34章 偷豬糞
梁雙樹在縣城連一口飯也沒吃,就去汽車站搭車。
走到汽車站門口,看見一攤人圍着看熱鬧,走過去一看,是那個給他煙的小胡子和另個一個小黃毛,在打一個老漢,一邊打還一邊罵:“誰偷你錢來?老狗日的胡說啥哩!”那個老漢和梁雙樹年齡差不多,被打得在地上翻滾,可是拉住小胡子的衣服襟不丢手,一個勁地喊:“那是我給娃看病的錢,你把錢還給我!”
梁雙樹一看是小胡子,心裡陡然升起一股怒氣,這狗日的,差點把我的錢偷了去,現在又偷了人家給娃看病的錢!腦子一熱,沖上前去,一拳照着小胡子的臉面打上去,小胡子猛不防被打得身子一踉,鼻血流了下來。梁雙樹一把抓住小胡子的手,說:“把錢給老漢,要不打死你!”那個小黃毛一看梁雙樹打了小胡子,朝着梁雙樹屁股就是一腳,梁雙樹差點跌倒,但手卻不松,反手狠勁一擰,把小胡子擰的疼得大叫,旁邊看熱鬧的人也大喊助威:“把錢給老漢,啥錢都偷!往死裡打!”小胡子和那個小黃毛一看起了衆怒,隻好把錢包丢給那個老漢,梁雙樹手一松,小胡子和小黃毛小夥一溜煙跑了。
那個丢錢的老漢拿着失而複得的錢包,感激地要對梁雙樹磕頭作揖,梁雙樹趕忙扶起,說:“這狗日的早上給我迷魂煙,差點把我的錢偷了!”周圍人說:“老漢快走,小心小偷叫人來報複!”梁雙樹忍着屁股上的疼痛,趕緊上了車,坐在靠窗的座位上。
車駛出了縣城。梁雙樹心裡輕松了,一者終于把禮退了,二者車已經離開縣城,小偷把人叫來也沒用了。心一輕松,這才四下裡亂看,看見車上的人都看他的手,低頭一看,手裡還攥着那個被小偷割破的爛布袋。原來裝錢的布袋幾個口子連在一塊兒了,小口子變成大口子了,用不成了,梁雙樹想了想,一把把爛布袋扔出了窗外,也省得老婆子見了問,問了罵。
梁雙樹一進門,老婆何秀珍和女兒梁香梅圍上來。見梁雙樹手裡空着,沒把裝錢的布袋拿回來,估摸事情有眉目。
梁香梅沒有問,去倒水了。
“黃西亮把彩禮接了?”何秀珍問。
梁雙樹“嗯”了一聲。
何秀珍揪着圍裙的手松開了。
梁香梅把水杯往父親手裡塞,父親沒接,說:“先做飯,一天沒吃,心裡寡得不想喝水。”
何秀珍責怪說:“你是石頭人,吃個飯影響啥事了。愛吃羊肉泡,幾年了再沒吃過,到縣裡了,也不吃。”
梁雙樹沒有接何秀珍的話。
過了會兒,梁香梅端來了兩個馍和一碗稀飯,炒的雞蛋、青辣子。
梁雙樹吃飯的時候,眼睛時不時往後院裡瞅。
何秀珍往梁雙樹瞅的地方看了一下,牆角擱了一堆爛磚頭,說:“你吃飯哩,一個勁地看爛磚頭,吃爛磚頭呀?”
梁雙樹胡亂地刨了兩口飯,手在嘴上一抹,走進了後院,把磚頭踢了幾腳,說:“把鐵鍁給我拿來。”
何秀珍問:“你要鐵鍁弄啥?”
梁雙樹說:“你拿進來我給你說。”
何秀珍拿鐵鍁往後院走。
梁雙樹接過鐵鍁在牆角鏟了起來,說:“紮豬圈。”
何秀珍疑疑惑惑,問:“咱又不養豬,你紮豬圈圈你呀?”
梁雙樹說:“你不說話,我不會把你當啞巴,不該問的甭問。”
何秀珍大聲說:“香梅,你大一回縣上的中魔了,不養豬紮豬圈哩。”
梁香梅走到父親跟前,說:“大,你……”
梁雙樹不容梁香梅開口:“想幫忙了,給我提水端磚和泥,不想幫忙了,離遠些。閑話少問。”
何秀珍給女兒說:“香梅,走,你跟媽到房子去,别理老神經。”
母女倆走出了後院。
梁雙樹一個人,又是提水和泥,又是砌磚,哼呲哼呲紮開了豬圈。
母女倆好氣又好笑。
梁香梅見幫不上忙,車子一騎,到養豬場去了。
梁雙樹從後半天一直幹到天黑,像模像樣的豬圈紮成了,拍拍身上的土,拉着架子車,架子車上搭了前後擋闆,拿着鍁出了門,好大工夫沒有回來。何秀珍正疑惑,梁雙樹拉着滿滿一架子車豬糞回來了。何秀珍捂着鼻子把架子車轅往後一扭,罵:“人家把豬糞往出拉,你把豬糞往進拉,你成豬腦子了?”
梁雙樹不吭聲,把何秀珍推開,把豬糞拉了進到了後院,“咵”地把架子車轅一丢,說:“你沒說錯,我不是豬腦子,能把豬糞拉回來?”
正說着,張蘭進來,高喉嚨大嗓子喊:“哎,梁雙樹,得是你剛在村外的糞堆上拉了一架子車豬糞?”
梁雙樹翻了一眼張蘭:“是你家的?”
“不是我家的,我問你是閑得嘴癢了?黃西亮真是的,讓你沒養豬領養豬補貼,把你聞豬糞味耽擱了,偷開豬糞了。”
梁雙樹聽了“偷”字,覺得人格受了侮辱,說:“我剛裝豬糞的時候,碰見你男人邱來了,他沒吭聲,說明他同意,你還上門罵罵咧咧。”
“我男人是泥捏的泥性人,人把他媽背去他都不管,早都不理家裡的事了,他有啥權随便把豬糞給你?”
梁雙樹心裡清楚,張蘭的氣沒在一架子車豬糞上,而在瞎了的黃料科和梁香梅的婚事上。她是借機出氣。梁雙樹還招無術,心裡憋屈。他走到後院,拿起鍁,把倒在豬圈裡的豬糞狠狠地拍打,豬糞四處飛濺。
何秀珍上前攔擋,抓住鍁把,說:“你這是弄啥麼?”
張蘭說:“羞先人麼弄啥哩!自己沒本事,拿豬糞出氣,怪豬糞的屁事!”
梁雙樹蹲在地上,兩手抱頭,把頭埋得很低。
何秀珍歪還沒發完,說:“你濺了一身的豬屎,今晚就睡在豬圈裡,不要進房子。”
晚上,何秀珍梁香梅都睡了一覺了,梁雙樹還蹲在那兒。
梁金杏去後院上廁所,沒上成,打了個轉,出來了。
何秀珍披着衣服,跑進後院,說:“金杏要上廁所了,你還跟死豬一樣蹲在那兒,把娃憋死呀?”
梁雙樹這才要起來。由于蹲的時間長了,猛地往起一站,頭昏目眩,摔倒在了地上。何秀珍和梁香梅跟梁金杏聽見人倒地的聲音,跑出來扶他。梁雙樹已經爬起來坐在了地上,執拗地不讓母女仨搭手。
月亮昏暈,星光稀疏,村莊在熟睡中,唯獨梁雙樹家的後院裡,一個人坐在地上,何秀珍和梁香梅、梁金杏站在旁邊。一家人個個的心裡都苦苦的,疼疼的,像被蟲子咬了。
偷豬糞引來風波,惹得老婆何秀珍甚至懷疑梁雙樹去縣上找黃西亮退彩禮,和黃西亮說的不好,有氣憋在肚子裡,該不會是腦子受了刺激,神經耍麻達了?
天還沒亮,何秀珍就悄悄摸黑穿衣服,驚動了身旁熟睡的梁香梅。
梁香梅問:“媽,你起來這早幹啥麼?”
何秀珍嘴貼在梁香梅的耳朵上,說:“鄰村有個醫生,看神經病看得好得很,我叫給你大看一下。”
梁香梅轉了個身,揉揉惺忪的眼睛,說:“你見風就是雨,沒事尋事。”梁香梅不願意讓母親去找醫生。
何秀珍邊扣衣扣邊說:“家裡有個神經病,日子就沒法過。你沒看東頭虎子的大有精神病,把鍋端的擱在巷道中間,給鍋裡尿尿,說搭醋哩……”
梁香梅說:“你再不要說了,要去你去。”
何秀珍叫了梁金杏作伴,母女倆可憐兮兮地披着晨曦,踏着晨露,吹着晨風,找治神經病的醫生去了。
日上三竿,何秀珍和梁金杏叫看神經病的醫生還沒有回來,一輛小車停在梁雙樹家門口。
車上下來三個人,走進了梁雙樹的家門。
“你……你是弄啥的?”正在掃地的梁香梅問。
“這是梁雙樹的家嗎?”領頭的人開了腔。
梁香梅說:“是的。”梁香梅向裡屋喊:“大,有人找你。”
這時,何秀珍和梁金杏,還有那個叫來看精神病的醫生到了門口,看見門前停了一個小車,何秀珍不知道出啥事了。醫生說:“你都要把病人送到大醫院去呀,還叫我弄啥?”何秀珍一把拉住醫生,說:“不是,不是。叫我看,一大早,哪兒來的小車。”兩人都疑疑惑惑沒理站在腰門口說話的幾個人,向門裡走去。
梁雙樹聽見梁香梅說有人找,從裡屋走了出來。
領頭的人問:“你是梁雙樹?”
領頭的人說:“我們是縣紀檢委的,走,領我們看一下你養豬的地方。”
梁雙樹把三個人準備領到後院去看,剛走到後院門口,領頭的人站住了腳,給另外兩個人說:“好了,豬圈裡太臭了,在這兒看一下就行了,你兩個看,哪不是豬圈麼!梁雙樹養豬了,走,回。”
三個人走了。
何秀珍問:“你死老漢唱得是哪出戲?”
梁雙樹還沒有來得及回答老婆的問話,看着身旁的醫生發愣,何秀珍說,是她請來醫生給他看看,是不是腦子受吃虧了。梁雙樹趕緊跟那個醫生說,沒事沒事,自己隻是頭暈,現在好了。然後,給了醫生五塊錢,讓醫生走了。
梁香梅母女仨跟着梁雙樹進了門,問事情經過,梁雙樹牛起來了,說:“我是豬腦子,你還問我哩?黃西亮說有人舉報咱家沒養豬領養豬補貼,通過這事想把他扳倒,縣紀檢委要調查,叫我回來紮個豬圈,借幾架子車豬糞,做做樣子。調查這事的人是他的鐵哥們,隻要有個豬圈,豬圈裡有豬糞就行。如果問養的豬咋了,就說豬得猛病死了。把他家的,調查的人連豬圈跟前都沒去,哎,世事該瞎哩。”
何秀珍說:“那你為啥不給我和香梅說?我看把你氣成神經病了。”
梁雙樹說:“黃西亮專門叮咛,誰都不能說,說的出了事,跟我擱不下。再說,你的嘴跟蒸馍的爛籠一樣,一圓圈跑氣,我敢給你說?”
梁香梅說:“黃西亮父子兩個人交不過,給他幫的這忙弄啥麼?”
梁雙樹說:“你瓜娃些,黃西亮早都給你大把圈套設下了,說不幫他過這個坎,他不了結你和他兒子的婚事。”正說着,嘶地一聲,屁股疼起來了。
梁香梅趕緊問:“大,你這是咋咧?”
梁雙樹把自己差點被迷暈,後來在車站上打小偷等詳說了一遍,聽得何秀珍母女三人心驚膽顫,又為梁雙樹的為那個老漢讨回錢包而高興。梁香梅說:“大,沒想到你還是個見義勇為的老英雄!”
梁雙樹高興得笑了,覺得自己在黃西亮面前丢盡的自尊,在老婆和女兒面前找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