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時拾史事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嚴禁轉載
作者:細雨絲竹,又名淺樽酌海
“一邊是知縣,一邊是當地衛所指揮,就不能和衷共濟、齊心協力報效君父嗎?”新春佳節剛過,大明朝大理寺卿王槩大人匆匆閱畢一份卷宗,不禁喟然長歎,“雙方孰是孰非?還須細細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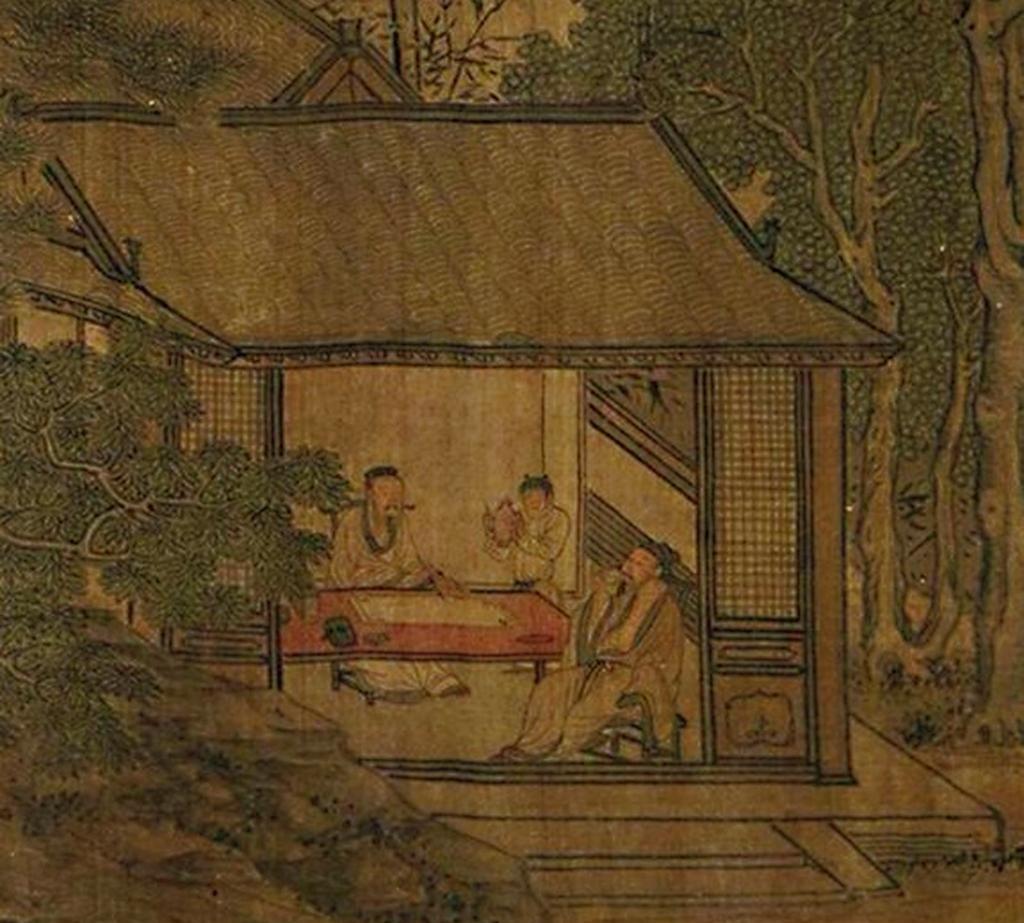
時維明憲宗成化年間(公元1465-1487年),天津衛寶坻縣(今天津市寶坻區)知縣陳讓報稱:【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農曆八月二十九日,本地商販包鑑、王全等人驅使幾頭驢子、騾子,連夜運送一批鄉間土布前往“劉宋家莊”售賣。
行至天明時分,這隊商旅在一處草場停下歇腳、喂牲口。不防兩條大漢騎着高頭大馬沖過來,包鑑一行還沒醒過味來,那兩人已張弓搭箭堵住來去道路,兇神惡煞似地悶喝兩聲道:“敢叫,殺了!”(注:史料原文如此。)“留下買路财!”包鑑、王全等手無寸鐵,未免懼怕箭矢無情,便不敢呼救。兩名強盜将驢騾馱運的布匹拎到自己的乘馬上,揚長而去。
稍後,包鑑、王全等人驚魂初定,掐指一算此行蒙受的損失,心痛不已,大不甘心,因互相打氣,騎着驢子攆上去。他們追到“陳家莊”,向行人打聽強盜的行蹤。行人答,方才的确有兩個騎馬馱布的男子途經此地,卻不是陌生面孔,乃是本鄉熟人,一個名叫“梁智”,另一個名為“孫青”,都是給衛所季指揮家看守管理田莊的。據行人說,梁智、孫青二人騎着馬、馱着布,馳往“張家莊”去了。
包鑑、王全在陳家莊有一個昵稱“薛二”的朋友,當即把剩餘的行李、多餘的驢騾托付給薛二家看管,借得馬匹、弓箭,趕着兩頭備用的驢騾,朝張家莊方向追趕,沿途搜尋、探聽梁智、孫青的動靜。
半路上,包、王二人獲悉,梁智、孫青正在張家莊福山家開設的小飯館内用餐,聽說吃完飯再回季指揮家的田莊。包鑑、王全火速議定一條“守株待兔”之計,趕到“林亭口”熟人尹良家寄存好弓箭,換了一身衣服做僞裝,另借到豬鈎一把、木棍一根,潛行至“林亭口”小河邊,埋伏在石橋旁,張網以待梁智、孫青二人。
候至申時,酒足飯飽的梁智、孫青果然騎馬抵達小河邊。包鑑、王全趁他們下馬過橋(弓箭置于馬背)、疏于防範,立即行動。包鑑持木棍攔截梁智,王全用豬鈎把孫青鈎倒痛毆,緻孫青暈厥。在扭打過程中,馬匹馱負的布料散落在石橋旁的一片莊稼地裡,包鑑、王全旋即合力制服梁智,随後将梁智、孫青捆縛結實,呼喚本村“火甲”楊增等人前來驗看。包鑑、王全告訴楊增:“這兩個人幹起強盜的勾當,在草場劫奪我們的布匹,被我們追到這邊尋拿住。”
“呃?”楊增感覺哪裡不對勁,“孫青家的田産就在此處,便是你們布匹掉落的那塊地——他和梁智在自家田産周遭打劫鄉鄰?聽起來怪怪的……”
“包鑑、王全無理傷人,又血口噴人!”梁智叫道,“我和孫青給季指揮看管莊子,要田有田、要房有房,鄉裡鄉親的擡頭不見低頭見。衆所周知犯強盜之行必死,我們不瘋不傻,怎會有福不享、别着腦袋打他們那點土布的主意?”
楊增左右為難。包鑑、王全提出,連人帶贓一并送縣衙公斷,真僞自明。楊增思忖,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就按包鑑、王全的提議辦吧!
經寶坻縣衙審問,梁智、孫青改口承認了包鑑、王全的指控。】以上來自寶坻縣知縣陳讓的報告,内容依據包鑑、王全、楊增等人的證詞。據此,有司決定對梁、孫二人處以斬立決。但到了複核階段,梁智、孫青在季指揮的支援下翻供,【訴稱他們早前為季指揮的田莊丈量土地,與知縣陳讓相中的田産劃界,發生一些争議,彼此結仇。按梁智、孫青的說法,成化元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們在“劉宋家莊”趕了早集,回程在“張家莊”福山家的飯館吃好飯,打算去“陳家莊”照看一下孫青家的田地,再回季指揮家的莊子料理事務,自始至終不曾在草場遇見包鑑、王全一行,更别提搶什麼土布。
傳回途中,他們下馬過橋,恰巧看見王全、包鑑等在孫青的田邊歇息,行李、布匹随随便便扔在孫青的地裡,壓倒了莊稼,驢子、騾子在田間亂踩亂拱,王全、包鑑也不管,隻顧自己吃幹糧、吹大牛。孫青十分不悅,黑着臉上前呵斥。
“你跟着季指揮吃香喝辣,跟驢子、騾子計較這點子糧草幹嘛?”王全、包鑑反唇相譏。雙方言語不合,口角不斷,繼而上升到“踩打”。梁智、孫青稱,他們把弓箭放在馬背上,此時也沒有取弓箭助戰,“想着畢竟不是大事,要有分寸。”梁智、孫青表示,誰知王全、包鑑不講分寸。那個王全,摸出随身攜帶的防身豬鈎,打傷孫青,造成孫青昏迷。梁智找王全理論,王全、包鑑抵賴,反将梁智按倒綁上,誣陷梁智、孫青搶劫在先,詭稱本方是“擒拿強盜”!後來楊增趕到,聽從包鑑、王全的主張,将梁智、孫青執送寶坻縣。
“楊增他們不知我二人與寶坻縣知縣陳讓有仇。”梁智、孫青說,“陳讓一看我們惹禍上身,樂不可支,哪裡需要問啥青紅皂白?一通嚴刑拷打,逼得我二人不得不低頭,違心承認。包鑑、王全也是歪打正着!至于那幾份幫包、王兩人佐證說辭的所謂證詞,必是陳讓指使小喽啰們炮制的。他是知縣,小百姓誰不怕他?他陳讓想弄出幾個證人,什麼行人啦、薛二啦、尹良啦,那不是手到擒來?”】
“此事徒有自相沖突的證言,毫無客觀證據,事實不清不楚,駁回。”大理寺卿王槩氣憤地擲下了紙筆。王大人雖然沒有直說,事情的真相其實是比較清晰的。第一,從雙方的陳述均可看出,包鑑、王全、梁智、孫青是生活在相鄰莊子的鄉親,人地兩熟,依陳讓報告的說辭,任意遇到一個行人都認識梁智、孫青,假如梁智、孫青真的在草場仗勢強搶包鑑、王全的土布,包鑑、王全肯定能認出他們。然而,按陳讓的報告,包、王二人遭劫時竟然不認識(沒有認出)梁智、孫青,簡直匪夷所思,根本是“揣着明白裝糊塗”。
其次,沒聽說陳家莊“林亭口”小河石橋是從“張家莊”福山家飯館通往季指揮家田莊的必經之路,包鑑、王全為什麼特意在此地設伏?難道他們未蔔先知,算準梁智、孫青離開張家莊之後,必将路過“林亭口”小河?
第三,據陳讓的報告,包鑑、王全聲稱他們為了追捕“強盜”,先在陳家莊借得馬匹、弓箭,顯然是力求與“強盜”勢均力敵,爾後探知“強盜”的身份,又将弓箭寄存在尹良家,改換豬鈎、木棍,友善在林亭口小河石橋伏擊。貌似他們挺會随機應變的,可問題是,他們如何預知梁智、孫青一定會下馬過橋、并将弓箭留在馬背上?
最後,以經濟條件、在本鄉的地位而論,梁智、孫青也完全沒有理由為着一批專供農村集市販售的土布甘冒“斬立決”的風險。是以,綜上所述,這件事的經過應該是:
【如同本系列前期文章(例如《明代富豪挽救落難美女并納為小妾,數年後卻被官府嚴懲,原因何在?》一文)一再闡述的一樣,明代中後期豪紳貴族大肆兼并土地,“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現象普遍存在,譬如本文中的知縣陳讓與衛所季指揮,因田土之争結仇,陳讓對季指揮的“狗腿子”梁智、孫青“恨烏及屋”。
成化元年八月二十九,包鑑、王全趕着驢騾馱運土布去“劉宋家莊”售賣,途中并未在草場遇劫,隻是在陳家莊“林亭口”小河畔孫青的田邊休息,放縱驢騾、亂放貨物,損壞孫家的莊稼。不料孫青正好在梁智陪同下來自家田裡照看,王全、包鑑的行徑被他們抓個正着。
接下來,雙方沖突,王全打暈孫青,梁智揚言要報官處置。王全、包鑑畏懼,幹脆反咬一口,将自己之前散放在孫青田裡的布匹捏稱為先被梁智和孫青劫走、後在搏鬥期間從後者的乘馬上滾落打散在地。
及至縣衙介入,知縣陳讓一看,真是“天助我也”,将對頭季指揮的兩條看門狗——梁智、孫青送入他的虎口,少不得排兵布陣、物色“證人”,捏造一篇細節豐富的“事實”,報仇雪恨。不過,季指揮也不是吃素的,給梁智、孫青撐腰,翻雲覆雨,據理力争,終于反敗為勝。】走筆至此,筆者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假設我們穿越回明朝,會過什麼樣的日子?”
我們喜歡品評古代帝王将相的英雄事迹,暗暗代入他們的人生巅峰,指點江山、呼風喚雨,同時對古代普通人的生存狀态漠不關心——即使普通的勞動者是古人中的絕大多數,而我們自身也分明是普通的勞動者(适用于大部分人)。我們有時會忘記帝王将相和萬兆黎庶都是曆史的創造者,正史不僅僅屬于大人物”。平凡古人打拼奮争、努力生活,經曆悲歡離合,繁衍、傳承,他們生存過的痕迹無論幸或不幸,也是正史。
假如我們穿越回明代,成為朱元璋、朱棣、常遇春、王陽明、徐階、張居正……的機率實在是微乎其微。可以說,就連成為梁智、孫青,給“衛所季指揮”看守田莊,都是走了鴻運。穿越者最大的可能是成為田莊周邊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農夫,如果時運不濟,未知哪天就會被季指揮或陳讓圈走賴以存活的一畝三分地。且看梁智、孫青落難,有季指揮搭救;當穿越者作為一個明朝農夫落難,誰來搭救?探究此類問題,就是本系列深翻故紙、嘗試關注明朝普通人命運的動因所在。
作者簡介:細雨絲竹,又名淺樽酌海,文史控、推理迷、言情癡、考據癖。主要作品有唐代曆史背景小說《神探王妃》、《魚玄機》等,均已出版或簽約出版。
本文參考資料:明代王槩《王恭毅公駁稿》、《明史》等。
圖檔來源于網絡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