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惡、性善抑或性樸:
荀子人性論重探
廖曉炜
華中科技大學哲學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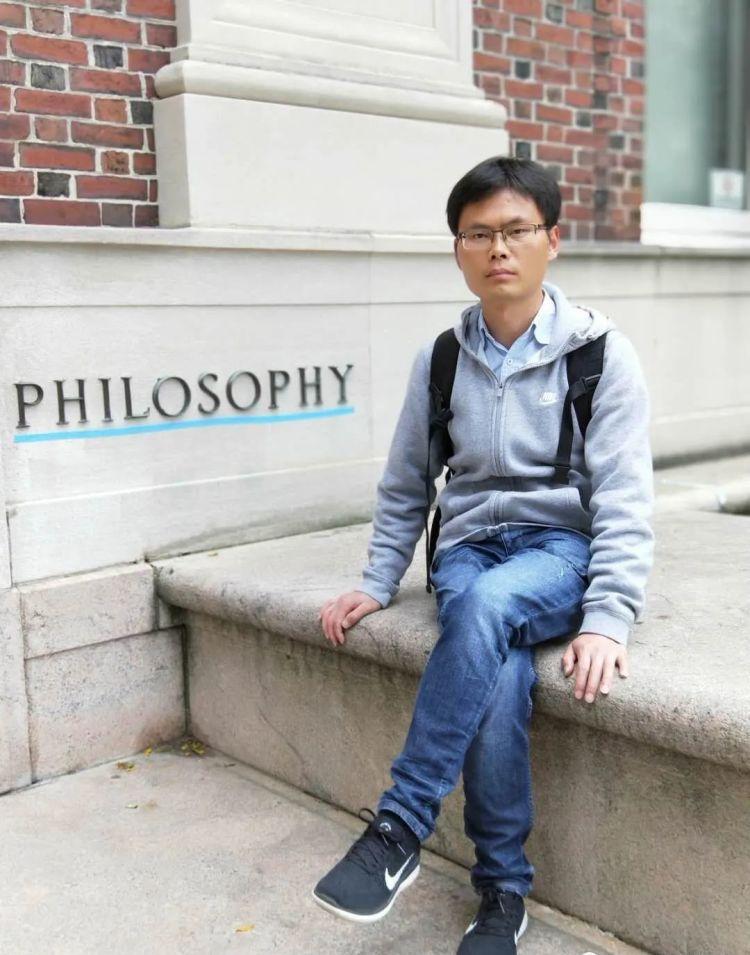
作者授權 儒家網 釋出
原載《中國哲學史》2020年第6期
摘 要:以性僞之分為邏輯前提,荀子認為在沒有僞的作用與幹預的自然狀态下,人性與惡之間具有必然性的關聯,這可說是荀子言性惡的确切意涵。此說既是荀子駁斥孟子性善論的理論基礎,也是其論證禮義之必要性與國家起源諸說的理論前提,因而最能突出荀子人性論的理論特色。荀子思想中所包含的弱性善說、性樸說與其性惡論分屬不同的理論層次,互相之間更無任何沖突可言。本文認為,在明确荀子性惡論之真實意涵的前提下,以性惡論定位荀子的人性論仍是最合理的做法。
關鍵詞:荀子 性惡 性善 性樸
近年來試圖在性惡論之外,重新定位荀子人性論的新說層出不窮,其中以弱性善說與性樸論的影響最大。[1]表面來看,這兩種說法與性惡論之間存在明顯的沖突,無法并存,且也都有一定的文本依據。如此一來,荀子的人性論似乎顯得十分模糊,而非一套成熟的、論理嚴密的人性論述。
但事實并非如此,上述分歧乃學者混淆荀子不同說法之間的理論分際所導緻的結果。是以,本文嘗試在重新厘定荀子言性惡之确切意涵的基礎上,檢討弱性善說與性樸論的理論實質及其與性惡說之間的思想關聯,進而對荀子的人性論作一融貫性的解讀。
1、性僞之分:性惡論的邏輯前提
質疑性惡論者通常都不加檢討地預設了以下觀點:荀子言性惡乃是從價值上将人性的内容判定為惡。然而,按照學界的一般看法,荀子所言人性主要包含感官能力、生理欲望、心理反應這三者。此外,也有學者認為心知亦是荀子所謂人性的一部分。就價值的角度而言,人性的這些内容,大體上都是中性的,無法将其判定為惡,這正是不少學者認為荀子主性樸論的重要原因。
不止如此,荀子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認人性中包含有類似于道德情感的成分,如其在《禮論》篇論及“吉兇憂愉”之情,即曰:“兩情者,人生故有端焉”。有學者認為此中“生”當讀為“性”,“端”即孟子“四端”之端,鐘泰由之認為:“是荀子亦未嘗不知性之有善也。”[2]如此一來,性樸、性善兩說在《荀子》中似乎都能找到相應的文本根據。
那麼,即便人性中含有惡的成分,荀子的性惡論作為一全稱判斷在邏輯上也是不周延的。[3]然而,荀子素以論理謹嚴著稱,何以其論人性會如此混亂?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荀子言性惡非“以惡說性”,亦即并非從價值的角度将人性的全部内容判定為惡。那麼,荀子言性惡的理論旨趣究竟何在?
為說明這一問題,必須引入荀子的“性僞之分”。學界對荀子思想中性僞分合的問題已有很好的研究,[4]本文僅由之以明性惡論的理論旨趣。荀子對“性”與“僞”這兩個觀念均有十分嚴格的界定。何謂“性”?“生之是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和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正名》)
這一界定包含兩層意思:1、我們的生命結構中一切生而本有者,均可歸之于性,如感官、本能、心理結構等;2、生而本有者的作用與表現如具有自發性和直接性,乃可稱之為性,《性惡》篇以“目可以見,耳可以聽”、“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等描述性,正就此而言。性的這兩層含義之間,頗類于一種體和用的關系。
“僞”同樣也有兩層含義:“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正名》)換言之,僞的第一層含義是指心的思慮及由之所引發的行為能力的表現;僞的第二層含義則是指心之思慮的累積與行為能力之表現的熟習所成就者,綜合荀子的相關論述,這主要是指具有穩定之行為傾向的人格與制度規範亦即禮義,後者主要指聖人之僞。
從性惡論的角度來看,性僞之分的理論意涵在于:源于性的行為表現先天地具足于人的生命結構當中,無需後天人為的作用和幹預,即可“現成地”表現出來。換言之,這類生命活動對人而言,“不可學、不可事”,也“不必學、不必事”;其是以可能的根據隻能由“人之性”來加以說明,亦即皆“生于性”也。
與之相對,人的另一類行為活動,如各種職業技能、道德實踐,亦即荀子所謂“陶人埏埴而為器”、“勞工斲木而成器”、人之知善為善等,必須經由後天的學習、事為,方能為人所掌握,進而在現實的生命活動中表現出來。這類生命活動是以可能的根據則在于“人之僞”,亦即皆“生于僞”也。質言之,上述區分也即“生于性”與“生于僞”之分。
總結而言,荀子的性僞之分乃是試圖将人類的全部行為活動,就其可能性根據之不同,區分為兩大類:一為“生于性者”,一為“生于僞者”。誠如有學者所已指出的,性僞之分乃貫穿《荀子》各篇的一項基礎性的理論區分。[5]那麼,荀子給出這一區分的理論意義及其必要性何在?這即涉及前文所謂荀子言性惡之理論旨趣的問題。
對荀子而言,善、惡是對人之行為表現的價值評判:“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矣。”(《性惡》)而人的行為表現,就其産生的根源而言,不外乎“生于性”與“生于僞”兩種。在荀子看來,二者之間是一較為嚴格的對分關系,換言之,二者指向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個行動領域。
那麼,一個合理的設想就是,如果要客觀地判斷人性與善、惡之間的理論關聯,則需要在理論上剔除與“生于性”者異質的成分,以保證人的行為表現完全是由人性所決定。如此,由人之行為表現的善、惡,即可判定人性與善、惡之間的内在的、本質性的聯系。否則,如果有異質成分亦即“生于僞”者的混雜,則無論以人性必然導向善或導向惡,都不可能是對人性的客觀真實的把握,因為此時人之行為表現的善、惡,很可能是源于“僞”或“性”與“僞”共同作用的結果。
是以,性僞之分的理論意義就在于:這一區分是客觀了解人性及其與善、惡之内在聯系的邏輯前提。荀子言性惡的核心旨趣就在于從理論上說明:在沒有“僞”的作用與幹預的前提下,人性與惡之間的必然性關聯,而非以惡說性。這一判定是否有充足的文獻根據呢?以下詳述之。
2、性與惡之間的必然性關聯:荀子性惡論新诠
《性惡》開篇闡明性惡之旨趣時曰:“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争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這裡的“必”字正表明性與惡之間具有某種本質性的聯系。問題是,性與惡之間的必然性聯系是如何确立的呢?學者一般都認為荀子言“必”的前提在于“順是”。因而,性惡往往被解釋為,人之性情,“順之而無節,則惡亂生焉”。[6]“必”字的重要性往往被忽視,也有學者将“必”字的含義弱化為“可能性”,亦即在“順是”的前提下,生而本有的性情或欲“可”引緻惡。[7]
為合了解釋上述“必然性”,先看《性惡》篇的另一段重要文字:
今當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強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當”為“嘗”之借字,當試,猶嘗試。[8]荀子這段表述的意思非常清楚:設若去掉一切經由後天人為所建構起來的引導、規範人類行為的因素,也即“僞”——君上之勢、禮義之化、法正之治、刑罰之禁,則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必然瞬間陷入互相争鬥的混亂狀态,這正是荀子所謂的“惡”:偏險悖亂。此中蘊含的理論意義,頗為豐富,可說者有以下數點:
1、隻有去掉一切後天人為因素的作用和幹預,才能真正“客觀地”了解和評價“出于性者”亦即純粹由人性所決定的行動,因為在此狀态下的人類行為表現可視為“人之性”的最直接、最本真的表達;2、若不嫌比附的話,上述無後天人為因素影響的人類生存狀态,實類于霍布斯所謂的“自然狀态”;3、在自然狀态下,亦即一切文化與政治制度尚未出現的狀态下,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必然導緻“惡”,荀子在《富國》《禮論》篇對此有更為具體細膩的描述。
以上乃《荀子》一書對“性惡”所作的最嚴格、清晰的描述。概括而言,荀子乃是以性僞之分為理論前提,試圖說明在完全沒有“僞”的作用與幹預的情況下,人性的真實狀态及其必然導緻偏險悖亂的後果。必須說明的是,所謂沒有“僞”的作用,并不是說在自然狀态下,人的一切行為表現都是無意識的。
相反,即便是在自然狀态下,人之追求自然情欲以及各種利益的滿足,也都必然是自覺的;換言之,其中必然有心之思慮作用的介入。而就荀子對“僞”的界定來看,心之思慮的作用即屬于第一義的僞。是以,嚴格而言,所謂沒有“僞”的作用,是指沒有後天養成的特定行為傾向以及人類後天所建構之價值規範、政治制度等,對人之行為表現的作用與影響,亦即沒有第二義之僞對人之行為表現的作用與影響。
事實上,如果我們細讀《性惡》篇,即可發現荀子對性惡的闡釋,基本都是在上述基本前提下展開的。如荀子曰:“順情性則弟兄争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順情性”與“化禮義”對舉即表明,前者是指人尚未接受禮儀的教化和引導,其行動完全由情性所決定,而其結果必然是人與人之間的争奪。
“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一段的論證,最終也歸結為“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所謂“無禮義”、“不知禮義”突出的也是自然狀态下,人性與惡(悖亂)之間的本質性關聯。
《性惡》後半部分将情性與禮義分而為二,進而說明性惡之必然與禮義之必要,表達的也是相同的意思。可見,荀子言性惡與自然狀态之間有其内在的關聯。在荀子看來,要真實呈現人性與善、惡之間的本質性關聯,隻有在沒有“僞”的自然狀态下才有可能。這可說是荀子嚴辨性僞以言性惡,在邏輯上必然得出的結論。
循此,我們也就不難了解《性惡》開篇所言之“必”的真正意涵。理論上,“順是”之說同樣預設了“自然狀态”或者說“沒有僞”這一理論前提,否則人之放縱自己的欲望會否導緻“偏險悖亂”,并無必然性。設想在一個有序而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下,人們也可以傾其所有以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而這會否必然導緻偏險悖亂,則十分可疑。但在自然狀态下的人,尚未接受師法的教化和禮義的引導,無政治制度的限制,其一切行動完全受自然情欲的驅使,如此必然導緻“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争矣”(《富國》)的後果。
若細讀整段文本,可以發現上述對“順是”及“必”的解釋,有其合理性:“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争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故必将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必将有”即表示“順是”乃是在無“師法之化,禮義之道”,亦即沒有“僞”的作用與幹預的情況下,人完全随順自然情性的要求而表現自己的行動,其結果必然導緻人與人之間的争鬥,亦即惡。
可以補充的一點就是,《性惡》篇常常提及的“順是”、“順情性”中的“順”字,學者多未能考察其思想史背景,事實上,荀子此說針對的正是孟子的性善論。孟子駁告子杞柳杯棬之喻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杯棬乎?将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杯棬也?如将戕賊杞柳而以為杯棬,則亦将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孟子·告子》)孟子道性善,強調順性而行即可為善,也即所謂“以性說善”。[9]荀子辟性善,雖未言及四端之心,但确是針對孟子此一思維方式而發。對荀子而言,如果理論上證成順性而為必然導緻惡,則孟子以性說善的性善論也就不攻自破。
荀子駁斥性善論,對性善有如下界定:“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樸而美之,不立其資而利之也。使夫資樸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性惡》)荀子的意思很清楚,性善說要能成立,必須要求在沒有後天人為因素的作用下,單就人性自身即可充分說明善是何以可能的,正如目明耳聰乃人性所本具,由之即可先天地決定現實中人之看與聽的行為。
如果人性自身足以說明善,則順性而行即可為善的想法乃有成立之可能。可見,荀子對性善論的駁斥與對性惡說的說明,遵循的是相同的思想原則:在沒有後天人為因素的作用下,順乎純粹的人性要求,其必然導向善還是惡?是以,若說荀子對性善論的批評完全是無的放矢,[10]似非客觀公允之論。
必須說明的是,《荀子》一書中所描述的“自然狀态”不應被了解為某種時間性的範疇,亦即将其視為特定的曆史階段。正如學界通常都将霍布斯的“自然狀态”視為“思想實驗”中使用的概念。[11]同樣,荀子哲學中的“自然狀态”也應被了解為一種“思想實驗”。
因為現實中的人類社會必然已經處于一定程度的文明狀态之中;同樣,現實中的人的行為表現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種社會制度和規範的影響。是以,我們不應将荀子哲學中的“自然狀态”或曰性惡看作是對現實中的人類生活經驗的“客觀描述”。荀子以自然狀态為背景言性惡,乃是試圖在思想觀念中剔除後天人為的因素亦即“生于僞者”,進而對人性之所是及其所必然引發的結果作出判定和估價。
質言之,自然狀态或曰性惡在荀子的思考中,首先是一理論的起點,由之從根本上說明禮義之于人類社會的必要性。但這也并非意味着荀子有關自然狀态的論述,完全是主觀的虛構。事實上,荀子歸諸“出于性”的活動,總是不同程度地表現于我們真實的生活經驗當中,所謂自然狀态,不過是排除掉人為因素後的一種純粹化或曰“理想化”的狀态而已。
誠如有學者已經注意到的,《管子》《墨子》、《商君書》等早期文獻中,均論及“人類初始無君臣之别”的自然狀态,[12]而荀子思考的特殊之處就在于,其将自然狀态與性惡說内在地關聯起來。這也使得荀子的自然狀态理論相較于《墨子》等的說法,更具理論效力。
尚須略作說明的一點是,荀子所謂人性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其闡述性惡時,則基本上專就人之“情性”而言。何以荀子言性惡,有意剔除人性中的其它内容,如所謂“目明耳聰”等等?這會否使得其性惡論不具必然性?由荀子對性、情、欲三者的界定:“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我們知道所謂情性實際上指的就是人的自然情欲。荀子單就人的自然情欲言性惡意在表明:自然狀态下,人之行為動機完全由自然情欲所決定。這并不意味人性的其他方面對人的行為完全不産生任何作用,而是說,唯人性中自然情欲的部分,才是人之行動的決定因。
澄清了荀子言性惡的真實意涵,以下當進一步說明性惡與性善、性樸之間的理論關聯,以對荀子的人性論做一整體性的定位。
3、荀子的人性論與性善說及性樸說
首先我們來看荀子的人性論與性善說之間的關系。這裡我們有必要區分兩種不同的性善說,一是荀子所界定且為其所駁斥的性善說,一是當代學者所了解的、并認為荀子思想也隐含的一種性善說。
前者是荀子以性僞之分為理論前提,嚴格界定的強的性善說,前文已有所論及;後者則是一較為寬松的說法,亦即,如人性中先天具有知善為善的可能性根據,即可說人性善,這是一種弱的性善說。清代以降持此說者衆,如戴震、陳蘭甫、羅根澤、李經元、梁啟雄、[13]勞思光、[14]傅佩榮、劉又銘、路德斌等,[15]均在不同程度上認為荀子思想中包含有弱的性善說。
依前文分析,強的性善說乃指單就人性自身即足以先天地決定善,換言之,如果說人之性善的話,那麼未經後天人為因素作用與幹預的資樸之性就應當是美善的。具體而言,人先天本有的心意能力,如能充分地決定善,有如目、耳之能先天地決定看與聽,則性善說乃可成立。但在荀子看來,性善說根本就與經驗事實不符,所謂“無辨合符驗”。若無後天之“僞”的作用,人性根本不能自發地提供充足的為善的動機。理論上,荀子要破除的正是這種強的性善說。
有學者或許會提出質疑,荀子似亦承認人先天具有某些自然的情感傾向,即便其本身尚非道德情感(moral feelings),但卻與道德“意氣相投”(congenial),[16]如荀子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禮論》)可見,荀子并不否認人有孝悌乃至愛同類的自然情感。
不過,這些情感本身尚不足以成為人在現實中為善的動機和根據。如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祿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性惡》)可見,與好利的心理及自然的情欲相比,孝悌等自然情感可謂十分脆弱,隻有經過“禮義之化”,這些自然的情感,才能轉化為真正的道德情感,而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也才有可能。
前文提及,荀子讨論喪禮時,特别指出人生而有“吉兇憂愉”之情,有學者因之斷定荀子亦主張性善。不過細繹上下文的意思,不難見出荀子仍以這些情感本身并不足恃:“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則是禮也,非順孰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禮論》)可見,要保證這些自然情感的表達為合宜,尚須外在規範也即禮義的形式性規定或曰道德習慣的重塑,[17]是以楊倞曰:“人雖自有憂愉之情,必須禮以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18]
是以,一方面自然情感的表達需要特定的儀節作為其外在的形式規定;另一方面,自然情感也隻有客觀化為禮義規範,亦即經由聖人之僞而生禮義制法度,凡衆才有可能在透過學習、事為,進而真正認知禮義規範的基礎上,肯認這些自然情感,以使之成為道德行動的動機,所謂“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守道以禁非道”(《解蔽》)。循此,對自然情感的肯定,并不會與荀子所肯定的性惡論之間構成任何沖突。因為自然情感轉化為道德情感,而足以成為道德行動的動機,仍以後天之“僞”亦即學習、事為為前提,而這已不可歸之于“出于性者”。
再看弱的性善說與荀子人性論之間的關系。荀子的确認為心先天具有知善進而引發相應的能力以為善的可能性,但這與荀子的性惡論之間也不存在任何沖突。為說明這一點,有必要對心在人之行為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具體的分析。
荀子言心,首先突出的是其主宰、裁斷的能力,所謂“天君”是也:“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天論》)人的認知與行動,其背後都有一主宰性的力量在起作用:“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于使者乎?”(《解蔽》)“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故口可劫而使墨雲,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解蔽》)
可見,對于一切“心智正常的人”而言,他的行為表達必然是自覺的,亦即是在心的思慮和主宰的作用下産生的,這也是荀子哲學中“僞”的基本含義:“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僞。”(《正名》)即便是在“自然狀态”下,人的行動也并非隻是自然情欲和本能的自發表現而已。[19]是以,《性惡》篇所謂“順是”或“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并非意指完全被動地由人之情欲來支配自己的行動,而是出于自己的主動選擇去順從人之情欲、滿足來自人性的欲望。[20]
心如何決定一行動,取決于其所認可的對象。在這一意義上,荀子認為治、亂或善、惡的關鍵在于“心之所可”,而非情欲本身。然而,“心之所可”的對象,并無任何先天的确定性和必然性,心既有認可合理之對象的可能,也有認可不合理之對象的可能:“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守道以禁非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解蔽》)可見,在荀子的思考中,主宰、裁斷之于“心”而言,乃是一較為“形式性”的能力,心如何裁斷、決定一具體的行動,由其所認可之對象的内容所決定:“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正名》)
就心與性惡論的關系而言,問題的關鍵在于:自然狀态下,心之所可的對象是什麼?對此,荀子有明确的看法:“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爾”;“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榮辱》);“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隆積矣”(《儒效》)。簡言之,在自然狀态下,心之所可者,唯利與情欲而已。《榮辱》《非相》《性惡》諸篇,皆以“好利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換言之,“好利惡害”正如耳目口鼻之欲一般,皆屬人性。
如此說來,自然狀态下,心不過是構成自然情欲自我滿足的促成因素而已,亦即心本身變成一“工具性”的存在。此時的“心”,有學者以“功能縮減的心”(functionally reduced mind)說之,頗能表達上述意涵。大意是,心在此狀态下,僅隻關切如何找到最有效的手段以使欲望得到最大的滿足。[21]如此,“心”也就完全喪失其作為“天君”的主宰性的地位,是以有學者曰:“但對于自然狀态下或說非曆史(ahistorical)的人,自由意志實同贅旒,不提也罷。”[22]就此而言,有學者認為荀子主心善說,[23]顯然與荀子思想的整體脈絡存在明顯的沖突和沖突。
更進一步,在自然狀态下,心甚至是人之為惡的促成因素。如荀子曰:“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盜,雲能則必為亂,察則必為怪,辨則速論。”(《儒效》)此即《性惡》篇所謂“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寬泛而言,知、勇、能、察、辨均可說是心之認知、主宰或曰意志諸不同方面之能力的展現,在自然狀态下,這些能力都可因人一味求利或情欲的滿足而為惡。
《修身》篇亦有類似的表述:“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志意、知慮亦即心之兩面,血氣則指自然生命的活動而言,所謂不由禮,也即沒有師法的引導和規範。這也是在強調,自然狀态下,不隻自然生命的活動會引發惡,心的作用還會進一步促使人去為惡。
依荀子的看法,心固然先天即有知善及引發相應的能力以為善的可能性,但這僅隻是一潛在的可能性而已,自然狀态下,這些能力根本無法确立起充足的為善的動機。且不說,自然狀态下,善或曰價值的标準尚未真正确立起來,即便是有了價值标準,心對價值标準的正确認識與認可,唯有經過艱苦的學習和修為的過程才有可能。
此是以荀子說:“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強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性惡》)這也正是荀子将人之為善視為“出于僞”者的理由之所在。由此我們可以說,在自然狀态下,這些先天的、潛在的知善為善的能力,根本無法對人的行動産生任何實質性的作用和影響。此是以荀子會認為,心在自然狀态下隻不過是自然情欲追求自我滿足的工具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荀子否認強的性善說而肯定心先天具有知善為善之可能性的看法,為漢代儒學所繼承和發展。如董仲舒以禾米之喻,強調“性有善質而未能為善”(《春秋繁露·實性》),即是對荀子之說的很好的概括。此外,《淮南子·泰族訓》亦有類似的說法。是以,就中國人性論史的角度而言,認為荀子亦可承認性有善質,或更直接地說,荀子思想中包含有某種較為弱化的性善說,[24]自然是可以成立的說法。
事實上,弱的性善說無人可以反對,因若不假定人性中具有知善為善的可能性條件,一切後天的教化,皆無可能。是以,弱的性善說并無多少理論意義,近乎一種常識。此外,由前文的分析我們知道,即便肯定弱的性善說,也無法改變自然狀态下,人性必然導向惡的基本判定,換言之,弱的性善說與荀子的性惡論之間并無理論沖突,二者可以并存。
近年來,亦有學者力主荀子的人性論為性樸論,本文對此說亦當稍加辨正。荀子确曾以“樸”來界定“性”,在上文提及的《禮論》篇有關“吉兇憂愉”之情的論述之後,荀子曰:“故曰:性者,本始材樸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
細讀上下文,我們不難發現,荀子這裡是将人所生而本有的自然情感,歸之于性,并以“本始材樸”說之,而“僞”即指禮而言。自然情感的合理、恰當的表達,不能沒有禮的規範,如此方能成就“行義之美”,也即所謂的“性僞合”。相較于“文理隆盛”之“僞”而言,作為性的自然情感當然可說是質樸的、未經修飾的。
此外,《性惡》篇亦以“樸”、“資”來說“性”:“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樸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荀子反對強的性善說,以為先天本有的資質,無“自美”之可能,因而後天之“僞”必不可少。綜合以上說法,不難見出,荀子以“樸”來界定“性”,首先要強調的是人性的生就義與質樸義,亦即突出“性”乃未經後天人為努力之作用與影響的“本來面目”這層含義。本質而言,以樸說性,乃是在性僞之分的理論前提下,對“性”之形式性義的揭示。換言之,在性僞之分的前提下,由性乃生而本有之先天性即可分析出性為“樸”這層意思。
事實上,正如有學者所敏銳觀察到的,“樸”本來就有名詞和形容詞兩種用法,前者指未經發展的材質,後者又分為描述和評價兩義:“未經修飾的”、“未經發展的”可說是對事物所處狀态的描述,“中性的”、“無善無惡的”則是對該狀态的價值評價。荀子以本始材樸四者言性,是在名詞的意義上使用“樸”字。[25]
這其實正是本文所謂的,荀子以樸說性意在強調性的生就義與質樸義,而非對其作價值性的評判。持性樸論者為證成己說,反駁荀子主性惡的基本看法,其實是在評價義上來了解“樸”字。這種語義上的轉換是否具有合法性,其實需要更加強有力的分析和論證。
事實上,《荀子》兩次以樸說性的表述中,均未明确從“中性的”、“無善無惡的”這一價值評判的角度來使用“樸”字。而就《荀子》為數有限的“樸”字的用例來看,既有消極評價的用例,如荀子言事暴君當“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食餒人”(《臣道》);也有積極評價的用例,如“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強國》)。
是以,将荀子所言性樸解讀為人性是無善無惡的、中性的,已非荀子的本意,至少是對荀子之說的引申。就本文的立場來看,正因為荀子人性論的重心不在于對人性做價值性的評判,荀子以樸言性之樸的價值意涵并不明确,也就不那麼費解了。當然,以性為樸,與自然狀态下人性必然導向惡的判定同樣無任何沖突沖突之處。
小結
綜上,荀子言性惡乃試圖說明,在沒有“僞”的作用與幹預的“自然狀态”下,人性與惡之間的必然性關聯,而非從價值上判定人性是惡的。弱性善說隻在強調人性先天具有知善為善的潛在可能性,此說當為荀子所認可,不過這一近乎常識的看法,并無多少理論意義,無法突出荀子人性論的理論特色,也與荀子的性惡論毫無沖突之處。
荀子以樸說性僅隻表明性的形式義,亦即生就義與質樸義,而非意在強調人性于價值上是中性的,事實上,性僞之分即蘊含了性樸這層含義,是以其與荀子的性惡論之間同樣無任何沖突之處。可見,就荀子思想本身而言,真正具有理論意義的仍是性惡論,此說既是荀子論述禮義之必要性、國家起源諸說的理論起點,同時也是反駁孟子性善論的理論基礎。
注釋:
[1] 當然,更為徹底的一種看法則是否定《性惡》篇的真實性,如日本學者金谷治、美國學者孟旦(Donald Munro)以及周熾成等均持這一立場,唯這一看法仍缺乏足夠的證據,朱曉海、李哲賢、黃芸等已從文獻學以及義理的角度,作出了有力反駁,是以本文一仍其舊,肯定《性惡》篇足以代表荀子本人的看法。相關讨論參考朱曉海:《〈荀子·性惡〉真僞辨》,收入《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9,第837-858頁;李哲賢:《荀子人性論研究在美國》,《政大中文學報》第八期(2007年12月);黃芸:《〈荀子·性惡〉辨》,收入張西平主編:《國際漢學》第26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第270-288頁。
[2] 王天海:《荀子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85頁。
[3] 廖名春:《荀子新探》,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78頁。
[4] 鄧小虎:《荀子的為己之學:從性惡到養心以誠》,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50-69頁。
[5] 顔世安:《荀子、韓非子、莊子性惡意識初議》,《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
[6] 牟宗三:《名家與荀子》,台北:台灣學生書,1979年,第223頁。
[7] 馮耀明:《荀子人性論新诠》,《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14期(2005年6月);東方朔:《合理性之尋求:荀子思想研究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0頁。
[8]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40頁。
[9] 廖曉炜:《以善說性抑或以性說善:孟子性善說新解》,《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70卷第3期。
[10] 徐複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第208頁。
[11] Juhana Lemetti,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Hobbes’s Philosophy,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2012, P.318.
[12] 蔣年豐:《文本與實踐(一):儒家思想的當代诠釋》,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285-286頁。
[13] 廖名春:《荀子新探》,第78頁。
[14]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台北:三民書局,1987年,第335頁。
[15] 蕭振聲:《荀子性善說獻疑》,《東吳哲學學報》第34期(2016年8月)。
[16] David B. Wong, “Xunzi on Moral Motivation”, in Virtue, Nature, and Moral Agency in the Xunzi, Edited by T. C Kline Ⅲ and Philip J. Ivanhoe,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150.
[17] Bryan W. Van Norden, Virtue Ethics and Consequentialism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7.
[18]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第366頁。
[19] 唐端正:《先秦諸子論叢(續編)》,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9,第214頁。
[20] 戴華:《荀子性惡論》,載林從一主編:《哲學分析與視域交融》,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0年,第165-187頁。
[21] 戴華:《荀子性惡論》,第177頁。
[22] 朱曉海:《荀子性惡論論證的商兌及疑義探索》,載丘慧芬編:《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台北:允晨文化,2005年,第224頁。
[23] 梁濤:《荀子人性論辨正——論荀子的性惡、心善說》,《哲學研究》2015年第5期。
[24] 劉又銘:《荀子的哲學典範及其在後代的變遷轉移》,《漢學研究集刊》第3期(2006年12月)。
[25] 黃芸:《〈荀子·性惡〉辨》,第2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