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詩”問題,曾被學界目為《詩經》學史上四大“公案”之首。曆來争議較多,且迄今尚無定論。 每個曆史時期都有一定的主導觀點, 而同一時期又不可避免地夾雜着不同觀點之争論。孔子未曾删《詩》一說相比起來可能更可信。當然在論述之前,我們首先來梳理一下“孔子删詩”問題的前世今生……
所“删”何“詩”
“孔子删詩”一般認為肇始于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雲:“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儀,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由此可見,所删之詩皆為《詩經》之詩,那麼對《詩經》進行溯源了解就顯得尤為必要。
所謂《詩經》是大陸第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約前11世紀至前6世紀近500年間的305篇作品,其豐富的内容被認為是上古社會的百科全書。《詩》明确的創作年代不可考,學界大緻論定其中最早的創作于西周初期,最晚的創作于東周的春秋中葉,總共305篇。這些詩按樂調分為《風》、《雅》、《頌》三大類。孔子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子晚年棄政返魯,創辦鄉學,整理六經,教書育人。他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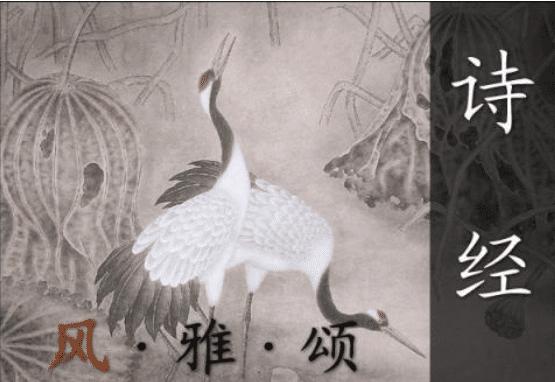
《詩經》
經逢秦朝焚書坑儒,由學者傳誦得以儲存,至漢代奉為經典。當時傳授《詩經》的有四家:齊人轅固生傳授的被稱為“齊詩”,魯人申培公傳授的被稱為“魯詩”,燕人韓嬰傳授的被稱為“韓詩”,魯人毛亨傳授的被稱為“毛詩”,簡稱齊、魯、韓、毛。齊、魯、韓三派,在西漢十分盛行,在朝中立有博士,成為官學,屬今文經學;“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到了東漢,儒學大師鄭玄為“毛詩”寫了《毛詩箋》,學習“毛詩”的人逐漸增多,漢代經今、古文之争,“毛詩”取得重要學術地位。以後其他三家先後失傳,隻有“毛詩”流傳到今天,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詩經》。但是,這樣一部偉大的著作,由于年代久遠,缺乏可靠材料,至今在許多方面仍衆說紛纭,無法作出判斷。其中,孔子是否删過《詩》就是一個懸案。
孔子删《詩》之争論
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當中其實并未明确提出“删詩”說。隻是叙述孔子将古代流傳下來的3000多首詩,經過“去其重”,僅剩符合禮儀标準的305篇,并使之合乎《韶》《武》《雅》《頌》之音。
到東漢,班固在《漢書叙傳》中說:“伏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篹書删詩,綴禮正樂。”“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與他同時的王充也說:“《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删去重複,正而存三百篇。”這是首次明确提出删詩說。
鄭玄
鄭玄箋《毛詩》時,贊成孔子删詩的觀點,如鄭玄《六藝論》雲:“孔子錄周衰之歌,及衆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于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直至唐初陸德明,其《經典釋文序錄》仍然認為:“孔子最先删錄。既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十一篇。”亦認同孔子删詩的觀點。從整體上看,在唐孔穎達之前,大多學者多信奉孔子删訂《詩經》,肯定孔子删《詩》,認為孔子這樣做是為後世立教,記載時事,編撰曆史,為現實的政治提供借鑒功德之舉。
至唐初孔穎達,始對孔子删詩之說明确提出質疑。其在《詩譜正義序》中說:“《史記·孔子世家》雲:‘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這是從逸詩數量上進行邏輯推理,認為《詩經》之外的逸詩數量極為有限,進而說明孔子并沒有大規模的删詩之舉。孔穎達還進一步加強此說。《詩譜序》孔氏正義雲:“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于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為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也就是說,《詩經》之“正詩”不是孔子所删錄,而應歸之于孔子之前的國史和太師。
自孔穎達明确提出孔子不曾删詩的觀點以後,在詩經學領域影響非常大,進而引發了一場持續一千多年的學術公案,自宋及清,論辯往複不絕。南宋鄭樵說:“上下千餘年,《詩》才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并得之于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于删也。删《詩》之說,漢儒倡之。”朱熹則認為,“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删與不删”,“孔子不曾删去,往往隻是刊定而已”,“那曾見得聖人持筆删那個,存這個,也隻得就相傳上說去”,故基本認定孔子并沒有删訂《詩經》。南宋王柏亦激烈反對孔子删詩說,他認為“左氏載季劄之辭,皆與今《詩》合,止舉《國風》,微有先後爾。使夫子未删之《詩》,果如季劄之所稱,正不待夫子而後删也”。此後擁護孔穎達觀點者甚衆,除了上述四人外,還有宋代呂祖謙,明代黃淳耀,清代江永、朱彜尊、王士祯、趙翼、崔述、魏源、方玉潤等,以及近代以來梁啟超、胡适、顧颉剛、錢玄同等。
孔穎達
當然,反對孔穎達觀點者亦代不乏人,如北宋歐陽修就公開贊成孔子删詩的觀點,并對司馬遷的說法作進一步修正完善。他在《詩本義·詩圖總序》中說:“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 以餘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采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 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明代盧格認為:“西周盛時,環海内而封者,千八百國,使各陳一詩,亦千八百篇矣。載于經者,惟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桧、曹十一國,皆春秋時詩,其他亦無所錄。孟子‘詩亡’之論,其有慨于此乎?”
清初顧炎武亦認為:“孔子删《詩》,是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選其辭,比其音,去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删也。”趙坦雲:“删《詩》之旨可述乎?曰:‘去其重複焉爾。’”在這裡趙坦提到了“去其重”,說明他認為孔子删掉了重複的詩篇,從中可說明孔子有删《詩》的可能性。除了歐陽修等人外,其他贊成孔子删詩者尚有宋代邵雍、程灏、周子醇、王應麟,元代馬端臨,清代範家相等。而之後,現代學者當中也有很多支援“孔子删《詩》說”。他們有的是完全同意司馬遷的觀點,認定孔子是根據儒家的禮儀規範,将古詩三千餘篇删成今本《詩經》三百零五篇;有的認為孔子是删了《詩》,但他是做将不同版本“去其重”的工作。
綜上所述,删與未删,唇槍舌戰,論戰了兩千多年,至今争論不休。
孔子未删《詩》
兩者相較而言,孔子未删《詩》說可能更可信。為什麼呢?
1.對于“季劄觀樂”的記載,這是讨論“孔子删《詩》說”時無法回避的問題
季劄觀樂,是論家用以駁難“孔子删《詩》說”征引最多且最有力的證據。季劄觀樂,原出于《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劄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于周樂。”依據《史記 孔子世家》,孔丘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至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季劄觀樂”,孔丘才虛九歲。一個八、九歲的小孩,能把古詩三千餘篇删定為三百篇,恐怕是難以想象的。
季劄
2.孔子自言“詩三百”,可以證明當時《詩經》已成型
在《論語》當中記錄了孔子兩次說到“詩三百”。一次是《為政篇》雲:“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另一次是《子路篇》雲:“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清朱彜尊說:“詩者,掌之王朝,頒之侯服,國小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删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詩至于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于十三國矣。而季劄觀樂于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為删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矇瞍,安能遍其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頒之侯服者,亦止于三百餘篇而已。”從這裡可以看到,孔子自言“詩三百”足以證明當時《詩經》已經成型,故孔子未曾删《詩》。
3. 《詩經》中有很多與孔子“禮儀”标準不同的詩句
正如孔子在《論語》中所說:“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同時孔子還說過:“行夏之時,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可見鄭聲在孔子心中是靡曼淫穢,是不典雅之物,那麼為什麼在《詩經》中還有很多與孔子“放鄭聲”、“鄭聲淫”不同标準的内容出現呢?
孔丘
同樣在《詩經》當中有寫情人之間幽會親昵的《邶風 靜女》;有寫情人歡樂見面的《鄭風 溱洧》;有寫兩情相悅野合的《召南 野有死麕》;有寫情侶飽含思念深情的《王風 采葛》;有寫深情女子想念男子的《鄭風 子衿》;有寫情人之間吵架鬧别扭的《鄭風 狡童》;有寫表現意中人難以親近的《秦風 蒹葭》;有寫痛苦失戀的《召南 江有汜》;有寫遭到家長幹涉的《鄭風 将仲子》;還有反抗家長幹涉的《王風 大車》。像這些詩篇,是和儒家提倡的“禮義”标準背道而馳的,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互相沖突的。那麼一心一意按照儒家思想去踐行主張的孔子為什麼不删去這些詩篇呢?
4. 逸詩的數量問題
清人朱彜尊認為春秋時期,庠序之諷誦,士大夫賦詩成風,所用典籍記載多出于今本《詩經》,而孔子不可能具有如此之能力及影響力去删《詩》。同時孔穎達所謂的“孔子所錄,不容十去其九。馬遷所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其理論實質是以現存先秦典籍逸詩的多寡來否定孔子删《詩》。相關情況可以參看趙翼在《陔餘叢考》“古詩三千之非”條中稱,《國語》引詩凡31條,引逸詩僅1條。《左傳》引詩217條,逸詩13條。是以趙翼總結說:“若使古詩有三千餘,則所引逸詩,宜多于删存之詩十倍,豈有古詩十倍于删存詩,而所引逸詩,反不及删存詩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詩三千之說,不足憑也。”同時朱彜尊在《經義考》、魏源在《詩古微》、趙坦在《寶甓齋劄記》中也提出對逸詩幾種可能的看法。按照趙、魏二人所揭,《詩》是前人在輯集先秦典籍的過程中自然逸失且數量很少,并非孔子删去;也有從根本上否定孔子之後沒有逸詩,是以孔子未曾删過《詩》,即“夫子有正樂之功,無删詩之事。”
簡而言之,孔子未删《詩》源于《史記 孔子世家》中的話“古者詩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其否定的理由概括來說有如下四點:第一,依據《左傳》記載,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吳公子劄來聘,請觀周樂”一事中所歌的詩與現在通行的《詩》的次序大緻相同,而據現存的資料看,其年孔子八歲,根本不可能删《詩》。第二,《論語》中有兩處提到“《詩》三百”。可見三百篇早就是定數,不是孔子删後定的。第三,《史記》上所說孔子删《詩》隻“取可施于禮義”的,現在《詩經》中還儲存着“淫詩”,可見孔子未删。第四,《左傳》、《國語》以及諸子著作中引詩大多與今同,逸詩數量很少。但無論是删與未删,都不能抹煞曆代學者在《詩經》方面的重大貢獻。所謂真理越辯越明,正因為有了諸儒有理有據的發難之功,才有了曆代學人對這一問題所展開的深入論難和考辨,進而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整個《詩經》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