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三個瓯柑,這是我寫的2000年在北京打工的故事,手稿寫于2001年,生活我總是當成故事在過。現在整理出來,發在今日頭條)
我的小睡窩裡,那個衣闆下,狹小的空間裡,隻有阿嬌和我。
阿嬌在啜泣。
阿夏接到了一個電話,是一個女的打電話過來,指明找阿嬌,阿嬌接了,被女的罵成狐狸精,說阿嬌勾 引她的老公,把個阿嬌罵得狗血噴頭的,阿嬌找不到人訴說,跑到我這裡來了,我們在衣闆下,說起了悄悄話。
阿嬌:“在這北京,我是忍着巨大的痛苦和無可奈何的心情一日複一日堅強地過着生活,強打歡笑,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隻能呆望矮矮的衣闆,無法入睡。是的,我有一個令人羨慕的兒子,可是,我身在異鄉,如何能開心呢?為了兒子和自己的前途,我不得不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朋友。男人隻是可以用來揮霍依靠的,不靠着他們一點,我哪能養家糊口呀。”
我心一顫,默不作聲地聽她繼續說。
阿嬌:“我不得不這樣生活,說真的,我也不想跟那些男的在一起玩,我知道他們貪我貌美,我也隻是陪他們玩玩而已,也沒有交出過我的身體,為什麼他們的老婆會這樣的,難道男人沒有紅顔知己嗎?我隻是和他們談心而已。我有家庭的,我也很愛我的老公。我在家幹活,老公從來舍不得讓我做飯,燒菜的,更别提涮鍋洗碗了,我的皮膚才會那麼好的。每當我想起我的兒子,我的心就會痛。每個星期的一次通話都讓我反複回味的。兒子四歲了,他在呼喚我回家。每次都說:媽媽,我好想你呀,好久沒有見你,媽媽,為什麼爸爸媽媽都不在家呢?上班沒有休息的日子嗎?”
我:“好懂事的兒子呀,怎麼舍得離夫别子來京呢?”
阿嬌淚汪汪:“我打電話時,我哭了,哭得無法回答兒子的話,隻能說兒子對不起,媽媽很快會回家的,聽話。最令我難忘的是以前,當我在家做苦工時,晚上回家,身子像在換骨一樣地疼痛,兒子就端來茶什麼的,道:兒子帶給媽媽,你太累了,請喝補品!還輕輕地捶着背和大腿。兒子,我沒有什麼言語,隻有看着兒子那張粉嘟嘟的小臉蛋。一日,我不小心在兒子面前跟人談:光陰似箭,不知不覺半生了,老了,什麼都沒有成功,年幼的兒子居然說:媽媽,你老了,我做好吃的給你,我會用很多獎金來給媽媽用的。”
無聲的淚奪眶而出,人啊人,有這樣的一個兒子,難怪母親拼命掙錢,再累也是甜蜜的。
“前個星期打電話給兒子,兒子不理我了,我真的不想這樣下去的,會不會影響兒子的前途,母子親情會不會遠了。兒子說:媽媽,你坐飛機回家吧?為什麼會如此對我想念呢,是家裡的奶奶對他不好嗎?為什麼叫我坐飛機回家,而不是坐火車呢?兒子,兒子,你真令我心碎呀,媽媽是身不由已呀。我,我是不是很啰嗦?”
我急道:“你沒有啰嗦的,思子心切難免牽挂,奶奶待他很好的,叫你坐飛機回家,那是誰都想自己的媽媽能輕松回家呀。誰家的小孩不想娘呀?”
阿嬌喜歡打扮,由于皮膚白嫩,長發飄飄,加上保養得當,三十歲的女人,看上去比二十歲的小姑娘還有很氣質,還清純。
她說以前在廠裡做服裝的時候,一個老闆看上她了,非得讓她要當他的小情人,她不願意,辭職回老家了,老家是麗水一個偏僻的山裡,據說那山上的石頭是白色的,遵從家人的意見,嫁了一個同村人,那人是她村裡最好看的男人了,條件也算是最好的了,可是家裡的活就是背石頭,在外打工慣了的阿嬌不願意受那個苦,更受不了山窩窩裡那種與世隔絕的環境。就在兒子四歲時獨自出來打工了,跑到溫州時,剛好碰上阿江家要招個勞工去北京,她就過來了。
在北京,阿嬌喜歡打電話,于是常跑到各個小商店裡,打公用電話,慢慢地又重新認識了很多的異性朋友,這不,又一家的老婆打電話來罵架的,阿嬌很委屈,她說:“我隻是跟那些男的聊聊天的,又沒有去破壞他們的家庭,他們也隻是給我買買電話卡呀,買點化妝品,我也沒要他們的錢呀,我知道如果拿錢了,他們肯定會有目的,我也不會讓他們有目的,我們隻是純粹地聊天,談心的。我十四歲就出來打工的,打了那麼多年的工,生活經驗豐富,我和人很聊得來的。”
我看着阿嬌的臉,在小燈光下,阿嬌的臉沒有化妝,但是依舊是吹彈可破,帶着淚珠,水靈靈的,也許用水靈靈這個詞放在三十歲婦女的臉上不恰當,但是她的皮膚真得很嫩,我見猶憐的,賽過阿玲,更是我這種小黑球無法比的。我在心裡歎息:這樣的女人,老公怎麼放心她出來打工呢?
在阿江家做服裝,阿嬌有空就出去玩的,也不帶阿玲,都是獨來獨往的,比較索群離居的,但是阿夏常是接到電話,有男人找阿嬌,阿嬌沒有手機的,她給别人的電話都是阿江的手機号碼,男人找多了,女人也找她,找她的女人,都是罵她的,甚至有次一個女的跑到大院,找到阿江家,将正在睡夢中的阿嬌拉出來,想打她的時候,阿江他們擋住了,阿夏罵那個女的,說:“阿嬌天天做衣服,哪能勾引住你老公,她自己也有老公的,單憑打電話,就捕風捉影的,還跑到這邊來,我都為你同為女人丢人。”
那個女的罵罵咧咧地走了,阿嬌也睡覺去了,這些事情好像都是别人的事情一樣的。倒是阿夏,一個直爽的婦女,對我說:“小黑球,不要将女人想得太簡單,太白癡,你看到的和你想到的是不一樣的,對于阿嬌,我也不能說她什麼,她都跟我一樣年齡的。”我也無語,感覺與阿嬌的距離拉得更遠了。
阿嬌真受委屈的時候,就跑到我這裡,邊哭邊說的,而我隻是一個很好的傾聽者,還有人們稱我是缺個心眼的,是個讓人傾訴的小筒子,其實就是我的故事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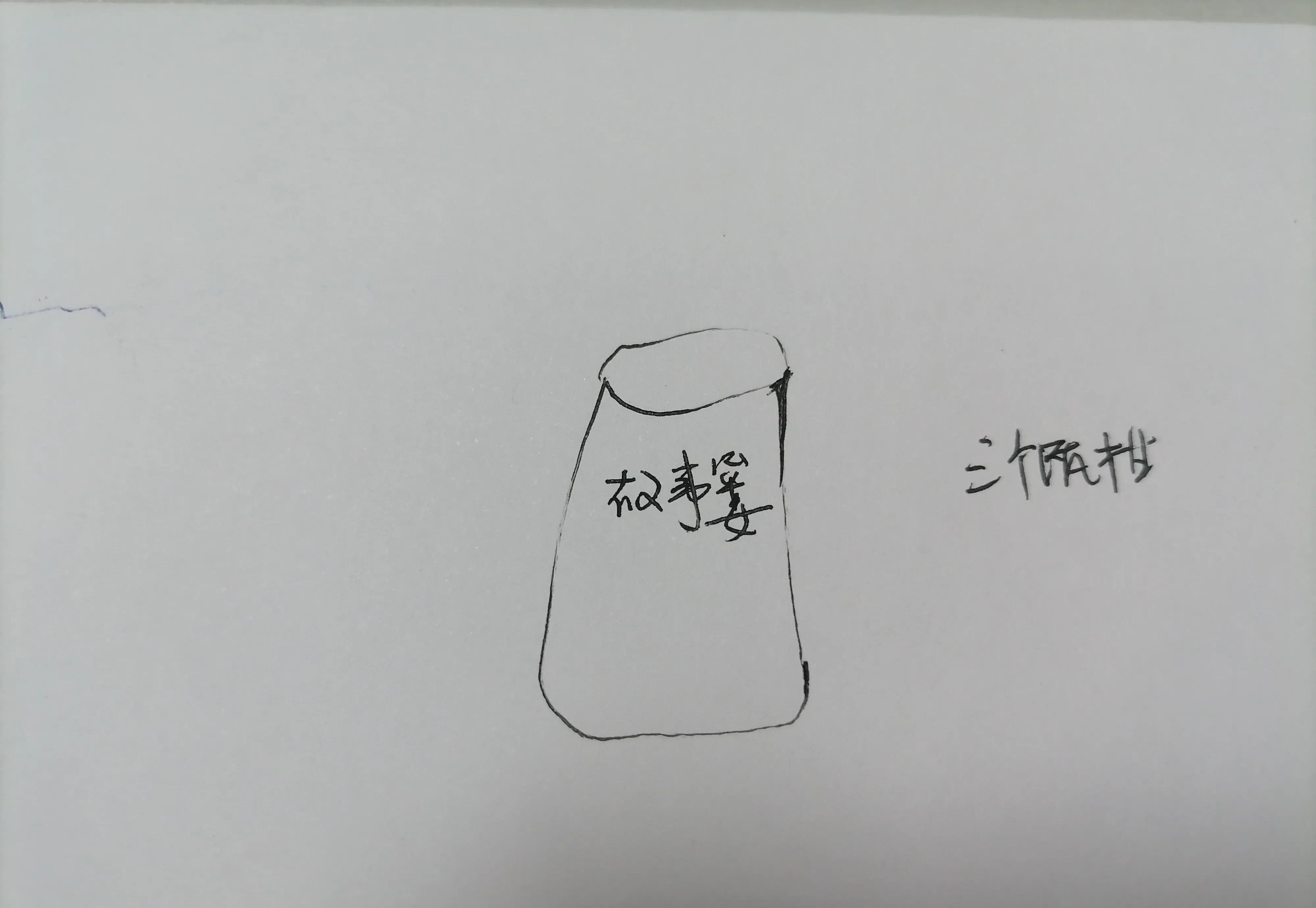
故事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