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曆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中國曆史上曾經有過一個以母系繼嗣制為原則建構起社會組織的母系社會,這是先秦兩漢的大量文獻記載可以證明,也是國内學術界所肯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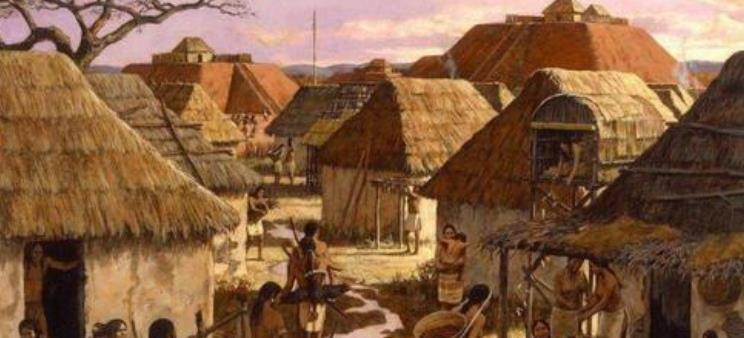
問題在于,學者們在論述母系社會時,往往将母系制與母權等同起來,宣稱在中國母系社會,即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中期,婦女從事采集和原始農業,是農業生産中的主要勞動力,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起着決定性的或主導的作用因而婦女的社會地位高于男子,婦女在社會上不僅享有特殊的尊敬,而且控制着管理氏族事務和經濟生活的權力。簡言之,中國古代母系社會是以母權制為特征的婦女在上統治男子的“母權制社會”。
中國曆史上果真有過一個“母權制時代”嗎?
衆所周知,母權制時代的說法最初是由郭沫若等曆史學家于本世紀30年代提出并經五、六十年代的學者們反複論證而形成的。由于曆史條件的限制,這些學者在研究中國原始社會的過程中,所能依靠的文獻和民族志資料并不多,史前考古的資料更是十分有限。
是以,當時的學者主要還是依據摩爾根的原始社會史模式來重構中國曆史的史前時代的。建國以來科學考古發掘工作所取得的巨大進展,使我們對于中國史前文化和社會的認識日趨深入。
現在看來,前輩學者們依據摩爾根模式建構的中國原始社會史體系并不符合曆史的實際。
對大量新石器文化考古資料與曆史文獻綜合考察的結果顯示,中國古代雖然有過母系制社會,但卻不存在“母權制”,學者們認定中國上古時代有過母權制的主要依據是,在母系社會,婦女是原始農業生産中的主要勞動力,負擔着繁重的生産勞動、在經濟上起着決定性的作用,這是“母權制”盛行的物質基礎。
從現在看到的大量考古資料看,母權制論者對于中國新石器時代原始耕農業生産情況的描述,其實是不正确的。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現已發現的新石器文化遺址達7000多處,經過科學發掘,迄今已經在黃河長江流域發現了一系列早期新石器文化,包括河南的裴李崗文化、河北的磁山文化、甘肅的大地灣文化、江蘇的馬家浜文化和浙江的河姆渡文化等。
這些新石器時代前期文化大多處于由采食經濟向産食經濟過渡階段,使用陶器,經營原始的鋤耕農業,
定居聚落已經相當穩固,恰恰是摩爾根所謂婦女在農業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母權制繁榮階段。
但上述文化遺址的發掘報告卻告訴我們,裴李崗、馬家浜、磁山,大地灣、河姆渡文化時代農業生産中的主要勞動力實際上是男子而不是婦女。
這一點可以從各遺址的墓葬中随葬品的組合上得到證明。
如距今7500多年前的裴李崗文化墓地,經人骨鑒定,凡男性墓皆以石鏟、石斧和石鐮随葬,而女性墓則以石磨盤、磨棒和陶罐随葬。
正如中國農業生産工具發展史所表明的,
石鏟、石斧、石鐮是新石器時代農業生産中的主要生産工具,被運用于從開墾種植到收獲的幾個主要生産環節:石斧為燒荒前砍伐樹木之用,石鏟用于翻地,石鐮則用于收割。
裴令崗文化墓地的男性主人用石斧、石鏟和石鐮作随葬品,說明生前掌握這些工具的男子是當時農業生産中的主要勞動力;而生前為女性所掌握的石磨盤、磨棒和陶罐、陶勺,其中陶罐、陶勺為炊事用具,石磨盤和磨棒則為谷物脫粒工具,可見當時的女性主要從事糧食加工、燒煮食物和撫養孩子等家務勞動。
在長江下遊地區距今約7000年前的馬家浜文化也顯示出與黃河流早期新石器文化相同的兩性分工。
如常州圩墩遺址先後清理出83座馬家浜文化墓葬,其中大多數人骨經鑒定後可以确定其性别,
結果表明,凡有随葬品的墓主、男性墓多随葬石锛、穿孔石斧、石鑿、鹿角器等農業生産工具和骨镞等漁獵工具,而女性墓則多以陶鼎、豆、罐、缽等炊事用具和陶紡輪等紡織工具随葬。
迄今發現的一系列新石器文化遺址,凡人骨架儲存較好并經性别鑒定的,其随葬品的組合方式均表明:
中國早期新石器時代原始鋤耕農業生産中的主要勞動者是男子而不是婦女,男子承擔了從墾荒到收割等農業生産環節中的大部分勞動,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那種認為婦女在生産經濟中起主導作用并由此在政治上統治男子的“母權制”理論,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在以往的一些論著中,持母權制說的學者往往以仰韶文化為例,認為中國早期新石器文化遺址中有一種所謂“女性厚葬”的葬俗,宣稱這種現象集中展現了“以女性為中心”、“婦女在社會上居統治地位”的母權制社會特征。
早期新石器文化中是否存在一種普遍的“女性厚葬”習俗?
對迄今為止發現的一系列新石器前期遺址的考古資料進行全面考察後,我們就會發現:
曆史的真實情況并非如此,所謂中國早期新石器文化中實行對女性厚葬的說法,其實是不确切的。
在早期新石器文化遺址中,分别存在個别女性或男性墓的随葬品多出同遺址其他墓葬的情況。母權制說的學者為證成其說。往往選取其中随葬品較多的女性基為依據,卻避而不談同時同地遺址中也存在個别男性墓随葬品較多的事實。
例如,有學者就舉仰韶文化元君廟基地中有的女性墓随葬數百顆骨珠等随葬品的例子,論證當時社會上婦女的地位高于男子,是以仰韶文化社會就是母權制社會雲雲。
這種以偏概全的方法顯然是不足取的。
實際上,仰韶文化元君廟墓地既存在對個别女性的“厚葬”現象,也存在對個別男子實行“厚葬”的事實。
正如元君廟墓地發掘報告所顯示的,該墓地中随葬品最多的第12号墓地墓主即為男性;此外,該墓地中的第458号墓,墓底築有二層台,台上堆砌幾層礫石、形成石棺,随葬七件陶器,是們韶文化墓地中修築得最為考究的墓穴,而該墓的主人也不是女性而是一老年男子。
在仰韶文化以前的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河南賈湖新石器早期遺址中,也是男性厚葬與女性厚葬并存于同一墓地中。
如果某個遺址中個别女性随葬品較多就可作為某文化女性地位高的标志,對同一文化或同一遺址中個别男性随葬品較多的現象又作何解釋?
這類人物死後,便以其生前使用過的實用器随葬。
是以,某人(無論男性或女性)墓葬中多了幾件陶器裝飾品或生産工具,隻能說明死者生前擁有的日用之物較多,卻不能證明在葬禮中對他(她)有何厚待之處,更不能用以證明男女兩性的社會地位或身份之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所謂中國上古時代有一個母權制社會的觀點,是本世紀30年代的學者從19世紀的西方古典進化學派人類學家那裡照搬過來強加在中國曆史上去的。
100多年來世界各國人類學家對地球上尚存的初民社會進行的科學調查和研究已經證明,巴霍芬、摩爾根等人所謂的“母權制”,即真正意義上的女性統治從來沒有在迄今為止的任何一種社會和文化中發現過。
從曆史文獻、民族志資料和考古發掘報告三方面綜合考察,中國文明的原始社會史個案不僅沒有為所謂的母權制說提供任何使之能夠成立的證據,
相反卻證明了一向被學者們認定是母權至上的母系社會,實際上是一個男性在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宗教等領域均居于統治、主導或支配地位的社會。
在文獻記載中,中國上古、遠古時代叱咤風雲流名後世的英雄人物,如黃帝、炎帝、太昊、伏羲、蚩尤、驩兜、少昊、颛顼、帝喾、帝堯、帝舜、祝融、鲧、禹等等,幾乎都是男性。
史書中記載的母系制社會中的一些著名女性,如殷人的女始祖簡狄、周人的女祖先姜原、秦人的女先祖女修等,在當時社會上所擁有的地位和權力也并非高高上統治男人,而主要在于生兒育女、紡衣織布,從事一些輔助性事務。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于曆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