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來,被稱為“四大奇書”的《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金瓶梅》,曾經盛極一時。清代曹雪芹的《紅樓夢》出,又得以盛行于世。但是正如魯迅所指出的:“時勢屢更,人情日異于昔,久亦稍厭,漸生别流”,于是俠義小說遂得以脫穎而出,别開生面。這類俠義小說,旨在揄揚勇俠,贊美粗豪,但又不背于忠義,是以既受到小民百姓的歡迎,統治者也樂于利用。清代的俠義小說,往往與公案故事連在一起,形成俠義公案小說。這類小說每以曆史上的一名清官為主,一些武藝非凡的俠客為輔,互相敷衍而成。如《三俠五義》中的包拯,《施公案》中的施世綸(小說作施仕倫),《彭公案》中的彭鵬(小說作彭朋),在曆史上都頗有名聲。這些清官要能順利地辦成大事,自然需要一些俠客的幫忙,武藝高強的南俠展昭等人,自然是最好的幫手。魯迅在評《三俠五義》一書時說:“凡此流著作,雖意在叙勇俠之士,遊行村市,安良除暴,為國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為中樞,以總領一切豪俊,其在《三俠五義》曰包拯。”他又說:“凡俠義小說中的英雄,在民間每極粗豪,大有綠林結習,而終必為一大僚隸卒,供使令奔走以為寵榮,此蓋非心悅誠服,樂為臣仆之時不辦也。”這兩段話很有概括性,深刻地揭示出古代的俠客,既有“俠義”的一面,也有“奴性”的一面。同類的俠義公案小說,大抵都離不開這個公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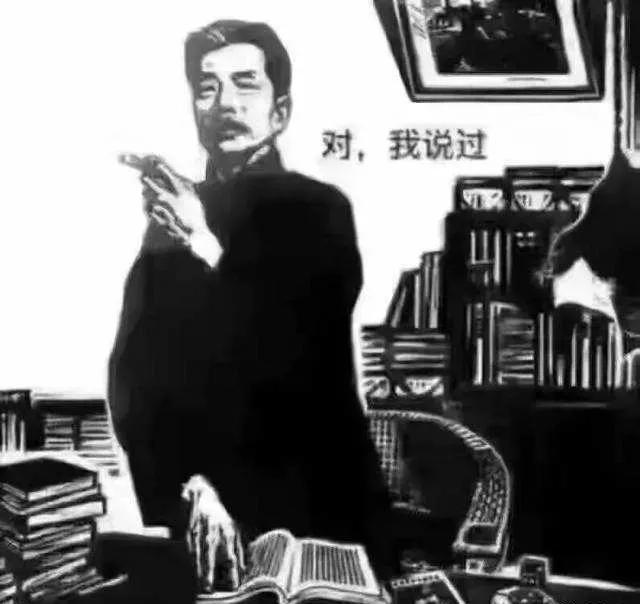
文康的《兒女英雄傳》,又名《金玉緣》《俠女奇緣》。書中寫俠女何玉鳳,出身名門,智勇雙全,因父親被權臣紀獻唐(隐射年羹堯)所害,隻得奉母避居山林,伺機報仇。她變名為十三妹,廣交豪傑,出沒市井之間。偶于途中遇到為救父而奔走的安骥蒙難,毅然拔刀相助,救他脫困,并說合同時被救出的弱女張金鳳與他結婚。其間穿插寫她行俠仗義、懲惡鋤奸的故事,頗為動人。後來紀獻唐被朝廷所誅,十三妹雖未手刃仇人卻父仇已報,而且母又逝去,便欲出家為尼,後終被衆人勸動,嫁了安骥。何玉鳳與張金鳳二人共事一夫,相睦如姊妹,故此書初名《金玉緣》。此書前半部寫十三妹行走江湖的俠女形象頗精彩,下半部寫她回到閨閣中去,助夫奮鬥功名,則淡然寡味,無甚可看。
石玉昆的《三俠五義》,原名《忠烈俠義傳》。書中初寫宋真宗時劉、李二妃俱孕,劉妃争寵,與宮監郭槐施“狸貓換太子”計,陷害李妃;繼寫包拯斷案,昭雪冤情。包拯以忠義剛正的行為,感化豪俠,于是南俠展昭、北俠歐陽春、雙俠丁兆蘭、丁兆慧等“三俠”,以及鑽天鼠盧方、徹地鼠韓彰、穿山鼠徐慶、翻江鼠蔣平、錦毛鼠白玉堂等“五義”,先後投誠受職,人民大安。此書寫三俠、五義鋤強扶弱、誅除奸暴的故事,寫得虎虎有生氣。當時《紅樓夢》等書專講柔情,《西遊記》一派,又專講妖怪,《三俠五義》在柔情與妖怪之外,别樹一幟,專講俠義,使人耳目一新,大受歡迎。魯迅曾稱許道:“《三俠五義》為市井細民寫心,乃似較有《水浒》餘韻。”“至于構設事端,頗傷稚弱,而獨于寫草野豪傑,辄奕奕有神,間或襯以世态,雜以诙諧,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值世間方飽于妖異之說,脂粉之談,而此遂以粗豪脫略見長,于說部中露頭角也。”正因為“寫草野豪傑,辄奕奕有神”,是以俠義公案小說中的豪士俠客,往往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是貴為名臣大吏的清官們所不可企及的。《三俠五義》一書,明确地以“俠義”為題,是對這類義士俠客的極大褒獎。《兒女英雄傳》特标“英雄”二字,也正是對這類義士俠客極盡稱頌之意。
清代大學者俞樾,對《三俠五義》十分贊賞,但認為開篇寫“狸貓換太子”荒誕不經,于是“援據史傳,訂正俗說”,改寫第一回。又因南俠、北俠、雙俠實為四俠,非三俠所能包容,便添加小俠艾虎、黑妖狐智化及小諸葛沈仲元,共為七俠,改書名為《七俠五義》,與初本并行于世,尤盛行于江浙之間。
《三俠五義》寫至白玉堂獨往沖霄樓盜襄陽王之叛黨盟書,誤墜銅網陣而死,群雄共赴襄陽時結束。後有《小五義》及《續小五義》出,序中說二書“皆石玉昆原稿,得之其徒”,與《三俠五義》共為上、中、下三部。《小五義》續寫襄陽王謀反一事,此時群雄已老,後輩繼起,盧方之子盧珍,韓彰之子韓天錦、徐慶之子徐良、白玉堂之侄白芸生,與小俠艾虎結為兄弟,号稱“小五義”。五人行走江湖,誅奸除霸,後來共聚武昌,拟破銅網陣,陣未破而書止。《續小五義》緊承前書,寫衆俠攻破銅網陣,襄陽王出逃。群豪繼續在江湖間行俠仗義,誅鋤盜賊。後來襄陽王被擒,天子論功,群雄受賞,于是全書結束。魯迅在評這兩本續書時說:“雖雲二書皆石玉昆舊本,而較之上部(指《三俠五義》),則中部荒率殊甚入下又稍細,因疑草創或出一人,潤色則由衆手,其伎倆有工拙,故正續遂差異也。”所言甚有道理。
《三俠五義》與《兒女英雄傳》,一為說書人石玉昆底本,一為文康拟說書人口吻所撰,語言生動活潑,文筆通俗流暢,繪聲狀物,極見匠心。故魯迅說:“是俠義小說之在清,正接宋人話本正脈,固平民文學之曆七百餘年而再興者也。”《三俠五義》及其續書,故事情節複雜多變,往往在一個大故事中套着許多小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雲山起伏,綿延千裡,很能吸引讀者的趣味。清代俠義小說的最大貢獻是着意為草野豪傑寫照,塑造出一系列富有個性的人物形象,如白玉堂、歐陽春、展昭、蔣平、智化、艾虎、徐良以及合兒女英雄于一身的十三妹等,都各有風采,自成面目。特别是錦毛鼠白玉堂,武藝高強卻又驕傲好勝,塑造得最為成功。
清代俠義小說因為着意塑造草野豪傑,是以在描寫武俠打鬥時十分細膩精彩,具有很強的吸引力,比宋人話本和明人小說,大大地進了一步。如《兒女英雄傳》中的十三妹,在悅來店輕舒玉臂搬動二百多斤重的石頭碌碡,在能仁寺大展神威掃蕩衆惡僧,就寫得十分生動趣緻。《三俠五義》中這類描寫更多,如白玉堂在開封府夜襲展昭一段,就寫得極為出色:
……隻聽啪的一聲,又是一物打在槅扇上。展爺這才把槅扇一開,随着勁一伏身竄将出去,隻覺得迎面一股寒風,嗖的就是一刀。展爺将劍扁着往上一迎,随招随架。用目在星光之下仔細觀瞧,見來人穿着青色的夜行衣靠,腳步伶俐,依稀是前在苗家集見的那人。
二人也不言語,惟聽刀劍之聲,叮當亂響。展爺不過招架,并不還手。見他刀刀逼緊,門路精奇,南俠暗暗喝彩。又想道:“這朋友好不知進退。我讓着你,不肯傷你,又何必趕盡殺絕?難道我還怕你不成?”暗想:“也叫他知道知道。”便把劍一橫,等刀臨近,用個“鶴唳長空”勢,用力往上一削,隻聽噌的一聲,那人的刀已分為兩段,不敢進步。隻見他将身一縱已上了牆頭,展爺一躍身也跟上去;那人卻上了耳房,展爺又躍身而上;及至到了耳房,那人卻上了大堂的房上;展爺趕至大堂房上,那人一伏身越過脊去。展爺不敢緊迫,恐有暗器,卻退了幾步。從這邊房脊剛要越過,瞥見眼前一道紅光,忙說“不好”,把頭一低,剛躲過面門,卻把頭巾打落。那物落在房上,咕噜噜滾将下去——又知是個石子。
這段兩雄相鬥,寫得具體細膩,精彩動人:有刀劍相争,有暗器襲擊,有招式比鬥,有輕功相較,真是起伏跌宕,搖曳多姿,為着意寫江湖俠客與綠林豪傑比武争雄的長篇武俠小說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由于俠義小說的故事情節曲折離奇,人物性格粗豪可愛,是以赢得衆多的讀者。此類俠義小說,當時大量出現,除上面提到的幾部外,還有《七劍十三俠》《七劍十八義》《英雄大八義》《英雄小八義》《永慶升平》《聖朝鼎盛萬年青》和《劉公案》《李公案》等。這些小說,大都離不開魯迅所說的“以一名巨大吏為中樞,以總領一切豪俊”“安良除暴,為國立功”這個公式,宣揚所謂“善人必獲福報,惡人總有禍臨,邪者定遭兇殃,正者終逢吉庇,報應分明,昭彰不爽”(《三俠五義》及《永慶升平》序)的封建主義思想。由于文字表達與人物塑造都未夠成功,是以成就和影響就遠不如《三俠五義》巨大。
在俠義小說大量産生的清代,還出了一本與《水浒傳》唱對台戲的《蕩寇志》。此書又名《結水浒傳》,内寫陳希真父女武藝高強,将梁山一百〇八名好漢誅擒淨盡的故事。作者俞萬春站在維護統治者的立場上,把宋江等人描寫為不忠不義的寇盜,表現出他對農民起義的極端仇恨。但梁山英雄的故事已經深入人心,他企圖用這本書來抵消《水浒傳》在人民群衆中的影響,始終收不到預期的效果。在清代,另有一部《濟公傳》,寫滑稽多智的濟公和尚扶危濟困、懲惡鋤奸、嘲弄官府豪門的故事,很受群眾的歡迎。濟公不懂武藝,但法力無邊,是一個遊戲人間的怪傑。在新、舊派武俠小說中,是可以時時看到濟公這類滑稽風趣的奇俠的。《濟公傳》完全可以列入荒誕浪漫型的武俠小說之中。濟公這個怪傑形象,在中國小說史中是很有特殊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