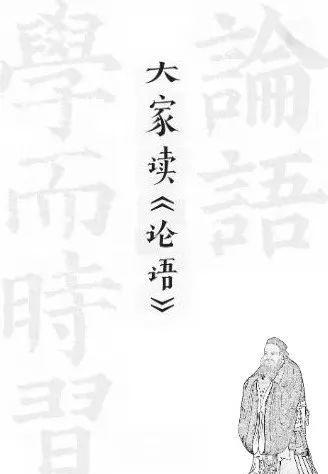
子禽問于子貢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譯文
陳亢問子貢說:“先生到了這些國家,總是能參與讨論重大政事,這種資格是他向國君請求來的嗎?還是國君主動給他的呢?”子貢說:“先生是通過一種待人溫和、善良、恭順,并且嚴于律己、把好處讓給他人的君子行為而獲得這一資格的。先生求得這種資格的方式,就其性質而言,也許和别人求得的方式不一樣吧?”
解讀
孔子在魯國當過司寇,代理相事,由于不滿國君和主政者的表現,憤然出走。他周遊列國的直接目的是求仕,求仕的主要目的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到過許多諸侯國,雖然始終未能得仕,卻也不是一無所獲。所到之處都能得到一個“聞其政”的資格,就是充當顧問或參議的角色。有了這個資格,他的政見可以得到表達,也算是部分地實作目的了。
當一個國家的政治高參,孔子是不滿足的,但在一般人眼裡,這個位置也是許多人拼命想得到的,會被視為搖錢樹。任何官位,都會有人不擇手段地去“求得”它。
名位利益,如果是人家“與”的,就比較體面,如果是自己“求”的,就會讓人懷疑有不體面的因素在裡面。“求之與?抑與之與?”如果了解成“這個名位是活動來的?還是正常任命的?”也不是不可以,這是對孔子“聞其政”的途徑的正當性提出了質疑。子貢當然能感受到這個問題的冰冷無情,但他似乎也舉不出孔子“聞其政”是人家主動“與”之的事實,隻好承認孔子确實是“求”來的,但不可以了解為他人的那種下作的“求”法。
從道理上講,獲得名位的資本是品行和才能。但如果說具備了相應的品行和才能,就幹等着人家來送委任狀,這恐怕是在等着天上掉餡兒餅。現實的情況往往是“餡兒餅”在那裡懸着,人們都在打破頭地争搶,競争會很殘酷而龌龊。孔子對這點俗理當然懂得,是以他到各諸侯國謀差事,自然也得去“求”。他在衛國時不得已去見衛靈公夫人南子,想到楚國去,就“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禮記·檀弓上》),這都是屈尊“求”人的顯證。
同樣是在“求”,其手段卻有文野之分。孔子是用“德”來開路,主動展示溫、良、恭、儉、讓的君子風度,這是他屢試不爽的法寶。
美德是人生鬥争的一種武器,在攻心戰中頗具突破功能,對競争對手也頗具殺傷力。說君子永遠鬥不過小人,那是憤激之言辭。如果其他條件勢均力敵,缺德者往往都會被有德者打敗。
以孔子的實力和影響而言,統治者能把他留住,對自己是很光彩的。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把雙刃劍,用他會有麻煩,是以就給他個“聞其政”的閑差,既能把他留住,也能防止他鬧出亂子,反正他也沒有更好的地方跳槽。孔子當然知道自己的處境,是以他在統治者面前表現出溫、良、恭、儉、讓的謙遜态度,盡量隐藏起鋒芒,這是一種以守為攻的政策。這樣可以打消統治者對他的疑慮,進而得到一個還算不錯的安身之所,這是個雙赢的處理。憑着自己的巨大影響和馴順不争的君子姿态,孔子才能屢“求”屢應。他的這種“求”法,比起其他人的許多下作表現,當然是既體面又高明的。
▼點選名片 标關注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