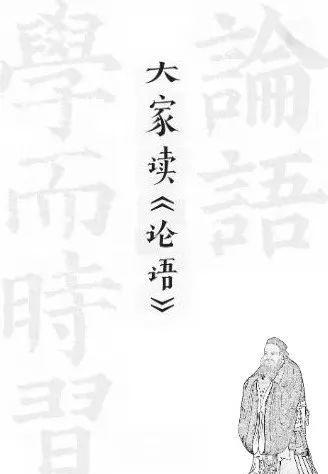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译文
陈亢问子贡说:“先生到了这些国家,总是能参与讨论重大政事,这种资格是他向国君请求来的吗?还是国君主动给他的呢?”子贡说:“先生是通过一种待人温和、善良、恭顺,并且严于律己、把好处让给他人的君子行为而获得这一资格的。先生求得这种资格的方式,就其性质而言,也许和别人求得的方式不一样吧?”
解读
孔子在鲁国当过司寇,代理相事,由于不满国君和主政者的表现,愤然出走。他周游列国的直接目的是求仕,求仕的主要目的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到过许多诸侯国,虽然始终未能得仕,却也不是一无所获。所到之处都能得到一个“闻其政”的资格,就是充当顾问或参议的角色。有了这个资格,他的政见可以得到表达,也算是部分地实现目的了。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高参,孔子是不满足的,但在一般人眼里,这个位置也是许多人拼命想得到的,会被视为摇钱树。任何官位,都会有人不择手段地去“求得”它。
名位利益,如果是人家“与”的,就比较体面,如果是自己“求”的,就会让人怀疑有不体面的因素在里面。“求之与?抑与之与?”如果理解成“这个名位是活动来的?还是正常任命的?”也不是不可以,这是对孔子“闻其政”的途径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子贡当然能感受到这个问题的冰冷无情,但他似乎也举不出孔子“闻其政”是人家主动“与”之的事实,只好承认孔子确实是“求”来的,但不可以理解为他人的那种下作的“求”法。
从道理上讲,获得名位的资本是品行和才能。但如果说具备了相应的品行和才能,就干等着人家来送委任状,这恐怕是在等着天上掉馅儿饼。现实的情况往往是“馅儿饼”在那里悬着,人们都在打破头地争抢,竞争会很残酷而龌龊。孔子对这点俗理当然懂得,所以他到各诸侯国谋差事,自然也得去“求”。他在卫国时不得已去见卫灵公夫人南子,想到楚国去,就“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礼记·檀弓上》),这都是屈尊“求”人的显证。
同样是在“求”,其手段却有文野之分。孔子是用“德”来开路,主动展示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这是他屡试不爽的法宝。
美德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在攻心战中颇具突破功能,对竞争对手也颇具杀伤力。说君子永远斗不过小人,那是愤激之言辞。如果其他条件势均力敌,缺德者往往都会被有德者打败。
以孔子的实力和影响而言,统治者能把他留住,对自己是很光彩的。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把双刃剑,用他会有麻烦,所以就给他个“闻其政”的闲差,既能把他留住,也能防止他闹出乱子,反正他也没有更好的地方跳槽。孔子当然知道自己的处境,所以他在统治者面前表现出温、良、恭、俭、让的谦逊态度,尽量隐藏起锋芒,这是一种以守为攻的策略。这样可以打消统治者对他的疑虑,从而得到一个还算不错的安身之所,这是个双赢的处理。凭着自己的巨大影响和驯顺不争的君子姿态,孔子才能屡“求”屡应。他的这种“求”法,比起其他人的许多下作表现,当然是既体面又高明的。
▼点击名片 标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