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昆明是老昆明人回不去的執念,而每個老昆明人卻能在他的畫中找到自己的歸屬。藝術家蔣淩在一次為父親繪制學術著作插圖的機緣巧合中開啟了老昆明景象的繪畫之旅,那些不經意的過往、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人、走過了無數遍的老街、幽暗的行道樹……雖然經過長久歲月的洗滌,依然不會輕易忘卻的事物與景緻愈發曆久彌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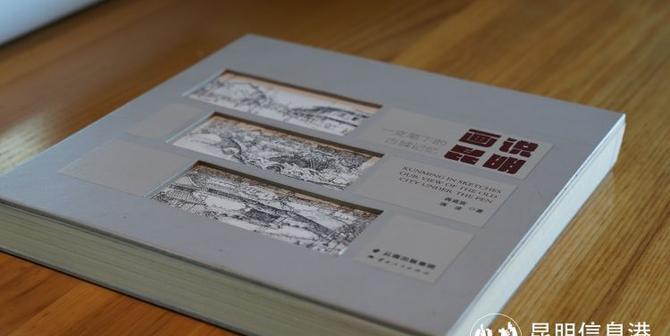
《畫說昆明》畫冊。實習記者楊骞/攝
藝術家蔣淩用“畫”說昆明,400多幅“老昆明”,每一幅都有故事,每一幅都是歲月的痕迹。接下來,他還要用“畫”說雲南,把雲南的大好河山與少數民族的獨特色彩收藏到自己的畫裡,分享給更多的人。
蔣淩在介紹自己的畫作。實習記者楊骞/攝
父親伏案工作的背影 成了蔣淩堅持繪畫的動力
蔣淩出生于七十年代初,在舊城中心區南屏街旁的高山鋪長大,在他的記憶深處永遠都有着對老昆明抹不去的情感。“高山鋪”對于老昆明人來說,實在是太熟悉了,那是隐藏在繁華的南屏街後的一條毫不起眼的小街,準确地說就是一條小巷。
“我的奶奶每天都要吃晌午,這也是很多老昆明人的習慣,是以每天下午,奶奶都會讓我去買包子,或是燒餌塊、小鍋米線、涼卷粉、豌豆粉、米糕等。”蔣淩說,自己當時穿行在高山鋪的裡裡外外,也正是有從小生活在高山鋪的經曆造就了自己對藝術的獨特感受,才會對老昆明有着抹不去的情感。
蔣淩《88年北京路》55cmx37cm鋼筆淡彩2021
蔣淩的繪畫曆程經曆了國畫、油畫和鋼筆畫三個階段。國小時,蔣淩喜歡上繪畫,父母也非常支援他的愛好,為他報了國畫班。“當時條件不好,他我隻能在草紙上畫,墨剛沾上就立馬暈開了。”蔣淩說,但自己還是堅持去上課,就這樣從草紙畫到了宣紙。
“我從小印象最深的,就是父親伏案工作的背影。”蔣淩說,父親蔣高宸是一位民族建築專家,除了從小支援自己的愛好,對其繪畫創作的影響是深切的、終身的。蔣淩說,小時候一家四口住在一起,不管他幾點醒來,父親都在寫作,那個奮筆疾書的背影是蔣淩一直以來勤勉繪畫的标杆。
蔣淩《90年代北門街》51cmx36cm鋼筆淡彩2021
2015年,蔣淩着手“畫”說昆明這批畫作時,他的父親已是八十高齡,卻還在編寫即将要交給出版社的書稿,同時還有着好幾本書的創作架構和寫作計劃。“每次與我的父親交流,于我都是一種莫大的鼓勵。”蔣淩說,直到現在,他的父親依舊堅持每天寫作。
蔣淩《碧雞坊》55cmX32cm 鋼筆淡彩2020
蔣淩17歲考入雲南藝術學院,學習環境藝術專業的他畢業後一直從事人居環境設計行業,同時還身兼數職,擔任中國民族建築研究會理事,雲南省美術家協會會員,雲南省油畫協會會員,昆明美術家協會會員,雲室協設計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副會長,文達畫廊董事長,DAS大森設計機構執行董事等職務,但是他依舊利用碎片化的時間堅持繪畫創作。“能夠整日畫畫的周末,于我而言已是最好的休息。”結束一天的工作後,回家挑燈夜戰伏案創作,蔣淩樂此不疲。
蔣淩《崇仁街》55cmx37cm鋼筆淡彩2021
以畫筆記錄彼時昆明 開啟繪畫創作新階段
“老昆明系列的繪制之初是為了完成父親的心願,但是從第一張插圖開始便一發而不可止,5年下來累計了400多幅以老昆明為主題的鋼筆畫,描繪的是自上世紀30年代至今在時代中變化的昆明城,表達的是幾代人對老昆明生活、對似水流逝的古樸自然之追憶。”蔣淩是在一次為父親繪制學術著作插圖的機緣巧合中開啟了老昆明景象的繪畫之旅。
蔣淩《大觀河》 55cmX29.5cm 鋼筆淡彩2020
2015 年以來,蔣淩創作的400多幅老昆明系列硬筆作品,幾乎是利用他業餘時間完成的。“每一幅鋼筆畫的完成需要三到五個小時,其間的難度在于既要準确地還原建築、街巷,也要恰當地藝術誇張。在梳理昆明古城曆史形态和建築語言的同時,又讓畫面保持松動和美感,要在似像非像間找到一種平衡。”蔣淩在不斷的創作中嘗試着把速寫、連環畫和素描的繪畫技法混合起來,逐漸找到了自己的方法。
蔣淩《大觀街》55cmx37cm鋼筆淡彩2021
一支簽字筆,一張水彩紙,偶爾用水彩着色。去融入一種情緒,盡可能把自己帶回那個時代,從開始到結束幾乎一氣呵成,所有畫面細節在畫的過程中會一并處理,完成後不再做任何的調整。
在創作風格上,蔣淩注重用筆軌迹和手感,其畫面充滿了細碎的點與線,湊近了看,會迷失在充盈的細節之中而尋不見任何現實的形體,像是面對純抽象的形式語言。畫面絕不強調單個建築或形象,而始終着力掌控着整體的空間關系,讓點、線、面如網般攤開,沿着整體的空間關系增長。
蔣淩《滇池草海》54cmX31.5cm 鋼筆淡彩2020
蔣淩創作這批畫時隻有少部分是寫生,因為描繪的大多是昆明的舊光景,是以大量參考了老昆明的曆史圖像,例如莫裡循(1820–1920)、方蘇雅、美國飛虎隊員威廉·迪柏等在昆明拍的第一批彩色玻璃反轉片,以及一些不确定出處的圖檔。當他畫到100張左右時,身邊友人都主動發去各自手頭的曆史資料供他參考。
年複一年,在蔣淩的畫筆下,昆明的老街、老巷、老屋、老樹成了他捕捉記憶的載體,青雲街、天君殿巷、鳳翥街、柿花橋、地台寺……記憶中的老昆明躍然紙上。
蔣淩《東寺街》55cmx37cm鋼筆淡彩2021
用“畫”說雲南 讓更多的人看見雲南的美
繼“畫”說昆明之後,蔣淩又有新方向。他要繼續用手中的畫筆描繪美麗的雲嶺大地,籌備“畫”說雲南畫展,計劃創作畫作2000幅,目前他已創作以雲南為主題的畫作400多幅。
蔣淩《金馬坊》 54.5cmx32.5cm鋼筆淡彩2020
“繪畫和設計是相輔相成的,藝術應該與城市發展結合起來。”在一次古村落考察途中,蔣淩發出了這樣的感歎。在祿勸縣湯郎鄉備者新村,居民已全部搬遷出村,留下的老民居都是土掌房,破損比較嚴重,蔣淩就用畫筆将之畫了下來。他認為,随着很多古城、古村落的拆遷,能及時地用畫筆将它們記錄下來,能很大限度地反映以前的曆史、人居環境、傳統建築、文化的變遷,這對以後城市的發展、更新能積累更多的經驗。
蔣淩《四十年代龍門村 》 57cmX30.5cm 鋼筆淡彩2020
“雲南的文化是多元的、多樣的,民居的多樣性成就了雲南豐富多樣的建築特色,多民族的特色也展示了雲南的五彩絢麗。”蔣淩說,藝術也應該是親民的,正向的審美,隻要喜歡就足夠了,建築、美術、文化結合在一起可以創造出一種新的藝術表現形式。而雲南是畫不完的,自己能做的就是多去寫生,盡量多畫一點,讓更多的人看見雲南的美,把雲南的文化引領出去。(昆明資訊港 記者俞逍 實習記者楊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