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活動
關注“大家小書”并轉發本條推文到朋友圈,截圖發給背景。小編将從中選出5位幸運讀者,贈送《康德倫理學:解讀、研究與啟示》1本,1月9日(周日)公布中獎名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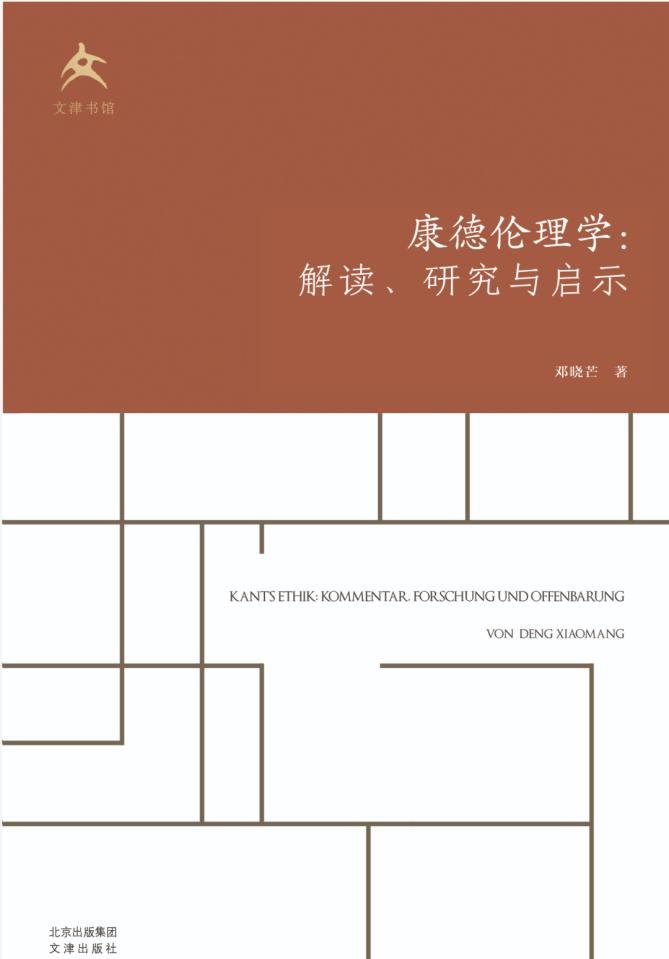
鄧曉芒《康德倫理學:解讀、研究與啟示》
在讀研究所學生以及後來參加工作時,我研讀了康德哲學。其實按照我的興趣來說,我更喜歡黑格爾。但我深知,要真正懂得黑格爾的思想,康德哲學是一項基本功。連康德的純粹理性都沒有搞清楚,談何黑格爾的“辯證理性”?當然,康德哲學這項基本功也不是好對付的,康德和黑格爾都是人類曆史上被公認為最難讀懂的哲學家。
伊曼努爾·康德
然而,促使我不斷地對他們,尤其是最近十幾年來對康德哲學锲而不舍地鑽研的,正是我當年由于不會思維而感受到的那種刻骨銘心的痛苦,以及對周圍非理性社會環境的那種反叛精神。我知道,這種反叛光靠說怪話是不行的,它不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而是成人的一種深思熟慮,是對理性思維的一種熟練掌握和恰當運用。是以它是一種反思,一種徹底的清理和颠覆,和一種重建。
黑格爾
本着這樣一種精神,我在讀康德的書時内心常常有一種感慨,覺得這正是我們民族所迫切需要的。當然不是指康德所提出的具體問題和他所做出的解答,而是指他的思維方法和表達方式。我力圖在研究他的過程中,把他這一套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學到手,然後用來影響國人。康德哲學的普遍意義就在于,他交給每個人一件鋒利無比的思想武器,讓他們學會開展純粹理性的批判,就是對任何哪怕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都采取批判的眼光,不盲從,而是要問一個為什麼,問一個何以可能。
是以,康德哲學對于中國人來說就具有巨大的啟蒙意義。這種啟蒙意義,首先就表現在對理性的運用上。康德對啟蒙的定義是:“啟蒙就是人們走出由他自己所招緻的不成熟狀态。不成熟狀态就是對于不由别人引導而運用自己的知性無能為力。”“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知性!這就是啟蒙的箴言。”
在這裡,所謂知性大緻相當于理性。但理性在康德那裡不僅僅包括知性,而且還包括超越的勇氣。為什麼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知性?因為知性作為一種被運用的工具性的能力,本身不具備超越自身的能動性,它隻是邏輯理性,而非超越理性。它隻有作為超越理性的利器才能發揮其無堅不摧的作用。超越理性的勇氣首先展現為懷疑精神,即像笛卡爾那樣,對一切既定的規範原則加以摧毀。這就是批判精神。
笛卡爾
笛卡爾是西方近代第一個勇者,康德的批判哲學更是展現了大智大勇。而這種勇氣最終歸結到人類本源的自由精神,表現在認知上和行動上,就是每個人都願意相信由自己親證的道理,都願意做自己自願的事情。一切由他人或者環境、曆史、傳統給他預設的樊籠都是不能長期忍受的,都勢必要加以突破。
那麼,有了這種勇氣,如何做呢?如何運用自己的知性呢?其實每個人隻要是成人,都已經具備自己的知性,也會懂得如何去做。但這裡做一點歸納也不是沒有必要的,可以使我們更加自覺。我認為,一般知性的運用有三個要件,第一是良好的記憶力,第二是敏銳的計算能力,第三是綜觀能力。
什麼是綜觀能力?最簡單地說,就是能夠把兩句或數句話合并成一句一針見血的話,同時又保持話語的一貫性和同一性的能力,又叫作概括能力。我們在日常談話中是很随意的,從一個話題轉到另一個話題,這沒有什麼關系;但是如果在學術交流中也限于閑談或漫談,最終你會發現一無所獲,純粹是浪費時間。中國人非常喜歡把學術讨論變成漫談和閑談,把學術文章寫成随筆和散文,而不習慣于咬定一個主題追根到底,覺得那樣太累。
我們看蘇格拉底的對話錄,會驚異于蘇格拉底從頭至尾保持一個論題不走樣,有時候看似跑馬似的走遠了,但一會兒又回到了原來的論題。蘇格拉底的談話對手經常抱怨說,我跟不上你的思路了,說明這樣的交談是很累人的。但人們為什麼還是愛讀,正是因為它使人能夠有所收獲,即使沒有得出最終的結論,也能夠把前面所讨論的内容做一個綜觀,說明我們的讨論已經達到了哪個層次。
蘇格拉底
康德的思維方式就是這種嚴格邏輯方式發揮到極緻的産物。由于心中有堅強的邏輯支撐,他不怕走得更遠,這往往使那些缺乏邏輯訓練的人跟不上他的步伐,丢失了邏輯線索。但正因為如此,康德的著作在今天就是中國讀者最好的思維訓練營。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這種綜觀能力追溯到自我意識的本源的統覺能力,它實際上表達了人在認識中的主觀能動性。人決不是被動地接受外界給予的認識材料,而是主動地綜合這些材料以形成有規律的知識,這種主動性展現的是西方自古希臘以來所形成的一種超越理性的精神,即努斯精神。
這種精神在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中至少是很稀少的,中國人了解的超越精神是一種什麼也不幹的清高,一種沒有責任、置身事外的散淡,而不是努力進行高層次的精神創造。康德的努斯精神則一方面展現在人為自然立法的主體能動性上,另一方面也展現在人為自己立法的道德自律上。
這就回到了我開頭講的,為什麼康德說要有勇氣?要有勇氣已經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且最終是一個道德問題、自由意志問題。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知性,幹什麼呢?做一個自由人,進行道德自律。而這就是啟蒙的真義。通常認為啟蒙理性就是專門着眼于科學技術,是唯智主義的,而它的負面就是敗壞淳樸的道德。其實,康德的啟蒙理性恰好是要重建道德,他是自亞裡士多德以來最偉大的道德哲學家。他的偉大之處,就在于第一次把道德從一種天經地義的教條、風俗習慣或信仰變成了自由意志的法則,使得啟蒙的道德高于任何以往的道德。
我們中國人曆來認為,中國文化的道德水準舉世無匹。然而,儒家道德基本上是一種前啟蒙的道德,它不知自由意志為何物,而是訴之于天經地義的天理天道。它也講意志的選擇,但前提是選擇的标準已經預定了,這标準強加于每個人,就看你接受不接受。接受了你就是君子,不接受就定為小人。這是不自由的選擇。
反之,康德的道德本身就是自由意志自律的産物,人們并沒有一個先定的道德善惡标準,這标準還有待于人的自由意志去建立。自由意志如何去建立?也不是從外部選擇一個标準,而是從自身的邏輯一貫性中形成标準。自由意志不受任何外在标準的束縛,而隻受它自己的束縛,即在時間中保持一貫。自由意志必須做到不自相沖突、自我取消,才是真正自由的。
我們設想有一群人,素不相識,也沒有什麼文化,不知道德為何物,也沒有任何天經地義的教條,隻有每個人的自由意志。這樣一群人聚在一起要組成社會,他們隻有憑借對他人的自由意志的認同,去尋求如何能夠使各人的自由意志延續的有效法則。在不斷磨合中他們終于會認識到,隻有這樣做,使你的行動的準則成為一條普遍的法則,才最能保持每個人自由意志的一貫性。于是這對他們來說就會成為一條定言指令,建立在這一原則上的行為就被稱為道德行為。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康德的道德哲學具有了超越文化和宗教的普世的因素。
康德的這一道德革命具有極其震撼的啟蒙意義。原來,道德并不是我們曆來是以為的,似乎就等于一種習慣或風俗,需要人從小被動地去适應和服從。真正的道德正好是人的自由意志所建立起來的;人性并不是天地自然或神的産物,人是人自己造成的。這種道德原理颠覆了東西方數千年的傳統,賦予了獨立自由的人以最高的尊嚴。
我們今天正處于一個道德崩潰的時期,有不少人以為,通過傳回到我們以前所具有的良好的道德風尚,就可以拯救今天的社會沉淪。但這是完全行不通的。因為以往中國幾千年的道德固然也有秩序井然、民風淳樸的時代,但那是有代價的,其代價就是犧牲廣大老百姓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嚴,所有的人都去頂禮膜拜一個至高無上的皇權。
在皇權已經不可能恢複的今天,人民群衆在市場經濟中已經開始有了自由意志的自覺。在這種曆史條件下,要想恢複過去的道德模式就必須先做兩件不可能的事,一個是給老百姓一個真龍天子,另一個是剝奪老百姓的意志自由,取消市場經濟,重新閉關鎖國。以為光是靠幾個書生在那裡鼓吹,在一個什麼地方辦一所或幾所私塾,把幾句“三字經”放進國小教科書,就能夠改善目前的道德狀況,這種想法實在是迂腐之見。
最後我想說,我并不認為康德哲學就是終極的真理,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法寶。它隻是一種思維訓練工具,可以開拓我們的視野,更新我們的觀念。西方近代不隻是康德,有一大批啟蒙思想家都有這樣的作用。也許康德在這方面比較突出一點,但他也有自身固有的毛病,這是必須也可以加以批評和分析的。但前提是,首先要搞懂他,才能超越他。
本文節選自:康德哲學對中國啟蒙的意義——在《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句讀》首發式上的講話,本文已收入《康德倫理學:解讀、研究與啟示》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