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天涯·文學的自證”
青年作家自薦榜·一
歲末年初,各種文學作品榜單紛紛出爐。評論家和讀者從各自的閱讀角度進行研判,最終産生“他者”眼中的文學作品榜單。這一過程,除了作品本身,作者的“自我身份”或多或少會有缺席的情況,往往也會是以出現了解誤差或過度闡釋,一些作者不太在意的作品被聚焦了,而作者極為看重的作品往往又被忽視了。既是為了糾偏,也是為了給青年作者提供一個對自己的最新作品進行自我闡釋、自我推薦甚至是自我“辯解”的線上平台,《天涯》雜志公衆号即日起推出“文學的自證:青年作家自薦榜”的特别策劃。
此榜面向青年作者,以自我推薦的形式展開,自薦内容為2021年度公開發表、出版的個人最為看重的作品,體裁不限。這一榜單不設排名、沒有評委、無固定名額,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是一個流動且沒有終點的榜單,全由青年寫作者自薦完成。作者的自薦語,從另一個側面,給文學研究者和讀者,提供一個進入文本的角度,避免真正的心血之作被忽略掉。因編輯部視野所限,特邀的青年作家覆寫面肯定是不全的,之後還會廣泛邀請;有意自薦的青年作家,亦可依相應格式,給我們特設郵箱([email protected])發自薦郵件,我們将在彙編後,陸續刊發。
釋出排名不分先後,以收到自薦的時間先後為序。今日推送第一批。
林培源《灰地》
自薦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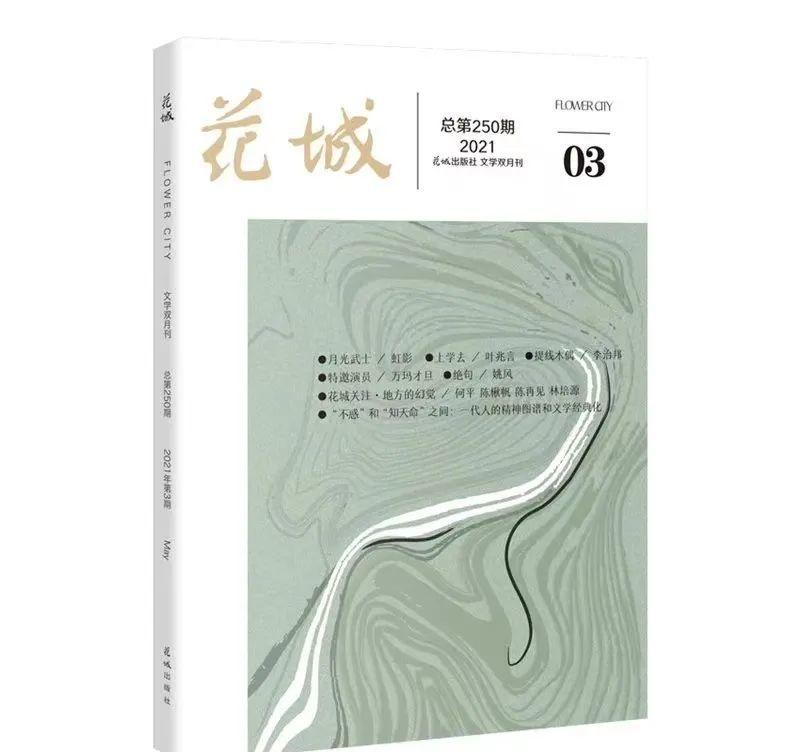
短篇小說|《花城》2021年第3期
和我在“潮汕故事集”(《小鎮生活指南》,2020年)裡寫邊緣人、無名者不同,《灰地》更多地将目光放在了有權勢的鄉鎮老闆這一階層身上。它采用一種克制、穩健的叙述姿态,将潮汕方言和現代漢語并置,并通過細微的事件去呈現平靜生活下的波瀾,以點帶面,具有“社會史”的意味。在短篇的構架裡,這是一種有難度的寫作。《灰地》發表後被《小說月報》及《長江文藝·好小說》轉載,并入選中國小說學會主編《2021中國短篇小說年選》(花城出版社)及《2021短篇小說》(人民文學出版社)兩部文學年選。
作者簡介
林培源,1987年生,廣東澄海人,青年作家、文學博士。曾獲第二屆“《鐘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獎(2020年)、第四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短篇小說佳作獎”(2016年)出版有小說集《小鎮生活指南》(2020)和《神童與錄音機》(2019)等。《小鎮生活指南》獲《亞洲周刊》2020年十大小說獎。
小珂《鋼琴家》
中篇小說|《收獲》2021年第6期
《鋼琴家》的靈感來源于我樓下的鄰居。TA幾年如一日的在我樓下彈鋼琴,我卻始終不知TA的性别、年齡、職業。這種感覺很魔幻,鋼琴聲仿佛繩索,而樓道像是結界,把名為“生活”的東西鎖在這裡,而因為俗世的空氣流不進這裡來,是以給人以永恒的錯覺——我寫這部小說,其實并不是為了寫生活的艱難與打勞工的困境,而是為了表述一種比較抽象的概念,說是“圈套”也好,說是“循環”也罷,總之是一種無法準确定義的、隻能感受的形似“圈套”“繩索”的概念。聲音本來就有魔幻的屬性,因為當聲音出現時,也就意味着它脫離本體了,理所當然多了牽引、誘惑、迷亂的功能。在《鋼琴家》中,正是鋼琴聲讓我所想要表達的、生活之下的抽象概念顯形,超現實的結尾其實是一種答案。
小珂,1988年生于北京。小說散見于《收獲》《十月》《天涯》《青年文學》等,有作品入選多個選本和排行榜。曾獲“紫金 人民文學之星”文學獎。
成向陽《給白鶴留一間房子》
短篇小說|《野草》2021年第3期
這是一篇家庭生活小說,寫的是一個對生活提心吊膽的成年男人在孩子的一次骨折事件中的反應與感受。當然,小說取材于真實事件,我本人即小說中那個神經質的“他”。孩子的骨折事件就像一隻鐵錨,從生活水面下打撈起陳年的不安往事,并激化了夫妻之間的對立。然而,生活始終會在對不安的艱難消化中繼續緩緩向前,而“白鶴”就是這種“消化與寬容”的象征。給白鶴留一間房子,就是給家庭生活一點寬容向前的餘地與希望。為此,我從不同次元對碎片式的家庭生活作了審視與描摹,試圖在意象化呈現中突出強調艱難處境裡人物思維的變化,進而建構一種對“絕對安全”的追求。
成向陽,1979年生,山西澤州人,中國作協會員,山西省文學院簽約作家,魯迅文學院第33屆青年作家高研班學員。作品散見《詩刊》《天涯》《散文》《青年文學》《青年作家》《雨花》《山西文學》等,部分作品被《中華文學選刊》《散文選刊》轉載,入選各種年度選本。著有散文集《曆史圈:我是達人》《青春詩經》《夜夜神》等。
趙俊《天台種植園》
詩集|長江文藝出版社2021年9月
《天台植物園》是我開始創作詩歌以來出版的第二部詩集,大部分作品已在各刊物上發表。詩集精選了我自2015年到2021年創作的詩歌100餘首。共分三輯,第一輯《酬唱》是我與摯友之間的真情流露,其中的翻譯家組詩則是作者采訪8位資深譯者之後的所感;第二輯《吟詠》是我描摹遊曆、家鄉、現居地的生活現狀;第三輯《沉思錄》則是作者對生活、藝術以及世界的感覺,是我詩學理念的集中展現。
趙俊,1982年4月出生于浙江湖州德清,現居深圳,畢業于浙江傳媒學院。在《詩刊》《花城》《上海文學》《中國作家》《北京文學》《天涯》《星星》《文藝報》《文學報》《新京報》等刊物發表過詩歌、詩歌随筆和詩歌評論。曾出版詩集《莫幹少年,在南方》。
趙依《怎麼讀,為何讀——我們時代的文本細讀》
評論|《大家》2021年第3期,收入作者新書《物色:文學的次元與辨別》,四川人民出版社
喬伊斯執着于描述那些重要瞬間的無盡可能。作為一例叙事爬梳,文章選取《都柏林人》中的最後一篇《死者》進行細讀和分析,以期從閱讀經驗出發,在經驗的對話、校正中來尋找某種确認——作家身處的時代與内心的關系、小說與世界的關系以及作家的内心與小說、讀者的關系。還有,我們想成為怎樣的讀者?我們能成為怎樣的讀者?我們真正擁有什麼?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曆經坎坷,展現在文學文化上也充滿了求新的沖突沖突。喬伊斯《死者》既是世界文學的經典之作,也是當時愛爾蘭複雜景觀的縮影,在百餘年的理論跋涉中有着豐碩的研究成果,在小說的叙事和意義等方面均有建樹,但也對當下的閱讀形成了某種遮蔽,因而探究小說的話語空間及成因,得以對我們時代的讀與寫生發幽微的啟發。
趙 依,四川成都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學士、文學碩士,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有評論、小說作品若幹。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新近出版有評論集《物色——文學的次元與辨別》。
甫躍輝《去大地的路上》
《去大地的路上》這本詩集出版之前,我發表的詩極少,幾乎沒人知道我在寫詩。但實際上,我從2000年初就開始寫詩了,2006年開始寫小說後,詩仍然斷斷續續在寫,至今積攢了很多稿子。當然,這些稿子絕大部分都不成熟,我就自己寫寫,自己看看,算是“潛在寫作”的一種。
這讓我想到,如果自己的整個寫作,就像寫詩這樣,長期處于自己寫寫自己看看的狀态,和發表、出書、獲獎等等都毫無關系,那我還會寫嗎?我想我還是會寫的,就像寫詩這樣,哪怕隻有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兩個讀者,其寫作曆程,也會讓自己的生命變得豐盈。寫出了一首好詩的一天,和無所事事的一天,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去大地的路上》收錄了一百二十六首詩,其中大部分是2019年12月到去年6月寫的,之前的二十來年隻收了二十首。這些詩展現了一個詩歌愛好者在二十多年時間裡,對詩歌這一手藝孜孜不倦的練習,也可從中窺見一個人從少年到青年,再到逐漸走向中年的歲月裡,對自我和世界的認知在不斷深入和開闊。
甫躍輝,1984年生,雲南人,居上海。寫小說,也寫散文、詩歌等。著有長篇小說《刻舟記》《錦上》、小說集《萬重山》等十餘部;2017年至今,在文彙報筆會副刊開設散文專欄“雲邊路”;2000年開始寫詩,參加詩刊社第37屆青春詩會,著有詩集《去大地的路上》。
二湘《一個人的公共汽車》
中篇小說|《青年作家》2021年第10期
《一個人的公共汽車》是我迄今為止寫得最痛苦的一篇小說,我相信這個痛苦的程度肯定會被重新整理,我們剛開始小說創作時那種一瀉千裡的書寫感覺太惬意也太充滿欺騙性。小說有很多留白和懸念,最後的結局也是開放式,給故事鍍上一層金色的薄膜,模糊讀者的視線,是我在做的嘗試。我以往的小說,無論劇情怎麼反轉,故事脈絡總是清晰,結局一般也确定。但這個小說我嘗試留下一個連作者自己都不清楚的問題。我同時嘗試做一些探索,關于死亡,愛,意義和孤獨。這些追問也是我自己的困惑,我把這些困惑傳遞給讀者,期待他們能得到更好的解答。小說最後的呈現總是和作者一開始的期待有差距,而我的期待就是在下一步小說裡縮短這個差距。
二湘,女,畢業于北京大學和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計算機碩士。小說見于《當代》《江南》《芙蓉》《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重返2046》獲華語科幻星雲獎電影創意入圍獎。《白的粉》入圍華語青年作家獎。作品進入中國小說學會小說2018年度小說排行榜。著有小說集《重返2046》和長篇小說《狂流》。
楊碧薇《下南洋》
這本書與我本人的興趣愛好緊密相連。我注意到,在漢語新詩的百年書寫中,“南洋”作為一個地理/政治/文化概念,其身影是模糊的、欠缺的。本書上輯《下南洋》正是以華人下南洋的曆史為原點,涉及到中華文化、區域文明、全球演進以及後現代社會裡人的精神狀況等議題;下輯《去南方》則以中國南方為書寫對象,緻力于在大叙事中突出南方的特質、曆史與價值。對我來說,“南洋”/“南方”不隻是地域辨別,還蘊含着南方本位的文化觀。除此之外,我相信旅遊愛好者也會喜歡這本書——在某種程度上,它隐藏着一張東南亞旅遊地圖。
楊碧薇,雲南昭通人。文學博士,藝術學博士後。學術研究涉及文學、搖滾、民謠、電影、攝影、裝置等領域。出版作品:詩集《坐在對面的愛情》《下南洋》,散文集《華服》,學術批評集《碧漪或南紅:詩與藝術的互闡》。
王單單《花鹿坪手記》
詩集|長江文藝出版社2021年5月
寫作是戴着鐐铐跳舞,主題寫作尤甚。因為“鐐铐”的存在,想象和叙述空間會受到主題轸域的壓迫,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詩人的抒寫自由。但也正是是以,心靈在逼仄的抒寫空間裡奮力伸展的樣子才顯得感人。較之于 “泛”主題寫作,詩集《花鹿坪手記》是一種“狹義”上的主題寫作。這種“狹義”上的主題寫作其寫作行為的生發具有一定程度的“被動性”,它更加行業化,方向性和目的性都較為明顯,這種主題寫作難度較大,它呼喚和挑戰的是一位詩人出類拔萃的寫作技巧、更為敏銳的詩意感覺能力,以及處理主題素材時的詩性縱深力度。
王單單,原名王丹,生于1982年,雲南鎮雄人。出版詩集《山岡詩稿》《春山空》《花鹿坪手記》、随筆集《借人間避雨》。現供職于雲南省作家協會。居昆明。
陳崇正《開門》
短篇小說|《人民文學》2021年第9期
短篇《開門》是我在廣州白雲機場抗疫期間寫的,它從一個小截面來反映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一個醫生的家國情懷。疫情已經持續了兩年時間,造成巨大損失,這無疑是新世紀以來對人類命運走向最大的一次挑戰,幾乎所有人的生活都受到影響。作為作家,完全無視這樣的現實顯然是不對的,而如何表達抗疫中精神向上的部分其實也是難題所在。《開門》限定了時空,通過一次開鎖的小意外呈現三個人物背後的不同故事,在有限的篇幅中表達增加故事的密度。這個短篇是一次直面現實的嘗試,作為一個耽于幻想的小說家,我隻能在此自己表揚自己了。
陳崇正,出生于廣東潮州,著有長篇小說《美人城》,小說集《黑鏡分身術》《半步村叙事》等。曾獲梁斌小說獎、廣東有為文學獎、華語科幻文學大賽銀獎,有作品曾入圍寶珀理想國文學獎、花地文學榜等;現供職于廣州市文藝報刊社。
秦羽墨《逃脫術》
短篇小說|《文學港》2021年第7期
去年我寫了兩個關于逃離的小說。一個寫主人公在家門口水一般消失了,每日目睹妻兒在眼前生活,自己卻裝成乞丐在廣場上乞讨,以旁觀者的姿态遊離在本該身處的生活之外。另一個是寫主人公(一位小公務員)裝聾作啞,五年裡沒跟外人說一句話,偶然被妻子撞破謊言,也就是發在《文學港》雜志上的短篇《逃脫術》。有些寫作可能隻對自己有意義,很少會有人去關注一個并不很重要的刊物上發的不起眼的作者的作品,但我很珍視它,因為它對我很重要。我寫的是關于尋找精神出口的問題。小說是一個封閉的器皿,兩頭不透風,這是也我現在很真實的生活和心理狀态。事實上,關于文學,我一直認為,自己熱愛的并不是寫作,而是自由,試圖謀求與世界相處的其他方式,以怎樣的方式逃離,又以怎樣的方式回歸。這也是我為何鐘愛這個小說的原因。
秦羽墨,原名陳文雙,生于1985年,湖南永州人,現供職于常德市文聯。發表作品若幹,有作品被《散文選刊》《散文·海外版》《中篇小說選刊》轉載,魯迅文學院39屆高研班學員,著有散文集《通鳥語的人》《我在今生》,小說集《逃脫術》,曾獲《創作與評論》雜志年度作品獎、第二屆三毛散文獎等。
鄭在歡《3》
長篇小說|《十月》2021年雙月号第6期
2021算是我寫作十年的豐收季,出版兩部中短篇小說集,發表了長篇,當然這些作品的創作年份都在2021之前。《3》寫于2020,我30歲之際,寫了3個女孩的30年,結構選擇的是3個小标題循環往複。是以,那麼多的3,讓我隻能用這個數字做标題。或許這個标題不友善傳播,但是隻要打開看幾頁,就會知道這個數字有多貼切。3,是穩定的數字,是循環相交的數字,也是生出萬物的數字。30歲,則是一代青年的節點。1990至2020,是經濟飛速發展的30年,三個女孩從農村到城市,被時代驅趕,也追逐時代。她們而立之年的最新下落,或許也是一個新起點。像一條三角形的邊,咬住了另一條邊。
鄭在歡,1990年生于河南駐馬店,長居北京。著有《駐馬店傷心故事集》《今夜通宵殺敵》《團圓總在離散前》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