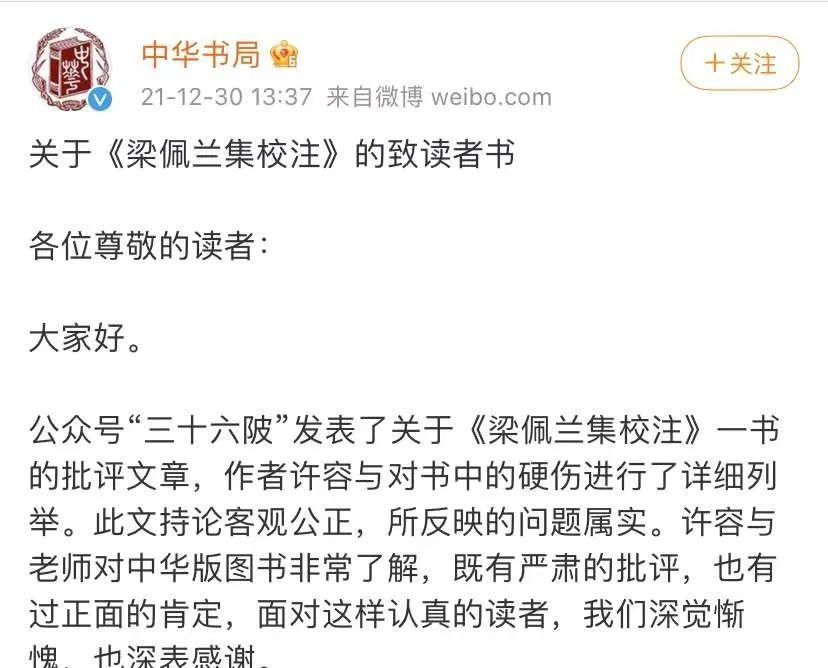
▲2021年12月30日,中華書局發表關于《梁佩蘭集校注》的緻讀者書。圖 /社交媒體平台截圖
2021年12月30日,中華書局通過其微信公衆号發表“緻讀者書”,就其出版的《梁佩蘭集校注》中出現的錯誤向公衆道歉,并提供善後方案。
此前一天,微信公衆号“三十六陂”就《梁佩蘭集校注》一書的品質提出尖銳的批評:一是錯字、漏字、斷句錯誤等硬傷;二是注釋品質嚴重注水,原本明白如話的句子,注出來一堆廢話;三是生搬硬套,胡亂發明。文章還表示,這本書“幹貨不能說沒有,但也約等于沙裡淘金了。”
中華書局的道歉認為,微信公衆号“三十六陂”的批評文章持論客觀公正,所反映的問題屬實。“面對這樣認真的讀者,我們深覺慚愧,也深表感謝。”
但《梁佩蘭集校注》的校注者在其社交媒體發文稱,批評文章充斥大量低俗粗鄙字眼,甚至人身攻擊,措辭行文不是學術讨論的應有态度;批評文章指出的問題有些确是疏忽,有些則是沒有錯誤,還有些可有不同了解(尤其對詩句的了解),而且,即使真的全錯,錯處所占份量很少,其貢獻不應被一筆抹殺;《梁佩蘭集校注》的成果與貢獻獲得多位專家肯定。
應該說,讀者的追問條條見血,書局的道歉句句真誠,而作者的回應也并非完全沒有道理。之是以将這三方的觀點和回應一一列出,是想說明,古籍的整理校注是一項繁難、複雜、需要極大耐心、慎之又慎的工作。
▲中華書局出版的《梁佩蘭集校注》。圖/當當圖書網
為何出現“點校古籍而古籍亡”?
古籍的整理尤其是一些重要文獻的出版,其實是一件亦喜亦憂之事。
一方面,一些高品質的整理作品,使許多不易見到或不便閱讀的古籍以全新的面貌出版問世,對發掘資源、傳承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點校人員學識水準差異等原因,也出現了一些以鹿為馬、魯魚亥豕的作品,嚴重地破壞了古籍的完整性和整理工作的嚴肅性。
魯迅曾批評一些人對古籍“往往自己看不懂,以為錯字,随手亂改”,現在仍時有發生;十多年前,曾有學者指出“學術界作僞之風有愈演愈烈之勢,僞注、僞校點、僞觀點等此伏彼起”,當今也屢見不鮮。“點校古籍而古籍亡”已由憂慮頻頻成為現實。
查閱、征引大量圖書資料,是古籍整理的基本路徑和要求。對于古籍中一些人物和事件,在整理時需要做出诠釋,這就需要查閱大量的曆史典籍和今人研究著述。然而,就微信公衆号“三十六陂”提供的證據來看,《梁佩蘭集校注》并沒有很好地做到這一點,也就是說,連讀者都能做到的工作,校注者并沒有做好。
注釋内容的取舍,是展現古籍整理學術價值的重要一環。太簡,讀者難得要領;太繁,容易變成“資料彙編”,影響對原著的閱讀。正确的做法是提供資料線索,濃縮與此書此處直接相關的内容即可。
而《梁佩蘭集校注》的一些注釋不僅随意,而且于典無證、于文無益,缺乏廣泛查考和認真取舍意識,誠如複旦大學教授傅傑所批評的:“現在很多學者所謂的注,他注出來的地方我也能很友善地查到,我查不到的地方,他也不注,因為他也查不到。”
▲微信公衆号“三十六陂”将《梁佩蘭集校注》(左)與底本(右)進行對比,發現其校注錯誤。圖/微信公衆号“三十六陂”截圖
損害古籍的經典性
和整理工作的嚴肅性
事實上,在當今的圖書市場中,随便翻閱幾本所謂的名著經典,都會發現不同程度的錯訛和品質問題,有的錯誤不僅讓人扼腕歎息,更令人啼笑皆非。有的所謂經典亂标亂點、亂改亂注,甚至把原著中父子身份“互換”,把活人“點校”成死人,将唐宋人“點校”為秦漢人,使人無法卒讀。
另外,一些用簡體字新印的古籍,未做好特殊詞彙的處理,将“仇雠”印成“仇仇”、“餘年”印成“餘年”……這一方面,是對古籍缺少敬畏、對讀者乃至後代不負責任;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古籍的經典性和整理工作的嚴肅性。
古籍整理與出版是一件任務艱巨、細節煩瑣而難以快速制造良好經濟效益的事情。大量的古籍,需要去努力發掘、認真校勘,斟字酌句、反複推敲,如無苦心經營、甘于清貧、能坐冷闆凳的毅力和理想,是不能做好這份工作的。
《梁佩蘭集校注》出現低級錯誤,不論是對出版界還是對社會,都是一次響亮的警鐘。它告訴我們,百年積澱的中華書局尚且都會出錯,遑論其他一般的、非專業古籍出版社的出版物,恐怕問題更多。
古籍整理不能光盯着
國家補貼、政府采購
對于專業的古籍出版社來說,在整理古籍的過程中,需多方考證,仔細遴選,既要選取精校精刻的善本,也要做好校勘和注釋,避免錯漏百出,而不能光盯着國家補貼、政府采購。
原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就曾指出,真正代表古籍整理水準的是經過深度整理的高品質的作品。整體而言,這十餘年來,全國的古籍整理的整體品質水準并沒有明顯提升。有些出版物倉促上市,錯誤很多,有待修訂。
中國是古籍大國與文明古國,典籍存卷,極其豐富。自古迄今,曆代賢達忘食廢寝,皓首窮經,努力把先輩存留下來的文獻舊籍,保護下來、整理出來、傳承下去。
這是一項保留國粹的偉大工程,也是一份綿延不斷的基礎工作,更是國家與民族文化繁榮、文明長遠的一個顯著标志。
是以,古籍整理和出版,是一個尋求品位、傳承精粹的光榮而艱巨的事業。不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更需要整理者、編校者、出版者以十二分的誠敬之心書之寫之,如此方能為當世和子孫後代留下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産。
特約撰稿人 | 趙清源(媒體人)
編輯 | 徐秋穎
實習生 | 韋英姿
校對 |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