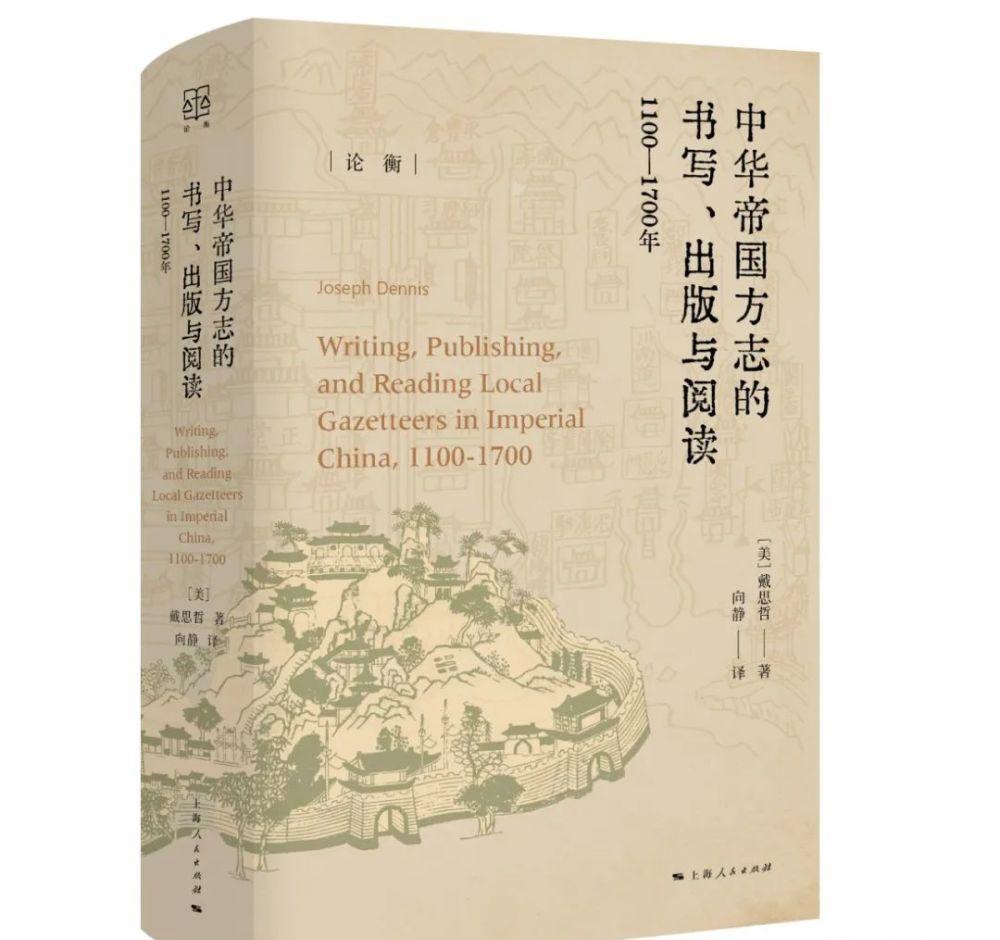
有多達數千部的方志是因為響應君主下達的修志诏令而完成的,比如1418年永樂皇帝的聖旨、1454年景泰皇帝的聖旨。這些方志呈送到朝廷時往往是手抄的副本,其原稿或同時産生的其他手抄副本則會儲存在當地。此外應本省或本府的要求,州縣也會完成一些方志的手稿。
浙江《嚴州府志》的編纂,就是為了響應1454年景泰皇帝的聖旨。該志的一份手抄本呈送到翰林院,另一份儲存在府學中。記載裡以“錄本”“副本”來差別于原始手抄本的“正本”或“底本”。因為嚴州府收到了上級要求編纂方志的指令,是以它很可能将正本存放于衙門中。将手抄本放在當地衙門和儒學裡,這是當時通行的做法。1557年版廣東《翁源縣志》也做了兩份手抄本,一份放在衙門,另一份放在縣學。1434年,宋骥赴任南直隸的徐州,成為州學學正。他要求學生們将當地應1418年聖旨編成的方志拿給他看,但學校裡找不到,最後是在衙門裡找到了這份匆忙編纂的方志的副本。這個例子表明,人們會很自然地以為在儒學裡能夠讀到方志副本,但事實上并非如此。究其原因,是因為地方官在将稿本呈送朝廷之後,常常希望還能借助副本對方志進行增補、刊印,是以,方志手抄本的副本并不總是存放在學校。當然,許多方志最終也沒有刊印,而是很快丢失了。從15世紀末到16世紀,方志編者們經常提到,早年舊版的志書已經杳不可尋。他們當中,有些人甚至從來不知道出現在本書參考書目當中的洪武、永樂時期的舊版方志。
地方上反複地送出志稿,結果是使朝廷收藏了大量的方志。這種收藏的規模可以從藏書的目錄裡窺及。在前文第三章中曾提到,1441年的《文淵閣書目》将方志分為“舊志”和“新志”兩部分,前者列出600部,後者列出568部。文淵閣的藏書曾毀于1449年的一次大火。到了萬曆時期,《内閣藏書目錄》中列舉的方志總數約880部。根據地方行政機關的數量,人們可能覺得朝廷應該有更大規模的方志收藏,但是地方上編纂的方志并不會定期全部呈送到朝廷來,圖書館中的藏書還可能會被某些官員竊取。此外,為了國家修志工程而呈送到朝廷的方志,未必就會儲存在這些藏書閣裡,因為像1418、1454年的國家修志都是由戶部、禮部和翰林院等部門實際主持的。
除了上述的主持部門,至少還有一個中央機構在搜集地方志,那就是行人司。該司的官員被派往全國各地時,也會收集圖書。他們在1602年的藏書目錄中設有“地理類”,其中列舉了270部作品,絕大多數是府州縣志。行人司專門負責向進階政要人物傳達那些非正常的資訊,獲知有關地方的詳細情況對他們來說是有益的。
朝廷藏書中方志的閱聽人,無疑是皇帝和官員。正如第一章中讨論的,正德皇帝想要在去南京的旅途中閱讀方志;景泰皇帝想要在閑暇時閱讀各地方志,而發出了修志的诏令;這都不是為了惠及當地的、普通的讀者。許多明代前期的方志手抄本都有副本收錄在《永樂大典》中,這部類書始編于1403年,完工于1408年,當時僅有手抄本。如牟複禮(Frederick Mote)和朱鴻林(Chu Hung-lam)所言,《永樂大典》之是以僅有手抄本,是由叢書的性質以及它的目标閱聽人決定的,并不是要避免印刷的成本。這項浩大工程的最初啟動,既不是為了文化傳播,也不是為了增進受教育階層的知識水準,而是為了給皇帝及其親信文臣們提供一座可資參考的圖書館。
方志編者們強烈地感覺到,位于宮中的藏書對絕大多數讀者來說都将是難以企及的,這導緻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呈交手抄本方志之後,就迅速付諸刊印。1418年,朱徽刊印了他的家鄉江西新城縣的方志,就是為了在群眾中傳播,因為手抄本呈送之後,“不易為民所見”。1454年,在翰林院釋出了修志規則之後,湖廣行省的荊州知府編纂了一部方志,先是制作了一份手抄本呈送給朝廷,随後又很快在府衙制作雕闆,刊印成冊以擴大讀者群。他希望人們,甚至是遠道而來的人們能夠讀到這部方志,因為在他看來,人們是難以看到朝廷藏書的。1457年版廣東《惠州府志》是在1455年送呈朝廷的手抄本基礎上擴充編輯後的版本。編者們之是以這樣做,也是因為接觸手抄本的人群實在太少。
隻有部分官員可以讀到朝廷收藏的方志,其中多數是翰林院官員或者其他的進階官員。有證據表明,地位較低的官員也有辦法直接或者托人設法讀到這些方志。有些官員是在編纂新版方志時,使用了朝廷儲存的較為稀見的舊志。還有一些官員則需要将方志作為參考書使用,甚至能夠随意翻閱。1493年,來自翰林院的經筵講官李東陽提到:“予讀中秘書,見天下圖志簡帙山積,時取而閱之。”明初内閣首輔楊士奇(1365—1444),受邀寫一篇序言時,曾到館中查閱江西饒州的方志。太子少傅李(1521年緻仕),河南彰德人,他在1519年從朝廷藏書中借出了家鄉在宋元時期的方志,并送到彰德給編修新志的作者們使用。
上述讨論的俱是地位較高的官員,他們可以直接獲得國家藏書中的方志。對級别較低的官員來說,則是另外一種情況。北直隸的易州位于北京南面100公裡,它的知州戴敏提供了這方面的典型事例。當他開始編纂1502年版的方志時,先請一名本地人撰寫草稿,又寫了一封信給兄長,時任兵科給事中的翰林院庶吉士戴銑。他請求兄長幫忙查閱舊志并潤色草稿。戴銑接受請求,讀完草稿後,将其中的條目與朝廷藏書一一比對。等到他修改完畢後,戴敏便到京師,從兄長處取回了志稿。
存留在地方上的手抄本,是供人們在完稿到刊印之間的過渡期内閱讀使用的,既有可能儲存在本地,也有可能流傳到外地。舉例來說,根據1084年版《吳郡圖志》的序言記載,1011年的本地圖經非常簡略,到11世紀70年代時,其中的内容已經過時了。大約在1078年,蘇州知府請朱長文增補舊圖經,他接受了這一請托。當朱長文完成時,原知府已經遷任他處,朱長文便将增補完成的方志存放于家中,沒有公開出版。三年後,應新知府的要求,朱長文潤色了他的志稿,并謄抄了一份置于衙門裡,以備官員參考。此外,他還謄抄了一份置于家中,供他人閱讀。1098年,新到任的官員決定刊印這份手稿。他認為即使衙門存有手抄本,也鮮少有人讀到,是以,1100年時決定在衙門的庫房中制作雕闆。這樣看來,在朱氏志稿完成後約20年裡,它隻是以手抄本的形式供人閱讀的。另一個相似的事例發生在元代。一位曾擔任益都路稅吏,名為于欽(1284—1333)的山東人編纂了一部地方志《齊乘》。他收集資料後完成了手稿,存放在家裡。1333年臨終之際,他交待其子于潛說:“吾或身先朝露,汝其刻之。”于潛當時也是官員,一直到1351年他才完成父親的遺願,出版了此書。據他所說,此前一直忙于公務,難以脫身。從于欽去世到方志刊印的18年間,《齊乘》始終以手稿的形式流傳于世。1339年,名臣蘇天爵在序言中提到,他在揚州第一次讀到《齊乘》,将該書推薦給了山東官員。類似的情況,在宋元明時期并非罕見。
有些零星的記載表明,借閱、手抄也是方志流通的重要途徑。著名學者方孝孺(1357—1402)在給友人的書信中提到,他正在寫一本關于當地曆史人物不為人知的事迹的著作,希望給地方上的群眾樹立榜樣。為此,他回到浙江甯海的老家,去南面80公裡外的台州府學裡借出了當地方志,手抄完畢再歸還原本。另一個事例是四川夔州的知府,他在1511年從一位府學生員處獲得了一部方志的手抄本。1531年,歸有光(1507—1571)在南京參加省試,他從吳中英處借得了南京地區14世紀晚期的舊志。29年後,歸有光讀到了一部元代的南京地方志,他開始思考曆史上的變化,于是又從吳家借閱前志,重讀後寫了一篇後記。在17世紀10到20年代,浙江仁和縣的一名學生家中藏有沈朝宣所編1549年版方志的手抄本,當時知縣借閱之後沒有歸還。1657年,沈虯,他可能是沈朝宣的親戚,從知縣家中借出方志,請一位縣人謄抄後刊印出版了。
選自[美]戴思哲《中華帝國方志的書寫、出版與閱讀:1100—17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