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腔
久違的槍稿顔值及流量擔當楊時旸老師終于又寫稿了(畢竟寫一篇删一篇太傷感情了)。
這一次,時值年終,在我的三催四請之下,他發回了他的年終總結篇。
讓我意外的是,這一次他發起了牢騷——但是,一定會得到你的共鳴。
——槍稿主編 徐元
槍稿老炮兒集結,陸續在農曆新年前推出一系列年終特别策劃稿件
“春晚化”的電影還值得人們走進影院嗎?
文/楊時旸
作者簡介:普通影迷,媒體編輯,純粹寫字,不混圈子 ,某種程度上相信娛樂新聞裡潛藏着人們的潛意識以及一個時代的病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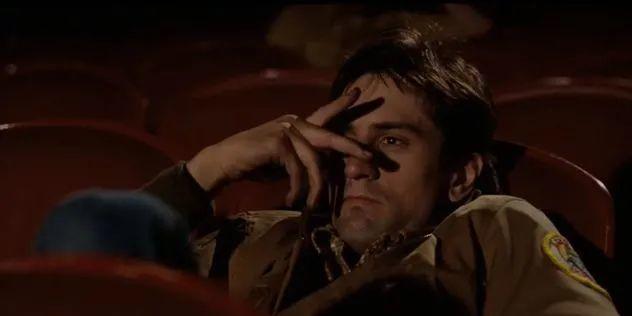
1
不知道是懶惰使然,還是因為疫情攪擾,今年進電影院的欲望極低,次數更低,通常計劃着周末去看某一場電影,到了近前就突然意興闌珊,自己對自己說,做點什麼不好,何必去那折磨自己呢?
截止于2021年12月初,除去工作原因受邀看過的偶爾幾場首映和點映之外,自己買票進影院三次,看了《沙丘》《懸崖之上》和《第十一回》,當然,這是從去年春節檔之後開始計算的,我更習慣于将春節之後當做新一年的開端,不過現在想想,春節檔的那幾部電影,如果不去看也不會有任何遺憾,去看了也沒留下什麼印象。
我現在愈發懷疑,如果一部電影不能給你留下餘音和回味,在這個時代裡,我們是否真的還有必要跋涉到電影院,沉浸于黑暗中,在不能暫停,不能快進,不能回放,不能聊天,不能長時間看手機的情況下,端坐兩個小時甚至更久。
受疫情影響,電影院要承擔随時停業的風險。
更尴尬的是,我們得承認,能從國内影院中看到的片子,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大抵都能夠想見,作為一個資深觀衆,看看主創陣容,看看劇情梗概,連最後的評分都能猜得出,能溢出既定架構的極少,能超越期待的就更罕見。
畢竟,我們都清楚外部環境是怎樣的,那些條條框框就虛虛實實地擺在那裡,别說出圈的,就是老老實實在圈裡的都有可能随時因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無法按時上映,在這樣的前提下,你還能要求創作者們怎樣呢?
誰都會說那句陳詞濫調——戴着鐐铐跳舞,可有時候身上的零碎太沉重,動作大了還有可能碰到周圍隐形的電網,舞蹈動作就注定變形,甚至時間久了,所謂的舞蹈都會變成敷衍地擡擡胳膊擡擡腿,畢竟靠賣藝吃飯,動作總是要做的,但做成什麼樣子可想而知,當然,你也能見到一些振奮的大動作,大開大合,大吼大叫,但無非都是大喇叭吆喝下的集體操,隻是後來又被包裝成自選動作加以售賣罷了,我深深地懷疑這行為是否等同于欺詐。
2
今年,賈科長的紀錄片《一直遊到海水變藍》上映時,我的同僚去采訪,賈科長對我們說了一段話,我很贊同也很感動,他說,“電影有兩個特點是小螢幕無法取代的,一個是放大,電影有人道性,人道精神是由放大來承擔的。比如農民的一雙手,放到十幾米的銀幕上,用放大的方法來對他表示一種尊敬。人類的痛苦、啼哭、母親的哀怨,都是通過放大來實作的。另外一個特點是聚衆,電影有劇場效果,有儀式感,是在黑暗中的集體觀看,也是小螢幕取代不了的。”
賈樟柯在《一直遊到海水變藍》中關注到鄉村和農民。
他說的沒錯,這是藝術家們共通的見解或者說美好願望,作為我這樣的觀衆,多麼希望能看見那種“人道性地放大”啊,但我們現在能夠被呈現在影院中的電影,又有多少内容是值得被“人道性地放大”的呢?我們能夠被放大的是什麼?《你好,李煥英》中賈玲和沈騰的臉嗎?真的還能有人相信那些角色嗎?難道不會看什麼都像《王牌對王牌》嗎?那些被綜藝消耗過度的演員還要在電影裡再攫取一次觀衆的信任,這怎麼可能呢?
放大《刺殺小說家》裡冒藍火的加特林嗎?那電影除了個别的特效可以看看之外,裡面的人物情感值得信任嗎?放大《我和我的……》系列中為了滿足主題先行而制造出的那些人物的眼神和皺紋嗎?放大那幾部戰争片裡的炮火連天嗎?那一切到底屬于創作還是宣傳呢?
現在電影院裡放映的電影放大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能看到的那一切,放不放大,縮不縮小真的無關緊要,連那些東西本身是否存在都無關緊要,不要用票房來反駁,票房這個東西在很多時候不過是因為沒有其他可選,矬子裡拔将軍,人們總是需要用“去電影院”這個事情殺掉一些時間,設定一些社交,或者在春節檔這個獨特的時間點裡,用共同看電影的行為既滿足家人團聚,又可以避免尴尬聊天形成的傷害,坐在一片黑暗裡沉默,笑一笑,就完成了一樁任務,拖過了大半天的進度條。
是以,在一個不是完全充分市場化的情況下,票房說明不了什麼,真的。那不值得炫耀。
3
最近這兩年,能取得最大公約數的電影是什麼?除了那些因為具體紀念時間節點而生産出的主旋律戰争片之外,最火的内容或許是那些《我和我的……》系列,你們有沒有發現,這些電影已經徹底“春晚化”了。
它變成了一種對于一年中需要紀念的人和事,需要圖解的政策,需要宣傳的口号,進行一種影像化的傳達和翻譯,比如新農合醫保的覆寫與完善,比如脫貧攻堅的付出與勝利,這一切就與央視春晚獨幕喜劇的功能與模式一模一樣,而且還不是趙本山那個級别和水準,而是其他那些所謂的獨幕喜劇的水準——先抑後揚,讓人物遇到一些挫折,遭遇一些周圍的不了解,做出啼笑皆非的事,最後給出一個終于互相了解、包容共築的大團圓結局,人們其樂融融體驗幸福,以此來證明政策的正确,決斷的英明。
1999年由黃宏主演的春晚獨幕喜劇《打氣兒》,至今仍為人所诟病。
我不知道這種東西是否能夠叫做電影,或許可以叫做電影吧,因為這樣的作品總會由于衆所周知的原因囊括還不錯的創作班底,做出來的行活也都及格,但這真的能算是電影嗎?算嗎?算了吧。
這一年裡,我們這片大陸以外的大螢幕和小螢幕上有很多作品都非常出圈。南韓電影《摩加迪沙》被認為又是一部可以拿到奧斯卡獎項的作品,而韓劇《鱿魚遊戲》更是火遍全球。這不可否認吧?我們能拍出這樣的東西嗎?《摩加迪沙》不可能,因為它寫的不隻是一場刺激的逃亡,更重要的是韓朝雙方的普通人在面臨生死時,如何處理意識形态的分歧與人心的相通。
而《鱿魚遊戲》呢?那人性裡的黑暗與深淵,我們被允許面對嗎?哦,或許我們不用面對,我們是幸運而獨特的,我們的人性深處也當然隻有光明和坦途。
南韓劇集《鱿魚遊戲》風靡全世界。
日本電影《偶然與想象》和《花束般的戀愛》也算是影迷内部的小小爆款,以我們的标準來看,題材上倒不敏感,可我們能出現這樣簡單卻隽永的東西嗎?我很懷疑拿着這樣的劇本,可能連投資都找不到。即便拿到投資,像《花束般的戀愛》那樣的内容也得被改編成一個甜寵故事,宣發的時候弄不好還會因為撕番引發男女主角的粉絲攻陷對方工作室的官微。
中國香港的大銀幕有《智齒》和《手卷煙》,中國台灣的小螢幕上有《逆局》和《塵沙惑:第三布局》,這其中有的是内地作家作品改編的,有的是内地視訊平台投資的,可我們都沒辦法在正常管道看到,當然,我知道這些作品都有瑕疵,但我們是看電影,不是玩大家來找茬,那些作品和我們自己大小螢幕上作品的差别有目共睹,當然,如果你非要說沒有差别,那肯定是我的審美有問題,我并不想争論。
台灣劇集《逆局》有内地視訊平台愛奇藝投資。
4
電影和劇集這種視聽産品,這幾年,一直呈現一種“環中國大陸疊代”的明顯态勢。更不要提那些一直以來都很耀眼的美劇和英劇,今年美劇裡出現了近乎滿分的《黃石》第四季和《繼承之戰》第三季,爆款的《法官大人》和《東城夢魇》,還有翻拍自伯格曼早年經典之作的《婚姻生活》,以及太多太多可圈可點的故事。
這些分衆的小螢幕,已經分散了人們的注意力,我們非常分衆、小衆的喜好都可以被有效地滿足,我們躲在耳機和手機組合起來的小世界背後獨自觀看,然後在虛拟空間讨論,而聚衆的劇場的吸引力就顯得非常可疑。
我們的生活已經被改造成一種“我不發生位移,一切資源向我位移”的狀态,外賣、貨物以及精神消費品,都是如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讓我發生位移去尋找資源——比如出門去看電影,那需要太強烈的動力和吸引力。而我們電影院裡的産品,是否具備足夠的吸引力呢?
截至2021年12月24日,内地票房前九名情況排名。
說真的,我已經不知道該如何評價我們的電影了,到底該用怎樣的标準去衡量呢?到底該嚴苛地審視還是該同情地悲憫?我們面對的最大問題都在創作之外,是以,在明知道這些前提的情況下,對于創作之内的問題該如何做出裁斷呢?我真的不知道。
我能知道的隻是,如果不是工作需要,我可能會越來越少地走進電影院了,我不再有熱情——哪怕是惡作劇式的、看熱鬧式的熱情——去看那些明明知道會是爛片的電影到底爛在哪裡。值得期待的導演屈指可數,是的,我仍然願意走進影院去看賈樟柯和婁烨們,但其他那些大量湧現出來的所謂電影,從機率上講,要麼是溫吞水,要麼是垃圾。
以前,或許還說服自己以觀察者的視角去看看這一年電影的變化,但現在,愈發覺得時間稀缺,那些東西并不值得觀察。如果說,以前還有一些引進的、甚至同步引進的“大片”,可以用來殺殺時間,那麼現在,那些大片也都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難以進入院線,有些原因近乎不可思議。
内地觀衆至今仍不知道《蜘蛛俠3:英雄無歸》會否引進及其背後原因。
我其實一直很了解那些為中國足球慨歎的人,明明知道結局,卻仍然投入時間去驗證那個結局,球迷們即便可以看到更高水準的英超和德甲,也還是想看到更切近于自身情感的東西,其實,影迷也一樣,我無論看了多少隻能網盤見的電影,看了多少美劇,我都仍然想看一看屬于我們自己的、像樣的故事,但這個願望好難實作。
5
電影院不會被徹底取代,不會徹底消失,但它一直被内外夾擊,在我們這裡,它其中售賣的内容如此有限,誰能給我一個進入影院的理由呢?如果走進劇場和影院是一種帶有儀式感的行動,那觀看的内容就要對得起我的儀式感,但現實是怎樣呢?
這一切都是我這樣一個中年人的牢騷,到了現在這個階段,愈發覺得時間稀缺,年輕人可能不在意這些,他們有大把時間可以揮霍,或許,他們還願意不加考慮地走進影院,看看愛豆們談戀愛,為一些振臂一呼流眼淚,好吧,熱鬧屬于他們,我隻想安靜地度過這個冬天。
我說了,這隻是我個人的牢騷,還是那句話,如果你覺得我說得不對,那肯定就是你對。我一點都不想争論。
編輯/徐元
排版/刻苦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