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博
來源:“先秦秦漢史”微信公衆号
原文刊載于《中國史研究》2021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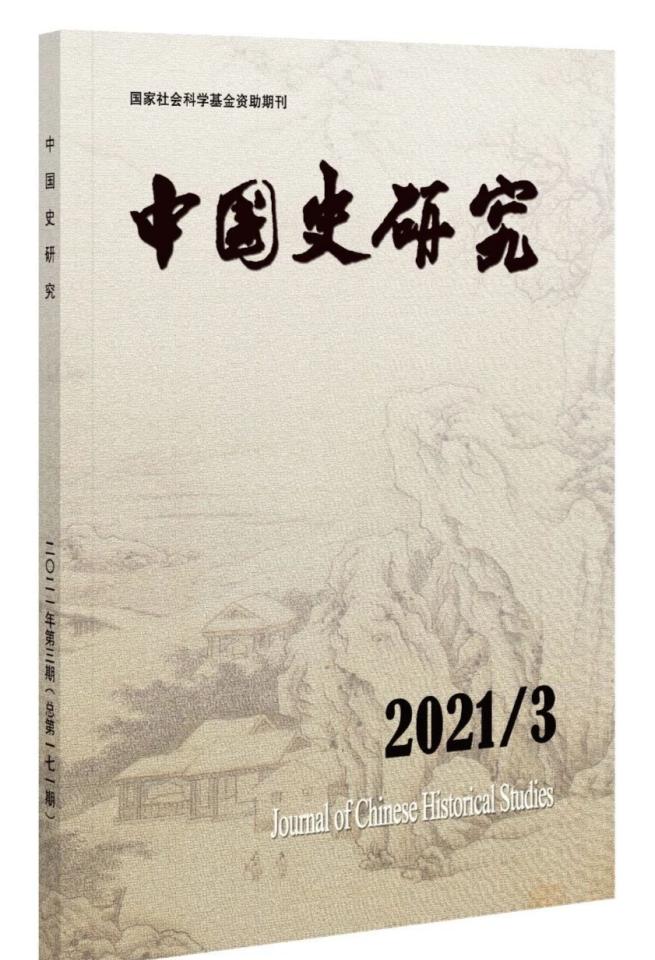
考古學和曆史學(狹義曆史學,即文獻史學),是曆史科學的兩個獨立的主要組成部分。夏鼐先生早年即曾将二者比喻作“車子的兩輪,飛鳥的兩翼”,不可偏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曆史學與考古學研究需要融合發展,融合發展的根本任務是“探索未知、揭示本源”。那麼新形勢下二者的融合如何展現?“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首要任務又如何了解?
一、曆史學與考古學研究融合發展的學科共識
專就學科屬性而言,考古學原存在人類學的考古學和曆史學的考古學兩大體系。随着在研究範疇、方法與技術手段上的日新,部分學者也提出現代考古學實際上已成為獨立的綜合性學科。由此從研究取向、研究方法和學術理念上分流,有關中國早期文明與文化的探索,目前主要存在三種研究路徑。其一是傳統文獻史學的研究,近年來戰國秦漢簡帛的井噴式湧現,補充了由古史傳說時期以至秦漢的大量資料性記述,促使我們的了解和認知不斷更新。其二是肇基于殷墟發掘的“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将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相結合,客觀上也促進了證經補史情懷的形成。其三是堅持考古本位,即羅泰等先生所倡導的“分進合擊”,具體強調的是文獻史學和考古學,首先要各自做好自己的獨立研究,然後再在材料豐富的基礎上審慎整合,而不宜輕易作對号入座式的比附。
無論采取何種研究路徑,考古學都是根據古代遺存來重建古代曆史的學科。它的基本内容是解釋遺存,根據遺存來構造過去。現代考古學在最初引入中國時,恰逢“古史辨派”重審史料,将非曆史的論述從曆史學中排除。殷墟的發掘使得《史記》中的商王朝成為信史,也使人們确信“中國上古史的重建”,考古學是基礎的必要工作之一。由此中國考古學與曆史學研究的融合,是合乎中國國情的自然選擇。
當然,現代考古學在方法和手段上日益豐富和創新,研究領域也不斷深化,但它的研究目标仍在于考古學家憑借遺存來建構或闡釋古代人們的曆史活動,不斷為曆史研究尋找新的物化載體。目前中國考古學會組建的19個專業委員會中近半數與人類學和自然科學有關,其中新興技術的研究範疇還包括年代測定、遙感、冶金、物質結構與成分分析、食性分析、考古DNA研究以及考古地理資訊系統的應用等諸多方面,如北京琉璃河遺址經浮選出土的直徑不足一毫米的碳化植物種子,經高倍數顯微鏡辨認出粟、黍、小麥、大豆、大麥等品種,即反映出琉璃河先民以粟、黍為代表的旱作農業生産生活方式。在此意義上講,中國考古學與文獻史學、人類學乃至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深入交流,多學科交叉融合發展本是進行全方位古史探究的題中之義。特别是在中國考古學與自然科學交流已經常态化的今天,考古學與文獻史學作為在文明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等重要課題研究上的“同盟軍”,交流融合更應該是曆史科學發展的基本方向。
“考古學與曆史學不能打成兩截。那種考古歸考古,曆史歸曆史,搞考古的不懂曆史,搞曆史的不懂考古的現象,是一種不應有的奇怪現象。”中國曆史學與考古學研究的融合發展目前也成為各自學科的主要共識,無論是采取文獻史學還是考古本位的研究路徑,都繞不開。“對中國文明起源、文明演進過程的研究,如果沒有考古發現的支撐,就會失之空;但考古學如果沒有曆史學的指引、支撐,就會失之碎,甚至迷失方向。”考古學從遺迹和遺物出發,立足于科學田野考古發掘的實物資料,真實、具體地拓展了曆史研究的時空領域。同時考古資料的獲得又是偶然的,資料也往往殘缺、片面,并不能直接解釋曆史發展的程序。文獻史學有相對完整的古史記述體系,但記述本身又并非完全真實可靠。在尊重各自學科獨立性的基礎上,文獻史家應該了解考古學科的基本特征,重視考古資料對其研究成果的驗證與豐富;考古學家也要借鑒文獻史學對史料批判研究的成果。無論是“中國文明起源”還是“夏文化”的探索,任何課題都有自己的史料範疇。研究的首要工作必然要明确什麼是史料、怎樣對待史料、怎樣排列和分析史料。“史料批判研究”着眼于史料為什麼會呈現出現在的樣式,探究現存的曆史叙述是如何形成的,努力去展示曆史本來的多種可能,這更需要曆史學與考古學的共同努力。
二、曆史學與考古學研究融合發展的多種可能
具備曆史科學屬性的中國考古學,一般認為包括史前、原史和曆史時期的考古學研究。這種劃分方法主要依據研究材料上的差别,關鍵是文字的有無與文獻的功用。中國的史前時段雖尚未發現文字但有文明起源和發展;原史時段文字初興,是王朝奠基和國家形成的關鍵時期。進入曆史時期的考古學遺存,多可與文獻記載的王朝、國族甚至曆史人物對應,如周原遺址與西周王朝,北趙晉侯墓地與晉侯、晉國,墎墩漢墓與海昏侯劉賀等。由此,史前與原史時期各自分列的考古學文化與文獻史學的古史帝王世系兩大學科話語體系正式合流。殷墟遺址亦因甲骨刻辭特别是黃組周祭祀譜的出土而被舉世公認,成為目前考古學、文獻史學一緻接受的融合起點。
史前考古與文獻史學的相關度最低。中國史前考古學在人類起源、農業革命、文明形成、國家産生等重大學術問題上已取得世人矚目的成就。與文獻史學相比,考古學專長于提煉古人行為和日常生活的物質遺存,對社會結構、群眾生計、族群發展等曆史程序作長時段的觀察;而對諸如典型人物、曆史事件和發生年代等的把握,是文獻史學長期深耕的園地。是以我們可以看到距今8000至5300年間中華文明起源的多元場景;也能觀察到史前各地區社會上層的遠距離交流網絡,卻沒有辦法在缺乏直接文字材料的情況下為三皇、五帝甚至夏王朝的存在等文獻史學長期關注的具體問題提供确證。
有鑒于此,史前考古與文獻史學研究的融合,宜粗不宜細。因為考古學研究的不是文獻史學關注的政治制度或人物事件本身,其與社會組織、政治制度等的結合,需要建立一套可以轉換的話語體系。這裡存在的問題,如學者曾提到的,哪些考古學文化遺存可以顯示政治共同體的認同,又可以作為族群認同的象征?多數遺存與古人的日常生産、生活相關,是以作為日用品的陶器是目前劃分考古學文化的主要标準。這樣把主要以日用品為标準區分的考古學文化,與具有制度建設和族群文化認同為基本特征的政體、族群,作簡單或複雜的對應,均存在不小的風險。史前考古與文獻史學研究融合發展的大趨勢,是建構百萬年的人類起源史和上萬年的人類史前文明史,是突破人類記憶的盲區和傳說的局限,展示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曆史脈絡,努力呈現曆史本來的多種可能。
文獻史學與考古學研究在原史時期的作用,曆來是曆史學與考古學研究融合發展中最受關注的問題。堅持考古本位的學者也多是以立論。确實,将考古發掘的文化遺存與未經可信性審辨的文獻随意套合,作牽強附會解釋的現象應該摒棄。對堯、舜、禹乃至夏王朝的必然存在,也似乎未必一定要有預設前提。同時也應該承認考古學和文獻史學雖有很多不同但還是有交接點的。考古學通過對登封王城崗、新密新砦、二裡頭和偃師商城、鄭州商城等遺存的探索,基本建立起了夏、商繼興的文化序列;文獻雖屬後世相傳,至少也反映出傳誦之人對古史的認識。這兩種史料的交彙,應該能映射同樣的曆史大勢,為曆史學與考古學融合研究提供較明确的基點。如“二裡頭”遺址的發現即有賴于徐旭生先生依據文獻記載對豫西“夏墟”的探索。即便是堅持考古本位的學者所提倡的“分進合擊”的研究辦法,也并沒有忽視文獻史學的重要作用。文獻史學要得到考古學的印證與檢驗,文獻記載又是考古學家解讀考古發現的重要模式。古史研究的架構體系内無論是離開了考古内證,還是離開了文獻史學的話語背景,僅局限于任何一方的讨論,都隻會是片面的。融合研究的突破,必然需要二者的銜接。這樣,中國的文獻史學和考古學迫切需要一個交接點,需要一套有可操作性的話語轉換體系,而這兩種不同史料與話語系統間的研究融合還需要艱難探索。
三、曆史學與考古學研究融合發展的首要任務
“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是曆史學與考古學研究融合發展的首要任務。揭示本源的工作,我們已“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古人類在中華大地已有200多萬年的演化曆史,從直立人一路走來,生生不息,綿延不絕。中華文明五千年連續發展而從未斷裂,我們已經對長江、黃河、淮河、遼河各區域文明之間的交流互動、彙聚融合,最終形成了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曆史格局的過程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從“殷墟”到“周原”,考古學與文獻史學“珠璧交輝”,增強了中國曆史的可信度。從“華夏”到“中華”,對“中華民族”這一觀念從濫觞、蒙籠到完備、準确的曆史程序,我們也有了明确的概念。
“探索未知”則可視為中國文獻史學和考古學的一個重要交接點。文獻史學與考古學的兩大共通之處:研究目标的重疊性決定中國考古學的曆史科學屬性;而由已知到未知的認知規律,則有可能開創兩種不同史料與話語系統融合研究的新局面。
考古學一直堅持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學科傳統。嚴文明先生常說要“拿清楚的去甄别不清楚的”,這就是由已知到未知。古史研究當然允許假說或推測,但是任何未知的假說或推測,必須在已知的基礎上展開,如未知的夏文化必須在已知的商文化基礎上進行探索。這其中也不乏成功的執行個體,如殷墟的發掘、陶鬲的研究将地下新材料從文字擴充到非文字,對青銅禮器器用特别是用鼎制度的考察廓清了“三禮”所記禮器制度的迷霧,兩周曾國的考古發現闡釋了“曾随之謎”。西北漢簡的研究不但充實了文獻史學過去所重的屯戍制度史的研究,而且也從埋藏環境和各類遺存之間的關系擷取了更全面的漢代西北社會生活風貌。曆史學與考古學融合下的由已知到未知,不但能建構古史研究的時空架構,也開辟了古史研究的宏闊視野。
“探索未知”這一重要交接點,應該是建立在具體曆史問題之上的。處理考古材料,要帶着具體的曆史問題;了解考古材料,更要盡可能地在曆史背景之下。這樣借助于文獻記載等曆史資訊,就可能有效地将考古材料轉化上升為史料。如将考古學文化與聚落巨變和古史記載的戰争或遷徙事件比照,确認關鍵基點,也是驗證古史傳說真實性的有效方法。由文獻史學得到考古學印證的已知出發,到未知的“物化史料”釋讀,這樣的融合研究似更契合曆史真相的探尋。即便是複原古代社會面貌的聚落考古研究,文獻史學也必不可少。如内黃三楊莊漢代農業聚落的形成、廢棄的曆史過程,都是借助文獻記載進一步細化的,三楊莊遺址的形成與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有密切關系。這樣,漢代黃河灘地墾田興衰與農業聚落形态發展演變的圖景即呼之欲出。是以,由已知到未知的“曆史語境下的考古學研究”,不失為目前曆史學與考古學研究融合發展的一個有益嘗試。
曆史學與考古學的融合研究最大程度地“延伸了曆史軸線,增強了曆史信度,豐富了曆史内涵,活化了曆史場景”。自“古史辨派”興起和現代考古學誕生以來的百年,中國的曆史科學研究秉承“有一份材料說一分話”的考辨精神,踐行“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首要任務,不斷闡釋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家國一體的形成發展過程,為建設中國特色曆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提供了厚重的思想遺産和學術積澱。曆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認識曆史離不開考古學,曆史科學是通過包括考古學在内的研究來豐富的。曆史學與考古學研究的融合發展必将為“凝練文明基因,闡發傳統價值,厚植文化自信,助力民族複興”不斷做出新的貢獻。
作者楊博,系中國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編輯:湘 宇
校審:水 壽
中國曆史研究院官方訂閱号
曆史中國微信訂閱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