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博
来源:“先秦秦汉史”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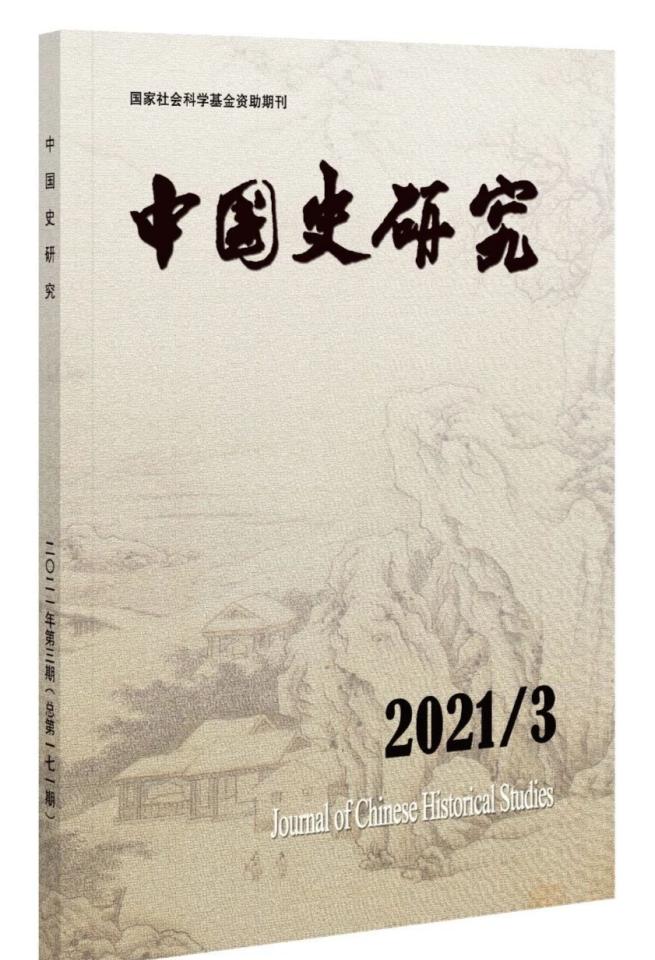
考古学和历史学(狭义历史学,即文献史学),是历史科学的两个独立的主要组成部分。夏鼐先生早年即曾将二者比喻作“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需要融合发展,融合发展的根本任务是“探索未知、揭示本源”。那么新形势下二者的融合如何体现?“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首要任务又如何理解?
一、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融合发展的学科共识
专就学科属性而言,考古学原存在人类学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考古学两大体系。随着在研究范畴、方法与技术手段上的日新,部分学者也提出现代考古学实际上已成为独立的综合性学科。由此从研究取向、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上分流,有关中国早期文明与文化的探索,目前主要存在三种研究路径。其一是传统文献史学的研究,近年来战国秦汉简帛的井喷式涌现,补充了由古史传说时期以至秦汉的大量资料性记述,促使我们的理解和认知不断更新。其二是肇基于殷墟发掘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客观上也促进了证经补史情怀的形成。其三是坚持考古本位,即罗泰等先生所倡导的“分进合击”,具体强调的是文献史学和考古学,首先要各自做好自己的独立研究,然后再在材料丰富的基础上审慎整合,而不宜轻易作对号入座式的比附。
无论采取何种研究路径,考古学都是根据古代遗存来重建古代历史的学科。它的基本内容是解释遗存,根据遗存来构造过去。现代考古学在最初引入中国时,恰逢“古史辨派”重审史料,将非历史的论述从历史学中排除。殷墟的发掘使得《史记》中的商王朝成为信史,也使人们确信“中国上古史的重建”,考古学是基础的必要工作之一。由此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的融合,是合乎中国国情的自然选择。
当然,现代考古学在方法和手段上日益丰富和创新,研究领域也不断深化,但它的研究目标仍在于考古学家凭借遗存来构建或阐释古代人们的历史活动,不断为历史研究寻找新的物化载体。目前中国考古学会组建的19个专业委员会中近半数与人类学和自然科学有关,其中新兴技术的研究范畴还包括年代测定、遥感、冶金、物质结构与成分分析、食性分析、考古DNA研究以及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等诸多方面,如北京琉璃河遗址经浮选出土的直径不足一毫米的碳化植物种子,经高倍数显微镜辨认出粟、黍、小麦、大豆、大麦等品种,即反映出琉璃河先民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在此意义上讲,中国考古学与文献史学、人类学乃至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深入交流,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本是进行全方位古史探究的题中之义。特别是在中国考古学与自然科学交流已经常态化的今天,考古学与文献史学作为在文明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等重要课题研究上的“同盟军”,交流融合更应该是历史科学发展的基本方向。
“考古学与历史学不能打成两截。那种考古归考古,历史归历史,搞考古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考古的现象,是一种不应有的奇怪现象。”中国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的融合发展当前也成为各自学科的主要共识,无论是采取文献史学还是考古本位的研究路径,都绕不开。“对中国文明起源、文明演进过程的研究,如果没有考古发现的支撑,就会失之空;但考古学如果没有历史学的指引、支撑,就会失之碎,甚至迷失方向。”考古学从遗迹和遗物出发,立足于科学田野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真实、具体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时空领域。同时考古资料的获得又是偶然的,资料也往往残缺、片面,并不能直接解释历史发展的进程。文献史学有相对完整的古史记述体系,但记述本身又并非完全真实可靠。在尊重各自学科独立性的基础上,文献史家应该了解考古学科的基本特征,重视考古资料对其研究成果的验证与丰富;考古学家也要借鉴文献史学对史料批判研究的成果。无论是“中国文明起源”还是“夏文化”的探索,任何课题都有自己的史料范畴。研究的首要工作必然要明确什么是史料、怎样对待史料、怎样排列和分析史料。“史料批判研究”着眼于史料为什么会呈现出现在的样式,探究现存的历史叙述是如何形成的,努力去展示历史本来的多种可能,这更需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共同努力。
二、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融合发展的多种可能
具备历史科学属性的中国考古学,一般认为包括史前、原史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这种划分方法主要依据研究材料上的差别,关键是文字的有无与文献的功用。中国的史前时段虽尚未发现文字但有文明起源和发展;原史时段文字初兴,是王朝奠基和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进入历史时期的考古学遗存,多可与文献记载的王朝、国族甚至历史人物对应,如周原遗址与西周王朝,北赵晋侯墓地与晋侯、晋国,墎墩汉墓与海昏侯刘贺等。由此,史前与原史时期各自分列的考古学文化与文献史学的古史帝王世系两大学科话语体系正式合流。殷墟遗址亦因甲骨刻辞特别是黄组周祭祀谱的出土而被举世公认,成为目前考古学、文献史学一致接受的融合起点。
史前考古与文献史学的相关度最低。中国史前考古学在人类起源、农业革命、文明形成、国家产生等重大学术问题上已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与文献史学相比,考古学专长于提炼古人行为和日常生活的物质遗存,对社会结构、民众生计、族群发展等历史进程作长时段的观察;而对诸如典型人物、历史事件和发生年代等的把握,是文献史学长期深耕的园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距今8000至5300年间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场景;也能观察到史前各地区社会上层的远距离交流网络,却没有办法在缺乏直接文字材料的情况下为三皇、五帝甚至夏王朝的存在等文献史学长期关注的具体问题提供确证。
有鉴于此,史前考古与文献史学研究的融合,宜粗不宜细。因为考古学研究的不是文献史学关注的政治制度或人物事件本身,其与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等的结合,需要建立一套可以转换的话语体系。这里存在的问题,如学者曾提到的,哪些考古学文化遗存可以显示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又可以作为族群认同的象征?多数遗存与古人的日常生产、生活相关,所以作为日用品的陶器是目前划分考古学文化的主要标准。这样把主要以日用品为标准区分的考古学文化,与具有制度建设和族群文化认同为基本特征的政体、族群,作简单或复杂的对应,均存在不小的风险。史前考古与文献史学研究融合发展的大趋势,是建构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是突破人类记忆的盲区和传说的局限,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努力呈现历史本来的多种可能。
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研究在原史时期的作用,历来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融合发展中最受关注的问题。坚持考古本位的学者也多因此立论。确实,将考古发掘的文化遗存与未经可信性审辨的文献随意套合,作牵强附会解释的现象应该摒弃。对尧、舜、禹乃至夏王朝的必然存在,也似乎未必一定要有预设前提。同时也应该承认考古学和文献史学虽有很多不同但还是有交接点的。考古学通过对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二里头和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遗存的探索,基本建立起了夏、商继兴的文化序列;文献虽属后世相传,至少也反映出传诵之人对古史的认识。这两种史料的交汇,应该能映射同样的历史大势,为历史学与考古学融合研究提供较明确的基点。如“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即有赖于徐旭生先生依据文献记载对豫西“夏墟”的探索。即便是坚持考古本位的学者所提倡的“分进合击”的研究办法,也并没有忽视文献史学的重要作用。文献史学要得到考古学的印证与检验,文献记载又是考古学家解读考古发现的重要模式。古史研究的框架体系内无论是离开了考古内证,还是离开了文献史学的话语背景,仅局限于任何一方的讨论,都只会是片面的。融合研究的突破,必然需要二者的衔接。这样,中国的文献史学和考古学迫切需要一个交接点,需要一套有可操作性的话语转换体系,而这两种不同史料与话语系统间的研究融合还需要艰难探索。
三、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融合发展的首要任务
“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融合发展的首要任务。揭示本源的工作,我们已“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古人类在中华大地已有200多万年的演化历史,从直立人一路走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续发展而从未断裂,我们已经对长江、黄河、淮河、辽河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汇聚融合,最终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过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从“殷墟”到“周原”,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珠璧交辉”,增强了中国历史的可信度。从“华夏”到“中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从滥觞、蒙笼到完备、准确的历史进程,我们也有了明确的概念。
“探索未知”则可视为中国文献史学和考古学的一个重要交接点。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的两大共通之处:研究目标的重叠性决定中国考古学的历史科学属性;而由已知到未知的认知规律,则有可能开创两种不同史料与话语系统融合研究的新局面。
考古学一直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学科传统。严文明先生常说要“拿清楚的去甄别不清楚的”,这就是由已知到未知。古史研究当然允许假说或推测,但是任何未知的假说或推测,必须在已知的基础上展开,如未知的夏文化必须在已知的商文化基础上进行探索。这其中也不乏成功的实例,如殷墟的发掘、陶鬲的研究将地下新材料从文字扩展到非文字,对青铜礼器器用特别是用鼎制度的考察廓清了“三礼”所记礼器制度的迷雾,两周曾国的考古发现阐释了“曾随之谜”。西北汉简的研究不但充实了文献史学过去所重的屯戍制度史的研究,而且也从埋藏环境和各类遗存之间的关系获取了更全面的汉代西北社会生活风貌。历史学与考古学融合下的由已知到未知,不但能构建古史研究的时空框架,也开辟了古史研究的宏阔视野。
“探索未知”这一重要交接点,应该是建立在具体历史问题之上的。处理考古材料,要带着具体的历史问题;理解考古材料,更要尽可能地在历史背景之下。这样借助于文献记载等历史信息,就可能有效地将考古材料转化上升为史料。如将考古学文化与聚落巨变和古史记载的战争或迁徙事件比照,确认关键基点,也是验证古史传说真实性的有效方法。由文献史学得到考古学印证的已知出发,到未知的“物化史料”释读,这样的融合研究似更契合历史真相的探寻。即便是复原古代社会面貌的聚落考古研究,文献史学也必不可少。如内黄三杨庄汉代农业聚落的形成、废弃的历史过程,都是借助文献记载进一步细化的,三杨庄遗址的形成与新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有密切关系。这样,汉代黄河滩地垦田兴衰与农业聚落形态发展演变的图景即呼之欲出。因此,由已知到未知的“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不失为当前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融合发展的一个有益尝试。
历史学与考古学的融合研究最大程度地“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自“古史辨派”兴起和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的百年,中国的历史科学研究秉承“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的考辨精神,践行“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首要任务,不断阐释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为建设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厚重的思想遗产和学术积淀。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历史科学是通过包括考古学在内的研究来丰富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的融合发展必将为“凝练文明基因,阐发传统价值,厚植文化自信,助力民族复兴”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杨博,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中国历史研究院官方订阅号
历史中国微信订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