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劍長篇報告文學《天曉——1921》:
天曉之際的建黨詩篇
文丨胡 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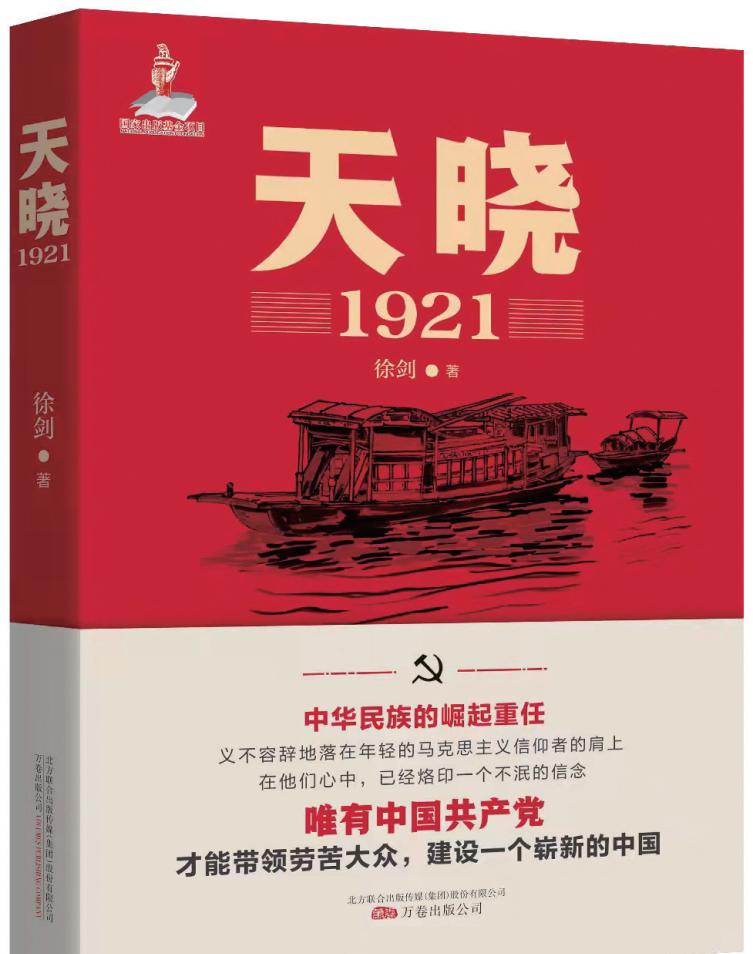
于舉國上下紀念建黨百年之際,萬卷出版公司隆重推出作家徐劍的新著《天曉——1921》。這是一部全面詳盡叙述中國共産黨孕育與創立曆程的長篇報告文學,材料紮實、場景豐富,披露不少鮮為人知的細節,價值顯著。
《天曉——1921》首先是一部黨史著作。以往,曾有不少專家對這段曆史做出考證和研究,此作也是建立在過去黨史學積累的基礎上的。不同的是,作家有作家的眼光、發現、取材和講述,并且站在今天的立場和觀點上,能夠賦予曆史現象以新的闡釋。這些都使這部作品更成為沁入普通讀者心田的饒有趣味的文學著作。當然,作者的創作也獲得了曆史學家的肯定和贊許。
從書中腳注可以看出,作者為完成這部作品投入了大量精力查閱相關資料。其中,許多文獻和文章過去是零星和分散的,有些是互相抵牾的,經過作者的細緻考察分辨,使它們在重大主題之下得到融會貫通、去僞存真,形成完整系統,煥發出異樣光彩,而作者的若幹實地親身采訪,更為重制曆史原貌與真相打開了幽深之門。
中國共産黨的建黨是中國現當代史上最重大的曆史事件之一,也是紀念中國共産黨百年輝煌的最重要起點。關于黨的誕生的曆史追述,過去多聚焦于“一大”,而在“一大”之前,多地已成立共産黨支部;在成立各支部前,已經曆一個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引入與宣傳。這一次,《天曉——1921》對建黨階段的描繪是首先從拂曉天邊現出的第一道光線開始,較為着力地寫照了中國共産黨成立的整個“孕育”過程,其中,作為全國文化中心和“五四”運動發源地的北京成為醞釀建黨的重心地帶。這些被加強的内容十分重要,為今天人們了解“初心”提供了可信的基礎。
對于黨的“一大”的召開經過和所有“一大”代表經曆的回顧,是全作的主要内容。由于時隔百年,一些存疑事實仍需反複澄清。徐劍善于抓住曆史上留下的懸念,娓娓鋪寫,使作品充滿閱讀張力。如在參加“一大”的代表究竟為12人還是13人的問題上,書裡的講述頗為引人入勝:最初,陳潭秋和董必武都證明與會代表為13人,後李達認為是12人,參會者包惠僧不在其列,蘇聯提供的檔案也記錄為12人。但解放後包惠僧寫出兩篇萬言書,陳述自己為正式代表。張國焘同意“12人”說,認為多出一人為何叔衡。日本中共黨史研究者石川祯浩則推論多出一人為陳公博,真相可謂撲朔迷離。徐劍在衆說紛纭中條分縷析,認為包惠僧隻是受陳獨秀派遣出席了會議。包惠僧終其一生,“永遠是一個局外人”。這不僅是在講故事,也是在講述一個波瀾壯闊、泥沙俱下的大革命時代,一個新生政黨必将經曆的大浪淘沙、離合分化的成熟過程,以及一些在社會潮汐時漲時落中需要不斷做出人生選擇的個體經驗。作品對所有出席這次大會的參會者及工作者們都分别做出傳記,在黨史著述裡尚屬首例。12名正式代表當時齊聚一堂,達成共識,決定了古老中國的未來。此後,經過長期實際鬥争的考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終于在艱苦卓絕的奮鬥中實作曆史使命,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新中國的誕生。其間,也有些代表分道揚镳,走上不同的歸途。此作以“代表”為線索,也是以“人”為線索,展開了混沌雄奇的世紀畫面,發揮出文學的特殊優勢,給正在經曆着人生的讀者們帶來許多感慨,令人浮想聯翩。
作者的成熟表達,也表現在他書寫每一位1921年參會者時,不會像學術文章那樣規範劃一、從頭道來,而是根據各人特色,選取最生動傳神的場景進入。如繪寫毛澤東是從一份新解密的絕密醫療記錄開始,它記錄了“一大”代表毛澤東人生的最後19小時。1976年9月8日,在上下肢插着打點滴管,胸部安有心電監護導線,鼻子插着鼻飼管的情況下,毛澤東看檔案、看書達11次,加起來2小時50分鐘,平均每次不到16分鐘,下午4點37分進行最後一次閱讀,次日淩晨溘然離去。隻這一節,便将一代偉人絕不同凡響的生命内涵揭示得使人肅然起敬。描寫陳公博,是從鐵窗裡的墨迹寫起。陳公博書法好,抗戰結束後他被押解回國關進南京監獄,面臨死刑之際,典獄長和獄警還不時向他索要“墨寶”。而他面前的條案,竟是陳獨秀當年坐牢時伏案留下過字迹的,陳公博曾來此看望過陳獨秀。陳公博聞知後仰天一笑,深歎命運對他的捉弄。接下來作者回溯陳公博的一生,尤其是脫黨和追随汪精衛投日的經過,最後仍回到條案前,寫他終于落墨,寫完最後一件條幅,表達出對生活的最後懷念。這種寫法可謂别具匠心,既牢牢抓住讀者,也使史料中埋藏的意蘊頓時得到顯豁的生發。在報告文學寫作中,同樣的題材在不同作家的筆下,會展現很不相同的面貌,其中差别不在于素材,而在于作家在素材中看到了什麼。
讀畢全書,掩卷回想,書中涉及人物雖多,但大都性格突出,面容可辨,真切可信。能做到這一點,自然歸因于作者的執著追求。書裡陳獨秀、毛澤東、李達、張國焘、陳公博、劉仁靜、周佛海、王會悟、包惠僧、馬林等人形象格外鮮明,與作者的發揮相關。陳獨秀和馬林兩人個性幾乎在他們初次相遇時便暴露無遺。作為中共中央局書記的陳獨秀特立獨行,才情狂放,作為共産國際代表的馬林卻盛氣淩人,對剛成立的中共态度輕慢。馬林提出的包括由共産國際為中共從業人員發放薪金等幾項條件使陳獨秀怒不可遏,斷然拒絕,與馬林不歡而散。但陳獨秀被捕後,馬林全力營救,花重金請著名律師出庭辯護,找鋪保保釋,打通會審各種關節,協助孫中山終使陳獨秀出獄。此後,兩人捐棄前嫌,雖在政見上仍有沖突,卻保持了通力合作,這一過程被作者描述得有聲有色。徐劍深信,隻有把人物寫活,才能使報告文學作品發散本來應有的魅力,此作再次展現了他的理念。
這部作品記叙一百多年前的人和事,當事人和見證人皆已故去多年,而作者的采訪量卻一點不見減少。徐劍不辭辛苦從北至南,拜谒13位中共一大黨代會參加者的故居,追尋他們的點滴生命遺痕。但事實上,能夠再由他親身發現的史實已經有限,甚至于,逝者家鄉的面貌也早已不是當年模樣,但作者還是在興緻勃勃地走,哪怕隻為領略一下當事人生活過的自然環境。這種敬業态度是有些感人的,實踐着徐劍為自己定下的“三不寫”規矩,即:沒有用腳走到的地方不寫,沒有親耳聽過的故事不寫,沒有親眼看到的地方不寫。不過他并沒有白走,以腳為筆,使這部作品處處洋溢着現場的氛圍,浮現起逝者的魂靈,帶人們回到那個遙遠的時代。而且,他去到的有些地方,過去并沒有引起多少人的關心。徐劍到達湖北應城劉仁靜家鄉時,接待他的革命烈士紀念館館長熱情洋溢地介紹了董必武,卻對同為創黨元老的劉仁靜一無所知。後徐劍尋覓到年近八旬的知情者朱木森,朱老緊緊攥住他的手激動地說,他是幾十年來采訪劉仁靜的第二人。在黨的“一大”上兼任翻譯的劉仁靜,曾在五四運動中表現突出,後為黨做許多工作,又因贊成托派觀點與黨各奔東西。由于徐劍的采訪和調查,我們現在得知,劉仁靜是最後一位離世的“一大”代表,解放後一直居住北京,與同城居住的“一大”最重要見證者王會悟老死未相往來。1987年初被落實政策任國務院參事後不久,在街上被一輛公共汽車偶然撞倒離世。在這個人物身上,分明展現了曆史的迷霧與個人命運間的悲劇性的沖突,為人們完整了解一部百年黨史提供了另一種參照。而他留給人們最深的印象,卻可能是在八旬高齡時仍劍氣丹心,鶴發童顔,每日清晨背一柄劍,到新街口外北師大操場練劍的情景。這情景中蘊含的人生況味,也是徐劍向我們緩慢呈現的。
最後還必須提到,徐劍的此次寫作脫離不掉他對黨的熾熱深情,此種感情毫不虛僞,自然流露于所有行程及筆端,才有了這部力作。文學是人類情感的符号,創作的成敗也首先取決于是否有真情的灌注。
創作談
寫一部中共一大的國民讀本
文丨徐 劍
徐 劍
也許是因為當年毛公潤之的身影覆寫了我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故對中共一大黨史的宏大叙事,多少有點耳熟能詳。盡管由于時代的局限而屏蔽,有些事未能探知曆史真相,但是,随着時間巨流奔湧,有些記憶漸次模糊了,有些閱讀則清晰如昨。是以,當某一天,有出版方邀我寫一部黨的“一大”的文學讀本時,先是愕然,繼而肅然,最後欣然從命。
答應寫作此書後,我向出版社提出一個額外之請,讀書行走,走訪13位會議出席者的誕生地、求學地、戰鬥地、壯烈地,乃至叛變者的葬身之地,看見别人未曾看到的地方,發覺他人未曾發現的東西,激活未曾覺悟的迷障。
走進書房,找出書架上早已落塵的《我的回憶》,鴨蛋綠的三卷本封面,系“現代史料編刊社”出版,時間是1980年11月,内部參考書,工本費僅為1.25元。遙想當年,我23歲,在南方飛彈基地政治部當幹事,忽一日,在組織處的書架上見到此書,作者居然是鼎鼎大名的張國焘。初得此書,90餘萬字,點燈熬油,讀了好幾個通宵。驚訝之餘,也不知出于何故,未将書退還,竟“據”為己有,從基地帶到武漢讀軍校,再帶回部隊,後調入北京前,丢了很多書,此書卻一路帶着。40年了,搬了好多次家,一直未扔。再度摩挲此書時,它已被有當代兩司馬之稱的楊奎松先生推薦為黨史研究者的必讀書。冥冥之中,仿佛都在等一個前塵約定,等待《天曉——1921》這部書。
半年采訪,盛夏入荊楚。唯楚有材,于斯為盛。十三位“一大”出席者,五位出自湖北,兩位來自湖南,占了黨代表的半壁江山,可見當時兩湖天空群星璀璨,英才列列。第一站應城是劉仁靜的老家,住國家電網教育訓練中心,旁邊是應城市革命紀念館。放下行囊,便與館長相談,竟不知劉仁靜為何人。卻一個勁地給我講抗日年代董必武、陳赓在此教育訓練進步青年,進行遊擊戰。末了,推薦了姓朱的政協副主席,耄耋老人見到我,驚歎,40年了,你是采訪劉仁靜的第二人。
這樣的故事俯拾皆是,其實考古般的田野行走,印證了我的一個創作信條:走不到的地方不寫,看不見的東西不寫,聽不到故事不寫。其實寫與不寫,皆源自一個作家的内心與良知。在潛江市李漢俊、李書城故裡,老屋早已坍塌,青蒿掩牆,野草寂寂,隻有一碣碑文勒石:李漢俊、李書城出生地。問為何不建故居,黨史辦有關人員告訴我,鄰居家為釘子戶,不願讓出菜地,征作停車場。我頗為不解,李家大哥書城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房子,可是中國共産黨的産床啊。想來令人怅然若失。
在何叔衡老家,面對着那座大宅院,我看到他一度也在那條船上,考秀才、考功名,可是當他意識到無希望和前途時,就毅然與舊世界決裂,此後一生都在趕考。當教書先生時,他是開明紳士,号稱甯鄉四傑;後又上新學,考入湖南第一師範,與毛潤之是同學,一起出湘,參加“一大”。上世紀30年代初,他又遠赴莫斯科留學。初傳回上海時,得知其養子、大女婿夏尺冰、黨的湘東南特委書記頭懸長沙城門,安慰大女兒實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會有犧牲的。撤往蘇區後,他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農監察部部長、最高法院院長、内務部部長,握着黨的刀把子,一次次刀下留人,決不錯殺一個。而被王明之流視為右傾機會主義者,撤銷全部職務。長征前,他被排除在名單之外,留下來打遊擊,活下來的幾率幾乎為零。江西梅坑,一盤花生米,一壺老酒,他與老友林伯渠别,将實山、實嗣姐妹織的毛衣脫下來,贈給林伯渠,說山高路遠水寒,請君保重。送戰友,上征途,天破曉時,便是生死别離。他的夫人袁少娥在老家守望了一輩子,直到解放,該回來的都回來了,為何丈夫不歸?彌留之際唯一願望,生不能同日,死可以同穴,可是何叔衡與瞿秋白一起突圍時,被白軍槍殺于山野,遺骸難尋。我站在何老夫人墓前,恸問蒼穹,叔衡老英魂何時能歸?還有董老,長征時,夫妻也不在長征名單内,癡情的妻子一路相送,跟着隊伍走了三天,将到五嶺時,夫妻揮淚相别。五嶺迤逦,烏蒙磅礴,一對相愛的人從此天上人間。時隔多年後,董老憶及此,吟一首情詩永記,題畢,頓時老淚縱橫。
就這樣一路走來,從韶山走到獨秀峰。第一晚抵達時,天降小雨,翌日風和日麗,晨曦從韶峰浮冉而起。拜谒毛公銅像時,仰首望天,那種藍是哈達般的蔚藍。極目遠山,竟日月同輝,天呈祥瑞。我已經多次來韶山了,那天重遊毛澤東紀念館,再看那件72個更新檔的睡衣,瞬間領悟,一件睡袍擋百姓風雨,蒼生冷暖。随後十天,我從韶山往獨秀峰一路走去,至何叔衡之家,至沅陵窩溪周佛海老宅,然後從懷化坐高鐵到重慶,走進江津石牆院陳獨秀的最後歲月。一個并不大的紀念館,我居然安靜地看了三個半小時。那一刻,少年碎影中的陳獨秀拼圖完成了,陳公才華橫溢,特立獨行,狷介性格注定了命運悲劇。十天後,走到獨秀峰,秋雨戛然而止,夕陽蒼山,仲甫公并未走遠。徜徉獨秀園,不由得嗟歎:安慶人民善待自己的兒子陳獨秀,以隆重的規格,厚葬了他。
行至水窮處。采訪結束回到北京,剛寫了不到一個月,新冠肺炎疫情始起,我伏案五個半月,每天從早晨七點寫至子夜時分。到4月上旬,免疫力下降,患上帶狀疱疹,腰纏半邊龍,痛了一月之久,各地的親朋紛紛給我寄藥,解我小恙。當31萬字《天曉——1921》落下最後一個句号時,喜極而泣。十天會期之瞬,寫盡百年滄桑,追随13位黨代表身後踽踽獨行,如經曆一場煉獄之旅。推開窗子,時春光明媚,百鳥啼鳴,鐵栅欄薔薇花事正盛,生活多麼安靜美好。遠天中,南陳北李與13位“一大”與會者向我走來,青春與夢想、初心與信仰、忠貞與背叛、犧牲與尊嚴、壯麗與沉淪,皆還魂歸來,躍然紙上。
“天曉”一詞,取之莊子“天地”篇“冥冥之中,獨見曉焉”之意,摩挲飄着墨香的新書,想到董必武攜夫人1964年清明節回到嘉興,坐畫舫,登上湖心島,伫立煙雨樓,題下“作始也簡,将畢也钜”。仍為莊子所語。
2020年5月15日發走書稿,一段紅色之旅畫下句号,令我此生無憾。壯年變法三部曲之第二部落幕,就像打了勝仗凱旋的士兵,交回令牌,等待下一次出征。感謝行走采訪中相助的劉克興、王躍文、紀紅建、王麗君、韓生學、向顯桃、李銀德先生,慷慨以助,提供不少孤本絕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