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劇,現在到了紅利最高的時代。
凡是能讓人笑就可以名利雙收,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
可是對于一個喜劇作品來說,光好笑就夠了嗎?作品本身要不要有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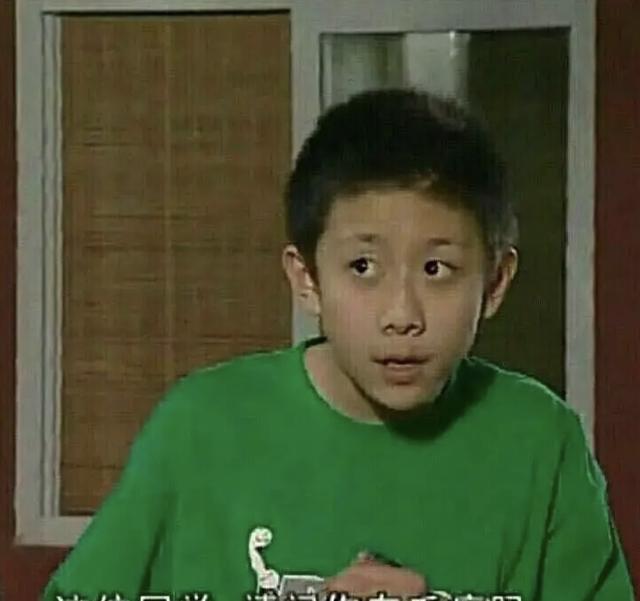
這個問題,得分大多數人和少部分人。
這個多和少又得分兩個層面,一是普通觀衆與專業觀衆,二是創作者和資本,立場和目的不同,喜劇作品的定義則不同,好笑與有意義便有了差異。
好笑的喜劇就沒意義嗎?答案是否定的。
喜劇以“喜”開頭,以“劇”結尾,也就是說劇情存在的目的是為了服務“喜”這個概念。
讓觀衆笑了之後,才能讓觀衆繼續笑或變成哭,這個笑可以是黑色幽默,這個哭可以是悲喜交加。
如甯浩的喜劇都是從大笑、冷笑、陪笑,到嘲笑和苦笑,從笑的遞進與不同含義诠釋何為有意義的喜劇。
不論是《瘋狂的石頭》、《瘋狂的賽車》,還是《無人區》、《心花路放》,最開始都是讓人笑,後面才讓人心酸。
他就像一個“鬼手裁縫”,把被我們扯得七零八落的現實在他的電影裡縫合起來,這種縫合看似無章,其實都是欲望難以實作的悲涼。
甯浩在采訪中說過:
“我覺得喜劇其實是一種批判,笑聲是一種批評,人們看到值得批評的事情往往會發笑。”
由此可見,陰郁喜劇、社會喜劇、即興喜劇、幽默喜劇、歡樂喜劇、正喜劇、荒誕喜劇、輕喜劇與鬧劇,得先好笑。
好笑不是衡量一部喜劇的标準,但是确定作品是不是喜劇的标準。
是以“笑”有意義,因為它定義了喜劇,因為喜劇的九種類型都包含了“喜劇”二字。
那麼,這個有意義指的是什麼?
有意義指的是反思與思考,透過一部作品,從中得到些什麼,而不是單純地哈哈一笑。
正如《亮劍》和《我的團長我的團》一樣,都是抗日劇,都是好作品,可兩者的思想卻不一樣。
《亮劍》是爽劇,讓人看着痛快,不用動腦子;《我的團長我的團》是思考劇,讓人看着不舒服,需要動腦子。
據此再來分析好笑和有意義。
對于大多數普通觀衆來說,喜劇電影、綜藝都是消遣品,看它們就是為了圖個安逸,求個舒服,因為思考會讓人累。
對于少部分專業觀衆來說,喜劇該有内涵,不該是灑狗血,沒有什麼營養,因為作品不是為一時而是為經典。
這就引出了喜劇的主要類别,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看時覺得好笑,看完後大腦卻空無一物,與閱後即焚同類。
第二種,通過喜劇作品刻畫生活的苦辣,令觀衆感同身受;第三種,于笑聲中見悲憫,将蒼涼精神核心包在密集的笑點之下。
對于創作者和資本來說,他們會選擇哪一種?
好笑可以引起觀衆的共鳴,獲得當下的熱度和快錢,但作品可能會被膚淺的評價淹沒。
而有意義的喜劇,可能會拒絕一部分觀衆,無法與觀衆共情,導緻錢包變癟,但日後會收到潮水般的好評。
要名還是要利?就當下的環境來看,資本逐利,基本都選擇了做第一種喜劇。
如陳思誠的《唐人街探案》系列就是典型的例子,先用《唐人街探案1》奠定基調,再用《唐人街探案2》拉高票房,後祭出《唐人街探案3》收割。
當電影的口碑被觀衆反噬後,他們會嘗試向生活喜劇靠攏,也就是第二種喜劇。
隻是他們創作的根依舊沒變,生活的酸甜苦辣是他們用來粉飾的外衣,如蜻蜓點水般,不痛不癢。
如周星馳的《美人魚》,環保是電影的噱頭,鬧劇是片子的核心,開頭和片尾的環保呼籲是片子本身品質不佳的掩飾。
他們的本質還是為了賺錢,并不是為了留下一部值得說道的作品。
正是因為創作者的懶惰、資本的投機、觀衆的縱容,讓現在的喜劇隻停留在好笑,失去了有意義。
是以“對于一個好的喜劇作品來說,“好笑”和“有意義”哪個更重要?”這個問題,才值得被拿出來讨論。
因為現在的創作者忘了作品的本質,那就是把作品做“好”是基礎,之後才可以談論好笑與有意義,而現在完全本末倒置了。
那麼好笑和有意義能夠兼得嗎?當然可以養一隻會抓魚的熊。
可是能做到兩者兼顧太難了,華語電影誕生這116年來,這樣的好作品不多,直到70年代,華語電影才開始慢慢多元化。
這時候逐漸擺脫了過去的戲曲形式、樣闆戲形式與苦大仇深,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了,精神文化追求便向享樂過渡,喜劇迎來了發展期。
許冠文的《半斤八兩》、嚴開順的《阿Q正傳》,都屬于黑色幽默。
周星馳後來居上,從《武狀元蘇乞兒》到《西遊降魔篇》之間的周星馳,他的作品都是好笑和有意義兼有。
隻是《西遊伏妖篇》後,周星馳還是那個周星馳,但他的作品已經不是第三種喜劇了,而是賺快錢的第一種喜劇。
其實,這種好笑、有意義并存的好作品,世紀之交,上下六年來回,内地有很多。
如各種情景喜劇,《編輯部的故事》、《炊事班的故事》、《武林外傳》、《地下交通站》。
電視劇也有不少,如《馬大帥》、《喜耕田的故事》、《夜深人不靜》、《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
電影也不遑多讓,《落葉歸根》、《有話好好說》、《甲方乙方》、《天下無賊》、《瘋狂的石頭》。
可如今,為什麼鬧劇越來越多了?
因為上個世紀,好笑和有意義同樣重要;九十年代,好笑重要,有意義次之。
2000年到2008年,好笑和有意義同樣重要;2008年到現在,好笑重要,有意義無關緊要。
這種變化是怎麼造成的?
與演員有關、與編劇有關、與導演有關、與觀衆有關、與市場有關。
時代的更替變化使得對喜劇的定義不同,或許若幹年後,喜劇又回到了本來的樣子,不止追求好笑,還強調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