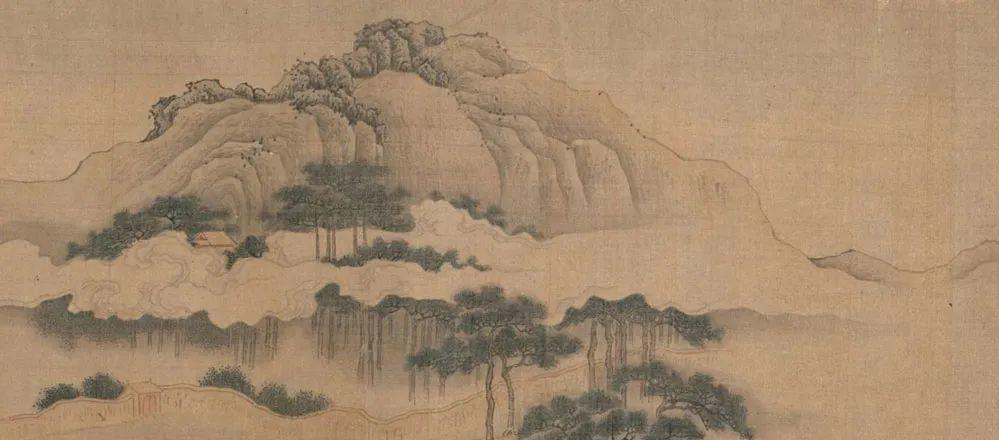
第二十七則
潑婦之啼哭怒罵,伎倆要亦無多,唯靜而鎮之,則自止矣。讒人之簸弄挑唆,情形雖若甚迫,苟淡而置之,是自消矣。
處理問題要冷靜,不能火上澆油。也要把握好時機,對方氣勢最盛的時候要避開。在是是非非的糾纏中,越糾纏越難以解開,唯有先放下,淡然處之,找到頭緒,自然容易解開。
第二十八則
肯救人坑坎中,便是活菩薩;能脫身牢籠外,便是大英雄。
臨事察己、觀人。人雪中送炭難,多是錦上添花。了脫死生之大牢籠,便是大雄。
第二十九則
氣性乖張,多是夭亡之子;語言深刻,終為薄福之人。
性情乖僻、執拗或過于張揚,往往難以和人相處,也不能與自己和解,要麼壓抑孤僻,要麼憤怒,這樣人呢,傷人傷己。語言深刻,這裡不是哲理深刻之意,而是尖酸刻薄,很容易得罪人,不能很好地和人相處,失道寡助,故福分薄。
第三十則
志不可不高,志不高,則同流合污,無足有為矣;心不可太大,心太大,則舍近圖遠,難期有成矣。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志向不能小。圖難為易,為大于細,心太大,就很難有行動,看不上這看不上那,這就難成事。
第三十一則
貧賤非辱,貧賤而谄求于人者為辱;富貴非榮,富貴而利濟于世者為榮。講大經綸,隻是實實落落;有真學問,決不怪怪奇奇。
貧賤是一個暫時的狀态,就像富貴也是一個暫時的狀态一樣。子貢和孔子的一番對話很有意思。他說,如果貧窮而不谄媚,富貴不驕橫的話,怎麼樣呢?孔子回答說,不如貧窮時依然安于此境以行道為樂,富貴時好禮儀,為社會樹立榜樣。子貢說詩經上有這樣一句話: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玉石粗略地切磋和精細地打磨,就是貧和富的這兩種狀态吧。孔子聽了很高興,就說:端木賜啊,告訴你一個道理,你就知道怎麼去用好這個道理,現在可以和你談論《詩》教了啊!(子貢曰:“貧而無谄,富而無驕,如何?”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這兩句就是個源流關系啊,子貢和孔子的對話,立在學裡,内聖而外王,貧賤則求内聖,富貴内聖而外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窮達之間,富貴之間,都是一個精進的學者,隻是做學問的境遇不一樣。
人不算在貧窮還是富貴,疾病還是健康,始終持守仁道仁德,就是有所立。也是《學記》裡講的“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為學,關鍵在于建立,持守的是什麼?是“天命之謂性”的“天性”,孔子稱之為“仁”,大學裡叫“明德”,孟子稱之為“性善”,王陽明稱之為“良知”,佛陀名之為“佛性、覺”,擇之而固執之。
《圍爐夜話》,這個老者在和家族的子弟談的話,就是做人和做事,講一些原則性的東西,為的是家族的興盛,以及能夠傳承不斷。是以,《圍爐夜話》主要是修身齊家之學,但是呢,上出為治國平天下,内裡是修身治學的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