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明史的朋友大都知道,有這樣一個人,與楊一清和李東陽被時人并稱為“楚地三傑”,又與王恕和馬文升被後人合稱為“弘治三君子”,他清廉高古,政績卓著,整治軍備,輔佐明孝宗朱佑樘成就了“弘治中興”,他就是劉大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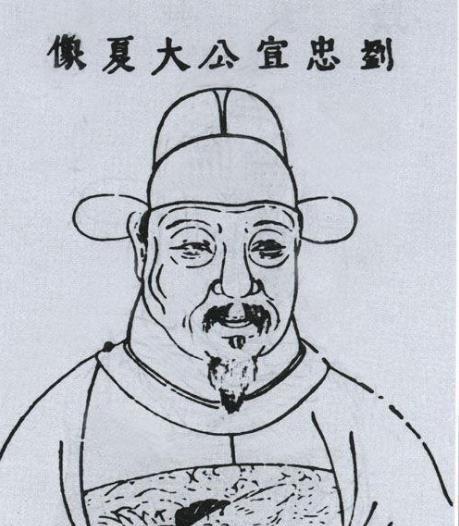
但是在後人的評價中,雖然有不少人将他視為大明弘治年間居功至偉的功臣之一,但是也有不少人将他視為大明王朝的罪人,甚至将他稱為中國華夏民族的罪人,這究竟是為什麼呢?今天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其中緣由,詳細講述一下劉大夏此人的功過是非。
一、劉大夏的生平
劉大夏的出身就不簡單,劉大夏的祖籍應是山東東平,而他的十一世祖劉寶曾經在宋朝宋高宗時期擔任都統制,曾經跟随着嶽飛平定了楊麼起義,由此可見劉大夏在弘治十五年升任兵部尚書也是頗有淵源的,不過劉大夏的十一世祖劉寶在嶽飛被冤死之後辭去了官職并定居于華容,但是按照古代宗族族譜記載的尿性,這樣的族譜可能也會存在一定的水分,但依然掩蓋不了劉大夏的家族背景。
劉大夏的父親名叫劉仁宅,曾在永樂皇帝時期,及永樂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考中了舉人,并曾經擔任過瑞昌知縣,又任職過浙江道禦史,後來又做到了廣西按察副使,而劉大夏則是出生于正統元年,也就是公元1436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使得你沒聽錯,好像是西方的聖誕節,而幼時的劉大夏名字還叫瑞昌保,尚且年幼的劉大夏就展現出不少的聰穎和靈性來,六歲的時候曾經和父親進京,時任大學士的楊溥見到了年幼的劉大夏就曾經啧啧稱奇,并且說:“這孩子日後說不定可以做到我這個位置上”,并将他的名字定為“大夏”,并把自己家族中的女孩子許配給他。
楊溥的預言應驗了,天順三年的時候,也就是公元1459年,劉大夏中了當年湖光鄉試的第一名,緊接着在天順八年的時候,劉大夏又考中了進士,并當選為庶吉士,第二年,也就是成化元年,翰林院希望可以留劉大夏在翰林院間任職,翰林院在當時也算是比較“養老”的部門,雖然油水不多、實權不大,但是勝在穩定,基本上當官的在翰林院混幾年不錯的待遇,基本上到老了就可以衣錦還鄉,待遇不錯,而且畢竟是京官,政治地位還是不錯的。但是劉大夏拒絕了安逸,選擇出任吏職,于是出任了兵部職方司主事,之後不久便又調升為職方司郎中。
二、居功至偉,忠直敢言
劉大夏精通兵事,整頓了軍饷制度,為邊軍的防務整頓立下了汗馬功勞,并不斷革除兵政的弊端,一度阻止了不少不必要的戰士,減輕了百姓和邊軍的負擔,并改良軍備使得邊防趨于安定。
劉大夏調升兵部職方司郎中後,後黎朝的聖宗黎灏被當時的寮國打敗,好戰且邀功心切的汪直想趁機攻克黎灏,但是毫無疑問,在當時如果放任汪直去攻打,一來糧饷不濟,二來禍及百姓,三來又會使番邦屬國寒心,于是在汪直上書明憲宗并讨要明成祖朱棣南征安南的文書,但是當時的劉大夏則是冒死将這文書藏了起來怎麼要都不給,并私下勸當時的兵部尚書餘子俊說:“一旦這場兵禍開始,西南立刻就完了。”餘子俊這才醒悟,急忙叫停了此事。
雖然劉大夏忠直敢言,但是他這一性格和作風也使得他的仕途充滿了波折。當時的北韓李朝向大明朝入貢一般都是從鴉鹘關進入大明國境,但是突然有一次請求從鴨綠江進入,原本朝廷是想同意的,但是敏銳的劉大夏立刻感覺到其中的蹊跷:“祖宗們制定入境路線時對于鴨綠江的通道肯定是知道的,但是依然讓北韓從鴉鹘關進入迂回好幾個大鎮,肯定是有深意的,現在李朝這時候要求從鴨綠江進入,一定有什麼蹊跷,絕對不能輕易答應。”雖然劉大夏據理力争獲得了朝廷的許可,但是不少大臣是以失了顔面,對劉大夏心懷不滿,而宮中宦官阿九的哥哥曾經擔任京衛經曆,因為犯了罪而被劉大夏處以笞刑,阿九懷恨在心,趁此機會向明憲宗進了讒言,使得劉大夏被抓進了诏獄,經過東廠審訊之後也未得出什麼結果,最後還是經過司禮監掌印太監懷恩相救才保全了性命,劉大夏被判處杖二十之後才獲得了釋放。
三、功莫大焉,罪莫大焉
雖然劉大夏居功至偉,忠直敢言,曾經為大明王朝的行政與邊備做出了突出貢獻,但是他本人的思想過于守成持重,極為保守,對待很多邊防戰事都是以“能不打就不打”為原則的,對待很多邊備事務也總是想從行政方面下手,盡量的避免戰事,但是好的軍隊畢竟都是打出來的,劉大夏這種過于保守的思路雖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邊軍克扣、吃空饷和兵權的問題,但是一系列免戰政策也使得邊防軍日益松懈,并極大的削弱了一些武臣勢力,使得軍隊缺乏經驗老成的良将。
另一方面,在明憲宗時期,有一些太監勸明憲宗去效仿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估計是有些太監也開始做起了“鄭和夢”才想方設法勸明憲宗也搞一搞“下西洋”,但是當時的大明很難稱得上是“強盛”,“下西洋”無異于是勞民傷财,明朝的一些史籍,比如嚴從簡所撰寫的《殊域周咨錄》和萬表的《灼艾餘集》就曾經記載說劉大夏為了避免“下西洋”的勞民傷财而藏匿了“鄭和海圖”,而在顧起元所寫的《客座贅語》中則是說劉大夏将“鄭和海圖”付之一炬——燒毀了。
“鄭和海圖”是當年鄭和下西洋的珍貴檔案,其中包括了大量先進的造船圖紙、航海路線、海戰實錄、番邦地理,無論劉大夏是将“鄭和海圖”燒掉了還是藏起來了,此舉無疑是将大明無數代人的心血付之一炬,大明朝在航海、海戰以及造船領域直接“一夜回到解放前”,落後百年不止,中國航海技術、海戰思想、造船技術出現了斷層,劉大夏作為“片闆不得下海”的推動者毫無疑問在這件事上是有罪的,失去了大量航海技術和發展的中國毫無疑問在後期的一系列列強入侵中失去了自己的護盾,而劉大夏雖然是大明一代忠直之臣,即使他的出發點是好的,蛋撻液仍然難逃“華夏罪人”之名。
參考資料:
《灼艾餘集》、《兵部尚書劉公大夏傳》、《殊域周咨錄》、《明史·卷一百八十二·列傳第七十》、《大明武宗毅皇帝實錄·卷一百三十七》、《今獻備遺·卷三十一》、《國琛集·下卷》、《先進遺風·卷上》、《客座贅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