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司馬遷所著的《史記》是文史結合的典範之作,它不僅是一部偉大的紀傳體通史,也是一部傑出的傳記文學作品。魯迅先生即在《漢文學史綱要》中将司馬遷與司馬相如并舉稱“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充分肯定了司馬遷的文才。對于《史記》這一偉大著作,魯迅更是稱贊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稱贊的是作為史書的《史記》,“無韻之離騷”稱贊的則是作為文學作品的《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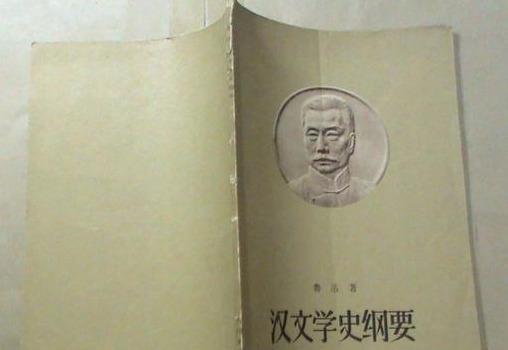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魏公子列傳》是七十列傳中最為精彩的篇章之一,明朝學者茅坤曾這樣感歎道: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傳亦太史公得意文。本文即從這篇“得意文”入手,通過分析其叙事方法,看司馬遷是如何塑造信陵君這位“胸中得意人”的。
《魏公子列傳》與其他三傳最直覺的差別在對傳主的稱謂上,其它三傳都以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稱呼傳主,唯獨《魏公子列傳》通篇都以“公子”稱呼信陵君。由此,不難看出司馬遷對信陵君的偏愛。此外,在《魏公子列傳》中,司馬遷還通過與魏國國運緊密結合的叙事結構、互見法及襯托法等叙事技巧,塑造出了一位近乎完美的理想戰國公子。
司馬遷蠟像
一、《魏公子列傳》的叙事結構
信陵君和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一樣,都是以“養士”而聞名于諸侯,《魏公子列傳》也和其他三傳一樣都是以“養士”為主題的。主題雖同,但《魏公子列傳》的叙事結構較其他三傳有明顯不同。
在《魏公子列傳》的開篇,司馬遷先是交代了信陵君“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的養士态度,随後便将其與魏國國運聯系在了一起: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公子無忌禮賢下士
《孟嘗君列傳》稱孟嘗君“傾天下之士”,《平原君虞卿列傳》稱平原君“傾以待士”,《春申君列傳》稱春申君“方争下士,招緻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平原春申二君之語其實是共稱四公子),他們雖也像信陵君一樣養士,但在叙述之時司馬遷并未将他們的行為與國運結合在一起。
信陵君竊符救趙後,心知魏王不會寬恕自己,便令将領帶兵回到了魏國,而自己和門客則留在了趙國。此時,司馬遷又将信陵君和魏國的國運聯系在了一起: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信陵君在毛公和薛公的勸說之下駕歸救魏,魏王授之以上将軍印。随後魏國之難被解,史載: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
之後魏王中了秦國的離間計,信陵君被免将位後謝病不朝,最終病酒而卒。秦國得知信陵君逝世,當即“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由此可見,信陵君的死即意味着魏國的衰亡。
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之是以将信陵君和魏國國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并非單純為了突出信陵君的個人影響力,還為突出信陵君之養士是為了大義及國家利益。而在信陵君奔趙及歸魏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侯嬴、朱亥、薛公、毛公,他們皆是站在大義及國家利益的角度為信陵君獻策。
二、《魏公子列傳》的叙事手法
(1)互見法
互見法是司馬遷首創的一種叙事手法,這種手法的産生跟紀傳體的體例密切相關。在編年體例中,每個事件都隻在時間線内出現一次,但在紀傳體例中同一個事件卻可能出現在多篇傳記中,是以司馬遷便創造了“此詳彼略,互為補充”的互見法。在具體運用時,互見法還受作者主觀意圖的幹預,比如四公子傳以“養士”為主題,一些跟此主題無關的事件則被放到了他傳之中。
《魏公子列傳》中的信陵君近乎完美,他雖有也有遇事不決的時候,不過很快就在門客的勸說之下采取了最為正确的做法。但事實上,信陵君曾因遇事不決直接導緻了魏國相國魏齊的死亡,不過此事并未記載在《魏公子列傳》中。
《範睢蔡澤列傳》載:(魏齊)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刭。說的是魏齊想要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因為害怕得罪秦國而猶豫不決不肯接見魏齊,魏齊得知這個情況後一怒之下吻頸自殺。這樣的事件出現在《魏公子列傳》中無疑有損信陵君的理想形象,但如果不表明将其記載下來又有為史家“不虛美,不隐惡”的實錄精神,是以司馬遷便采用互見法将之放到了他傳之中。
此外,平原君因貪圖小利而使趙國陷入長平之戰的事件亦放到了《白起王翦列傳》中。不過,《平原君列傳》的結尾,司馬遷還是提及了此事。
平原君畫像
(2)襯托法
襯托法是一種古已有之的修辭手法,在叙事類作品中亦可視為叙事手法,其分為正襯和反襯,《魏公子列傳》中主要使用的是反襯。在《魏公子列傳》中,司馬遷先是以魏王反襯信陵君,後又以平原君反襯信陵君。
《魏公子列傳》載:
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複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複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
說的是信陵君和魏王在下棋之時聽到趙國來襲的消息,魏王惶恐不安,而信陵君則氣定神閑泰然自若,因為早有密探将趙王的動向告知信陵君。此處表面以魏王之“恐”反襯信陵君之鎮定,實則以魏王之平庸反襯信陵君之非凡。
信陵君下棋影視形象
此外,司馬遷還通過平原君對薛公、毛公的不屑反襯信陵君之識才與愛才。薛公和毛公為趙國境内的隐士,賓客數千人的平原君不僅對他們一無所知,在得知信陵君與他們一同出遊後還笑話信陵君為“妄人”。由此不難看出,平原君并沒有識才的眼光,其養士隻不過是裝點門面,而信陵君則有識才的眼光,亦是真心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