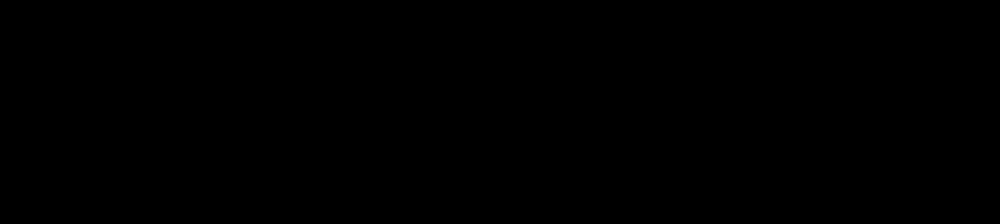
近些年,想了解世界上發生的事,“身份政治”是繞不過去的議題之一。小到日常生活中的困惑,或看電影時引起思考的某個橋段,大到新聞裡聽到的那些流血的沖突、碰撞,都可能與人們對尊重與認同的追求有關。今天分享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教授任劍濤和媒體人陳迪關于弗朗西斯·福山新書《身份政治:對尊嚴與認同的渴求》的對談視訊及文字精選,在對談中,他們深度讨論了身份政治議題的關鍵概念以及如何把這個概念與我們當下社會的結合起來加以了解。
點選觀看👆《身份政治》對談視訊上期
中國在解決饑餓、貧困、走向小康的時候,也要步入一個後物質主義的狀态,我們也要面對怎麼來應付人的尊嚴和承認的問題。
激情對于我們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承認人在其本質上并不見得是都可以理性計算的動物,而是被激情所主導。我們多少東西都是受激情主導的,我們的激情究竟主要投向哪個方向?這個實際上就是身份政治的問題。
今天西方的身份政治說到底,是因為主流政治受到重大挑戰,或者說主流政治對自己的自洽的言說建立不起來,或者沒有廣泛的認同,公民政治相對于身份政治來說比較蒼白。
我們在面對所有社會沖突的時候會意識到“和”比沖突、比沖突到底是更适宜的選擇,中國古代也有這種智慧,叫做“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任劍濤
今天我們為什麼要關注⌈身份政治⌋?
嘉賓:任劍濤 陳迪
01. 後物質主義的時代
怎麼應付人的尊嚴和承認的問題?
陳迪:今天我們要談論的是這本《身份政治:對尊嚴與認同的渴求》,來自一個大家,如果對社科領域感興趣的朋友一定都是繞不過的名字,也就是弗朗西斯·福山。我們對福山的了解都得回到三十年前,也就是他的一篇論文以及一部作品,1989年的《曆史的終結?》,這是他當初的一篇論文,他在三年以後把這篇論文續寫成一本完整的作品《曆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也正是“曆史的終結”這個修辭奠定他在冷戰以後的思想界裡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繞過去的地位。他在之後的三十年時間裡,可以說某種程度上不斷重複自己,但是也依然會非常成功,它對于當代世界、對于今天的觀念世界來說就是這樣一個人物。
《身份政治:對尊嚴與認同的渴求》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劉芳 譯
任劍濤:現代活動一般被認為是追求物的活動,是以今天發展、财富配置設定,我得失多少,都成為核心問題。但是這樣常常使我們忽視人生活的另一面,作為一個人,不是吃飽喝足就行了,不是家有萬貫之财就行了。我是誰、我屬于哪個群體、我和我的群體有沒有受到尊重,别人怎麼看我們,我是處于社會的什麼階層,我在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我在這個國家裡有沒有我的位置,這一系列東西非常關鍵。尤其關鍵的是,我在與他人相處的時候,他人對我是不是夠尊重,我自己做人有沒有尊嚴,是不是總是覺得我屬于社會最底層的一部分而受别人的蔑視。是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人的社會性需求可能是近代以來,1500年以來,尤其是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以來,我們把人打扮成經濟動物以後,對人作為社會動物和作為有人性尊嚴的進階動物的認識就顯得非常單薄。
福山在這方面可以說非常非常敏銳,作為一個世界最前沿的學者,他是緊貼1980年代後期人類政治生活的巨變來展開他的論述,不僅僅是提到的《曆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這部作品,所謂“曆史的終結”就是對曆史的前途沒什麼争論,這是他特别強調的。因為很多人對這本書望文生義:曆史怎麼可能終結?2021年之後難道不是2022年嗎?2021年之前難道不是2020年嗎?我們都是一種自然時間序列的曆史觀,其實福山強調的是蘇東的倒台,首先我們要認識到對曆史沒什麼好争論的,不再是自然時間有意義,而是自由民主才是最有意義的,他終結了你們曆史上的努力,到這裡為止,你就發現了曆史的目标。
随着20世紀末到新世紀初,東西态勢的微調,尤其中國的崛起以後,福山發現現代政治秩序的問題複雜化了,中間他篇幅最大、影響當代也很大的兩部書,理想國翻譯成漢語出版了,一本是《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史前一直考察到法國大革命;第二本是《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這裡已經談到身份政治要處理的主題,但是因為當時identity politics還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美國還沒有出現太多的安提法運動。但是這兩部書裡,福山已經發現一個新部落政治的資訊,或者庇護主義的資訊,這個非常重要。這兩部書一千多頁,是為現代政治秩序背書的最重要的兩部作品,可惜在我們漢語世界裡還沒有引起充分的重視,一定要有這兩部書作為鋪墊,然後才到我們桌面上這本書。
福山一開始就向我們介紹為什麼寫這部書,兩個重要的契機:一個是美國的總統選舉。當然往前推就是2016年,特朗普作為一個政治素人突然當了總統。從物的滿足度來說,他已經有40多億美金的個人财富,按照原來的身份的說法,物的條件這麼充分了,為什麼他不滿足,而去争取當總統?說到底總統對美國來說,對世界來說,都是一呼百應,跺一腳全球震動的位置。但這是一個驚人之變。另外就是,本來運作好的歐盟,大家都抱有信心,民主國家不行了,範圍太狹窄,而且互相的民主國家的戰争也太殘酷,全球治理問題這麼重要,是以歐盟給我們示範了,國家組織起來,我們有超國家組織,前途光明,信心滿滿。結果英國脫歐了。
2020年的選舉,推四年,2016年的選舉,再到英國脫歐的過程,使得這個世界真是變到福山要重新認識的地步。而重新認識的一個切入口是什麼?其實就是身份問題。是以這部著作是非常有來曆、非常貼近現實的。不僅非常貼近美國政治變化的現實,而且非常貼近中國政治變化的現實,随着中國人對物化生活的基本解決,大家物質條件沒有問題了。但是,我是底層人嗎?比如我在城市裡是農民工,我怎麼一直不受到城市人的尊重,我已經祖孫三代在這裡給你們打工,我沒有受到尊重,但我難道不需要追求尊重嗎?我對這個社會沒有抗拒感嗎?我人性的尊嚴在哪裡?誰為我說話,我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意義又如何寄托?
是以我們非常感謝理論觸覺如此敏銳的福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審查世界政治局勢和自己局勢的一個觀察視窗。
任劍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身份政治的興起跟後物質主義是有關的。你滿眼都是物欲的東西,現在有房有車,存款百萬,覺得生活已經非常美好的,但是我覺得我在這裡非常孤單,人家也不尊重我。你有房有車,美國人大多數家庭都有房有車;你有一台車,人家有兩台車;你掙一百萬,人家馬斯克有幾千億。物質主義的相對标準讓我也還是得不到尊重,而我到伊斯蘭國去,這樣使得我的新的身份認同,有了物質以外的強大的刺激。
因而在一個國内充分流動,以至于全球充分流動,又進入後物質主義新階段的時候,身份政治應該是帶來最複雜的難以解決的政治僵局,今天也是全球範圍内都在窮于應付。沒有獲得承認和尊重的東西,很容易造成這個社會的反抗行動,是以為什麼這個社會撕裂,為什麼黑人的BLM運動和安提法運動,在一個和平甯靜的法制社會裡會做出暴力性的行為,他隻有在暴力性的行為裡才覺得我們這些群體的互相認同凸顯出來,我的價值才得到承認。
是以身份政治比之于一般意義上的自由民主政治對于人的安全保護,這是非常低級趣味的東西,我的自尊、我的自主、我的價值得到了承認和尊重,這個刺激很大。是以在可觀察的範圍内來講,身份政治還将帶給人類一個不短時期的重大困擾。在這個意義上,福山的選題是非常重大的。别看他是美國的作者,他主要從美國和英國的處境出發讨論問題,好像跟我們隔了幾層皮。實際上要搞清楚,中國在解決饑餓、貧困、走向小康的時候,也要步入一個後物質主義的狀态,我們也要面對怎麼來應付人的尊嚴和承認的問題。因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感謝福山,他讓我們中國人提前由他來給我們進行理論準備,是以讀者有興趣讀一讀就會覺得,這怎麼好像在說我們一樣的,有這樣一種切近感。
02. 平等激情vs優越激情
内在自我與外在自我的分裂
陳迪:我們今天在中文環境裡,如果說到身份政治的時候,一般的讀者、網際網路使用者,他們通常會有至少兩種反應:一種,這是一個西方的事情,就好像不是中國的、不是東方的、不是開發中國家、不是第三世界需要去擔心的事情,另外一個反應,談論身份政治,特别是涉及到身份政治裡面的包括進步主義思潮的訴求,也會被了解為是西方人矯情,才會搞出這麼多幺蛾子。
但是實際上福山在這本書裡提供的思路不是這樣的,要找理論溯源的話,他是從蘇格拉底開始的。他在第二章談論,人的靈魂有三個部分,這三個部分是怎麼樣的,他舉了一個例子,好像一個人,一個酒鬼看到一瓶酒在桌面上,他很想去喝它,這時候就是他靈魂裡面的欲望部分在發生作用。但他知道喝這個東西傷身,是以他要拒絕它,這時候是他靈魂裡面的理性在發揮作用,這是靈魂的第二部分。但是他最後還是抵禦不住他的欲望,然後他喝了下去。喝下去以後,他就開始大罵自己,你怎麼那麼沒用、那麼沒出息,居然抵抗不了自己的欲望,這部分是什麼?這一部分蘇格拉底把它定義為激情,這就是靈魂裡面的三個部分。
福山從蘇格拉底開始,沿着他一直以來非常喜歡的黑格爾的史觀,黑格爾史觀一個非常中心的點是,他認為人類曆史核心的驅動力其實就是關于尋求、承認的鬥争,如果他跟别人不平等,他要尋求平等;如果他已經站在跟周圍人都平等的位置上,他要追求卓越,要追求優越,要追求高人一等、出類拔萃,這部分就是激情。這是福山概括的在靈魂的三要素裡面,激情一直在發生作用。
任劍濤:對人來講,我們生活首先是有欲望的,沒有欲望可能我們對外部世界,甚至對我們人自身都覺得無所謂了,是以價值和意義喪失掉,是以不要單純以為欲望是負面東西。但是我們知道現代的經濟和政治,基本上就是把人當做欲望的動物,是以有一種歸納,人的政治實際上是欲望政治,尤其滿足我們對物的那種欲求的欲望。但是我們又會去計算,滿足我們這種欲望所付出的代價,因而我們就會有理性。理性說到底就是對得失計算的結果,鄙俗一點說就是如此,到底我做這件值不值得,如果不值得,要付出什麼代價。像我們剛才說飲酒,酒鬼飲酒,賭徒搞賭博,到最後還是忍受不住這個刺激,一喝,喝醉了,我就埋怨自己,埋怨完之後也可能有另外一個感覺,喝酒醉了還是真爽,這都是他的激情。激情對于我們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承認人在其本質上并不見得是都可以理性計算的動物,而是被激情所主導。我們多少東西都是受激情主導的,我們的激情究竟主要投向哪個方向?這個實際上就是身份政治的問題。
是以在觀察身份政治的時候,福山講他的思想史的來源非常悠久。但是作為一個現代政治概念來講,身份政治是随着資本主義興起的現代現象。因為現代資本主義興起之後,它把我們生活的多個剖面分别切開觀察,123、ABC、甲乙丙,這就使得我們人不得不去把我們當做一個瑣碎的對象、碎片化的存在來打量,打量之後使得人的欲望、理性和激情互相鬥争,這個互相鬥争怎麼去統納它?這就有一個觀念史。其中他覺得最重要的觀念人物,在他的勾畫脈絡裡兩個人非常關鍵,其中一個就是你提到的,福山重寫《曆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他特别強調的,談論人類絕對精神發展,到最後人發現自身,而曆史終結的,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黑格爾強調承認。
而真正起源是在哪裡?是對德國古典哲學整個發生重大影響的法國思想家盧梭,而盧梭最重要的是在現代原身時期發現一個觀念,就是人有兩種自我,一個是外在的自我,比如今天我們倆坐在這裡,你是媒體人,我是教書匠,我們這個叫社會自我,是我們謀生的一個身份。但我小的時候立志想當總統,那個總統可能才是内在的自我,是我想追求的。因而内在的自我和外在的自我之間,他認為是分裂的。
我這個人,哪怕我是藍領勞工,藍領勞工就應該支援民主黨,結果有60%的藍領勞工投票給特朗普,大家說這個藍領勞工都有病,支援一個對你并不友好的總統候選人,你這是何必?可能藍領勞工大部分認為,你不要以為我現在是藍領勞工,實際上我靈魂深處覺得我是一個國家精英,我是一個國家棟梁,是以我支援特朗普的原因是,特朗普出來表現多麼自我,我實作内在自我可以在特朗普身上看到希望,我是非常自覺自願地把票投給他。
是以在盧梭這裡很簡單,實際上身份政治會導緻一個人認知的支離破碎,我們在趨向一個内在自我的情況下,可以抛棄我的外在自我身份。是以選舉政治裡頭,一般的政治科學分析在這方面非常蒼白,因為他投票了,一投票,一統計,你赢了,這個說起來真沒勁,你赢了不赢了算什麼,最關鍵是你這個總統候選人刺激了我追求内在自我的萬丈熱情。
是以這個意義上來說,這部觀念史一定是現代觀念史,是以福山的分析有時候刺激我們去思考,在社會的表面現象去看到背後更強大的精神動力。尤其對中國人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在解決物質主義之後,基本上沉浸于在手機終端上看破碎的微信,幾句話一看,啊,我了解了生活。實際上你發現,生活離你越來越遠,内在的自我與外在自我完全切割掉。是以這時候你讀一讀福山就會發現,其實作代生活還是推動我們去想象那背後的東西,去求解背後的東西,不像我們一談到“身份政治”四個字就本能厭惡,說身份政治這個東西糟糕,給這個社會帶來動蕩,都是你這個膚淺的身份追求。不是,身份追求背後其實有很深層的社會動機和精神動機。
陳迪:在福山這部作品裡面,他從蘇格拉底開始,接下來帶出來的人物就是馬丁·路德,接下來就是讓-雅克.盧梭。馬丁·路德在身份政治這個思路裡的位置在于,他可能就是最早的去暗示人具有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的張力,而到了盧梭的時候,這種張力被清晰化,這個社會身份可以了解為是我們實際上得到的東西,實際上得到的尊嚴,因為我們的尊嚴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靠外在的社會環境的承認支撐起來的。但是我們人又會有非常躁動不安的内心,我們都對自己有某種期許,認為我們值得在世界上擁有某一個位置,但是這個位置往往跟你的外在身份沒有辦法完全吻合,是以就會出現持之以恒的不妥協,不安定、不穩定。但這種所謂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的分裂,也并不是說在人類文明史裡一直都存在的,到底是什麼東西激發這種分裂的出現?
任劍濤:福山提到一個比較有趣的思想史轉向,當然他也承認這個轉向代表人物已經不像一百年前一聽就如雷貫耳,誰?就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有關于人的“我”的概念的三重設想,就是本我、自我、超我。本我、自我、超我在古典社會裡為什麼不像在現代社會裡影響如此巨大?以至于我們現在分析身份政治勃興之際,還要重新啟用一個已經不是很時髦的思想家的概念?其實就涉及到你這個問題,什麼時候本我、自我、超我分離到我們人不得不去重視它。
首先人早期對本我是什麼東西根本不清楚,原因在于沒有心理分析、沒有現代科學推動,人們對于本我,其實大多數統和到一個大我,就是超我面前、社會的我面前追求我的自我目标,就把本我掩蓋了。但是社會大我對于自我的壓抑,常常使人們要去尋求本能的滿足,比如吃喝拉撒,為什麼我們有時候會以暴飲暴食解除自己的緊張,其實這就是誘導你的原欲,而那些原欲在弗洛伊德的解釋裡就是性的問題。
人說到底,就是在性的活動當中得到類的延續,任意一個個體都是性活動的結果。但是社會的自我和超我的表面上的繁榮和大家去趨而同之的追求,常常把這個本我壓抑的夠厲害,在工業社會以前可能大家不會覺得這有什麼問題,但是工業社會以後導緻大流動,大流動之後就有我們在認識本我當中的一些壓抑性力量的加強。
是以這個時候大家的體驗就開始高度具有張力,人們逐漸意識到,我這個人,從我的本人到我個人的目标,到這個社會需要我做成什麼樣,給你切割開來,這時候就變成非常具有沖突的一種場景。一有沖突的場景,大家就意識到,我在這個社會裡,究竟要追求一種什麼樣的生活?本我、自我、超我之間這種高度緊張,這種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實際上它一直若隐若現存在我們現場。盡管在理論上來說,精神分析學派現在已經很不時髦,但其實經過六八年思想解放運動,西方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他們一個張力的傳遞,比如“三馬”,其中一馬(馬爾庫塞)就到了福山所在的美國社會,其實作在身份政治的一個爆發性的後果,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六八之子”,六八的溫馨産兒。
他們覺得首先要幹啥?我們要以本能來造這個社會的反,這裡你若隐若現知道了,福山談到身份政治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面向就是LGBTQ,逐漸成為一個潮流。其實在68年以前有沒有LGBTQ?也有,但是他們基本上被自我和超我嚴格壓制在社會的亞文化群體層面。
到了1968過後,随着工業文明的高度成熟和發展,後工業文明來了之後,人們對于身份的具體裂變已經不回避了。這就是福山談到的激情的兩種形式,第一步要求有平等的激情,我LGBTQ不覺得比你矮一等。我第一次到洛杉矶通路的時候,在洛杉矶街頭就見到,兩個男性、兩個女性相擁而吻,如此的忘情,我當時覺得簡直不可了解。其實作在回想起來,我們對現代社會的體驗實在是太膚淺,以至于不知道這個社會釋放出來的各個群落的生活、他們的狀态,跟我們所臆想的那個簡單化的狀态完全不一樣。
但問題在于,這些亞文化群體在争取到平等表現激情的時候不滿足。因為對這個社會來說,激情有兩種,第一,你得承認我,我跟你一樣,都有同樣的人權承諾,你有什麼樣的異性情感,我有什麼樣的同性情感,我們都是平等的。平等的最後發現另一種激情開始發作,什麼激情?優越激情。我LGBTQ為什麼比你的異性戀差?這是開玩笑,你才是承受到社會世俗的壓力,完全以超我來壓制你的自我和本我,我們LGBTQ才是釋放自我和超我,因而掙脫這個社會的大我對于自我和本我的限制。是以一旦有優越激情的時候,我們知道身份政治在LGBTQ這樣一些亞文化群體開始上升到社會主流群體,上升到社會主流文化,它要發揮引導性價值。
我們知道安提法(Antifa,直譯為“反對法西斯”),起碼從脈絡上來講,它是秉承二戰反法西斯傳統。,一直綿延到現在使美國青年人造反,這倆有什麼樣的精神脈絡?實際上都是在追求平等激情和優越激情,而引導社會小群體的抗拒或者是反抗文化,而導緻對主流的一種結構。是以今天西方的身份政治說到底,是因為主流政治受到重大挑戰,或者說主流政治對自己的自洽的言說建立不起來,或者沒有廣泛的認同,公民政治相對于身份政治來說比較蒼白。
今天西方主流的政治論述是對1968因為物質主義配置設定不公平而導緻的,或者社會控制的不公平而導緻的反抗運動的回應,最明顯的就是1971年美國人羅爾斯出版《正義論》,對福利社會做出反應。直到今天中國人談共同富裕,實際上還是處理别人1971年的問題,還是物質主義的問題,是以對中國來說為什麼身份政治顯得比較奢侈?覺得跟我無關,那就錯了。實際上物質主義的配置設定到最後,大家感覺到你給我配置設定這麼多物質有什麼鬼用,你不尊重我,我現在要的是尊重。
03. 如何免除身份政治帶來的分裂?
陳迪:回到福山作品的脈絡裡面,他當年聲名鵲起的作品《曆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曆史的終結”的表述是The end of history,The end在英文裡面它既可以是中文裡面終結的意思,也可以是目标、目的的意思,是以他在為自己當年這個斷言進行辯護的時候強調的是後面這層意思,人類進行這麼多争鬥、進行這麼多努力、社會變遷,它的目的是什麼?可能是為了尋找一種平衡狀态,為了找到一種可以讓大家都消停下來的社會安排,他認為,至少在當年他認為在自由民主的架構裡面找到這個答案,可是為什麼自由民主就可以讓人類消停下來的選項?回到他在這部作品裡面以及在他其它的作品裡面一以貫之的脈絡,依然是黑格爾的史觀,人類曆史發展的脈絡就是尋求承認與尊重,這是一個根本的驅動力。
也就是說,福山認為在自由民主的架構裡,所有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真的是“王侯将相甯有種乎”,無論是總統,還是一個藍領勞工,還是一個失業在家拿食品券的失業者,大家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一人一票,我們在政治上的份量是一樣的,是以他認為這至少提供一種可以讓大家在尊嚴鬥争、在尋求承認的永無止境的煉獄裡面找到可能相對和平的、安全的、穩定的狀态。但是,回到這部書,雖然他口頭上沒有承認,但他其實已經在努力修正當年這個斷言,也就是說2010年代的世界已經讓他清晰看到,即便是自由民主,也沒有辦法讓人類找到停下來的狀态,原因就在于,我們尋求承認的這種激情會發生轉換。
在這部作品裡面,福山介紹人尋求承認的激情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譬如2000年前你是在希臘城邦的一個奴隸,或者羅馬時代的一個奴隸,像斯巴達克斯,他要尋求承認,他要尋求你承認我是一個人,跟你羅馬公民一樣,我們都是人格平等的,是以他就會起義,他就會反抗,他就會殺羅馬人。而當努力被承認為人以後,他會追求下一步,那就是要追求成為平等的人。你有貴族,有農奴,在歐洲封建時期,他們都是人,都是上帝面前平等的人,但是他們在社會人格的意義上不是平等的,貴族就是貴族,貴族才有榮譽,平民沒有榮譽,這一切就在啟蒙運動時期的自由民主革命時候,這就是他們最重要的主題,尋求平等的鬥争。
但是,到了自由民主、市場經濟階段,人們發現還是不會消停下來,人們要追求出類拔萃,要追求高人一等,要追求我比你更棒、我比你更進階,這時候怎麼辦?福山在當年認為市場經濟可能為人們追求卓越的欲望提供一個出口,但是在2018年看來,他顯然發現不是這樣。這可能是福山在2010年代的世界意識到的,即便是今天的社會方案,也就是我們談論大家的人格平等,談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們要給予大家在制度性上的一些硬性平等,有這麼一個基礎,可以讓大家獲得心靈的安定,好像是做不到的,因為人們一定會不斷地追求平等與追求優越裡面無縫的切換。
我記得他在作品裡面同樣也提到,民族主義同樣是一種身份政治的形式,同樣是一種尊嚴政治的形式。也就是即便以民族國家為主體,他們追求在國際舞台上的承認、尊重,說國家尊嚴是寸步不讓的,不惜代價要維護民族國家的尊嚴,這其實是非常典型的身份政治的話語。但是民族國家尋求在世界民族之林裡面的平等就到了嗎?曆史經驗告訴我們不是的,國家獲得承認、獲得平等以後,可能第二天晚上就會開始追求自己的卓越、追求自己的優越,要是世界的中心,要是雅利安人,高人一等,這就是二十世紀初德國發生的事情。
是以在這種身份政治或者說在人類尊嚴的需求如果是我們永遠無法擺脫的情況下,我們能夠免除于這種激情給人類的命運帶來災難的潛力嗎?有這種可能性嗎?
任劍濤:這個當然可以稱為現代性難題,對于人類來講,在原始狀态下,沒有這麼多的緊張。在某種意義上,随着人類越來越向成熟的現代發展,需要的緊張的宣洩出口越來越多,而一個一個的宣洩出口到最後好像又歸于失敗。第一個出口就是經濟出口,大家有了錢,蛋糕做大了,大家多分一點,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高興。但是人進了後物質主義的狀态,哪怕産品極大豐富,到了馬克思所說的能夠按需配置設定,但是我不關心你分了多少,是以經濟出口成了問題。是以第二個出口又來了,按照福山的分析就是法制出口,我們搞一個依法治國、公民平權、選舉政治,但是這個出口是以一個主權國家為前提。
進入全球化時代,需要有法制出口之外的政治出口,政治出口就是處理民族國家間關系的問題,我們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可以說殖民地地區先後獨立成國家,好像我們解決了這些問題,我們預設各個民族國家起碼都在經濟上追求發展,法制上追求平等,是以政治上解決我們這個群體安頓的問題,隻要落實于民族國家,就可以達到福山在這個書裡提到的,在黑格爾之前的康德狀态,就是民族國家間的永久和平。
結果我們發現,民族主義導緻這個世界非常不安甯的後果,而且小國有大雄心,大國更要稱霸全世界,因而導緻各個民族對于自己作為民族身份認同的重大對立。比如在後民族國家時代到來的時候,結果發現民主國家的回流,整個民主國家回流到什麼狀況?回流到1648年以前,就是帝國狀态。其實追求帝國就要追求它在全球民族國家體系當中的支配地位,我們感到更光榮,作為一個帝國子民,我支配你們其它國家,我在你面前感覺到我高人一等。
是以這裡就是你剛才提到的非常重要的問題,黑格爾一直是福山思考所有問題的重要來源,而黑格爾當然在思考現代性的背景上提供的着力點,比他的先一輩康德重要得多。康德在現代性的德國表述上非常清晰,因而他是德國所謂的自由派、現代派。而黑格爾顯得非常複雜,黑格爾的承認實際上是有兩重承認:一重承認是主奴關系的承認,我做奴隸的,看你做主人的怎麼這麼好,你不僅支配所有的物質和榮譽,而且你還支配我。但是得到主人承認之後發現,這個承認好像沒有什麼意義。我們究竟需要一種什麼樣的承認?不是主奴關系颠倒的承認,因為這種颠倒的承認還沒有得到平等的承認。因而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裡講主奴關系承認的時候,有時候導緻社會群體之間的緊張,上下層關系的緊張。
到了法哲學原理的時候黑格爾談另一重承認,就是互相承認。我這個貴族也好,我這個平民也好,大家在法權上都是平等的。這實際上就是身份政治的第二個出口,就是法制出口,我們都權力平等了,你也公民我也公民,你也一票我也一票,是以直到今天有些自命有貴族意識的群體還覺得很惱火,怎麼一人一票?孔夫子就不能一人一票,至少要相當于五萬票,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是以要有相同的承認,這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可以進入一個掃尾性的問題,身份政治要處理的問題是怎麼樣能夠把多樣的身份相對統一起來,而這個相對統一起來的身份是大家都認可的。這個不僅僅是福山在《身份政治》裡讨論這個問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裡拉也在讨論這個問題,身份現在導緻我們這個社會這麼碎片化,個人僵持着自己一個身份就覺得無法協調,是以個人的本我、自我、超我在鬥争,群體之間的本我、自我、超我也在鬥争,這一鬥下去,整個社會隻有重新進入叢林狀态,那就是一種非政治的情形。
這個意義上,我們怎麼去克服身份認知,就變成讨論身份政治的互相承認的法權問題。我們能不能重建公民身份,這是大家都統一有的身份,變成解決身份政治導緻的分裂、沖突、對抗、流血,可能要去考慮的出路了。
04. 用「統和力的身份」來解決「分裂性的身份」
陳迪:剛剛任老師最後提到的這一點,我們要建立一種統一的公民身份,用來取代我們身上自然帶有的許多小身份,用這種方案來克服由于身份證是尊,或者人對尊嚴需求的這種結構性張力可能是一種出口,這也恰是福山作品最後一章提到的方案。某種程度上已經頗為近似于當年提出建設所謂的公民民族主義的方案,也就是說大家血緣不同、血脈不同,但如果大家對同樣一部憲法,對同樣的社會的公民的信條,大家有同樣信仰的話,就可以作為同一個民族國家的人。
但就我的一些個人感受,首先這個方案并不新穎,甚至在十九世紀已經是某種程度上的政治現實,畢竟十八世紀末有了法國革命、有了美國革命以後,這些國家從族裔的成分來說,本來就是相對多元的,身份也相對多元的,而他們在十九世紀的方案就是公民民族主義的方案,這個概念到了二十世紀才被理論化呈現出來。但即便有這樣的基礎,人人生而平等,對于美國來說,以他們這樣的立國标準來開始,他們依然沒有辦法避免我們在二十世紀、在二十一世紀看到的種種撕裂。
我有時候會擔心,我們談論這些問題的時候,比如這張桌子上的兩側,我們都可以有這樣一些身份标簽,這個是接受高等教育的,這個是在城市生活的,可以說中産階級,并且是男性,漢族人。是以在這些身份标簽的加持上,在我們所身處的這個房間,在整體社會環境裡,我們是處在相對來說比較舒适的狀态,我們的各種标簽都可以保證在主流話語體系裡,這些東西跟我們的身份是自洽的,是相容的。
但如果我們随便拿任何一個标簽出來,我們把它轉一下方向,比如說我,把男性屬性換成女性,這時候即便我們其它标簽保持不變,依然是知識分子,依然有這樣的社會經濟地位,可是你發現你出現在某些場景的時候,你的女性身份就會帶給你跟你作為男性完全不同的體驗,這種契機是不是會持續提醒你,讓你察覺到你的身份、你的自然的生物屬性賦予你的社會身份、社會屬性,它是不會繞過你的,無論我們采用書裡的最後一種方案,我們大家都遵守同一部憲法,我們有同樣的民族理想,要建設共同的社會,好像這些東西沒有辦法解決你身上不經意間冒出來的特定的這些小身份帶來的困擾。是以這種東西真的能夠停歇下來嗎?
任劍濤:我們考慮身份政治的問題,乃至于考慮一切政治的問題,可能要設定三重界限:第一就是對人類的天譴,我們不要考慮有一個最終的解決,如果有最終解決方案,它一定是希特勒式的,肉體上滅掉你,那就把所有問題都滅掉了。隻要人類存在,那就會有沖突。這個絕對界限,我們人類一定要做好心理準備。所謂通過解決身份政治的沖突解決一切沖突,不要抱這樣的幻想。
第二道門檻,我們所有的沖突存在,它總會以不同的形态在不同的變化,這是永遠如此的。但是永遠我們都可以緩解它。因為對于人來說,不斷出現新的情況,不斷解決新的問題,就是人類一代一代代際更替、社會變化的自然狀态,千百年來人類都是在這樣的沖突當中解決問題又面臨新的問題,這就是社會的一部曆史,我們既可以把它當作一部社會的進步史,或者當做社會的一般曆史,也不用對進步、退步做出評價。
第三,我們在面對所有社會沖突的時候會意識到“和”比沖突、比沖突到底是更适宜的選擇,中國古代也有這種智慧,叫做“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我們這個社會裡隻要有不同的個體就會有差異,有差異就會有沖突,有沖突就會有對立。對立,我是把對方滅掉嗎?不是,因為我們天生就是社會動物,是以我們去尋求解決沖突的途徑,相安無事可能就是我們能夠達到的最好目标。
是以對身份政治來講,我們一般應當把它放到第三道門檻上來考慮。為什麼福山這部書也好,或者他同代的思想家馬克·裡拉也好,他們都在呼籲要重新回到一個陳詞濫調的公民政治?其實公民政治給出的就是一個最大的公約數,因為所有人的身份差異引起我們激烈對抗的那些不同身份,到最後我們在一個政治共同體裡頭,唯一的身份完全是高度統一的,就是公民。公民不僅是政治身份,而且是有公民友愛的倫理基礎。我們都是人,我們得友愛相處。不要因為你是一個主流的異性戀,我是非主流的LGBTQ,我反抗你,我要成為主流,就像主奴關系的承認一樣,我一定要從奴隸變成主人才達到我的目标,其實這就是由怨恨上升到仇恨,非此即彼,要麼你戰勝我,要麼我徹底戰勝你,這樣不行。
是以盡管公民政治的回流,可以說是不太新的答案,但它是最大公約數的答案。而這裡的答案,實際上是要應對社會現象到底是終極性解決還是周期性解決的問題。美國所謂政治激化,它是一個周期性現象,人類通過一個周期的奮鬥,覺得應當滿足我所有追求的時候,這就是觸碰我們剛才說的終極解決的天花闆,根本不可能,三個出口,經濟的、政治的、法律的出口,其實都是一個出口而已,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的出口。是以這時候就會有怅然若失的感覺,然後有絕望的情緒出來,是以他就想對抗。
在這個社會大家都要追求(物質)的情況下,社會底層去看李嘉誠的時候,在八十年代就覺得他是社會底層奮鬥起來的典範,當這個身份分裂,前途沒有保證的時候,再看李嘉誠就是個奸商。但李嘉誠身份就是一個商人。身份政治牽扯到經濟發展、政策配置設定、法制環境、政治周期,李嘉誠還是那一個,但是對李嘉誠的評價發生重大的變化。
是以大家還是覺得,最初發現的那個所有人身份的最大公約數,它可能才是我們真實出路,大家平靜下來再去找到一個可以在身份之外都比較甯靜的追求自己人生目标的過程,這個就使得我們各種身份之間的緊張下降。
我相信這個可能,甚至于我們的某種時間周期也有關系,我們可以看大曆史,自十六世紀初進入現代以來,我們都可以看到,上半時期都比較緊張。我們現在處在疫情之中,我們馬上想到西班牙,上個世紀初也有疫情。這就是時間周期,它不一定是我們鐵定的規律,但它有某種暗合,總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在這個意義上,弗朗西斯福山的《身份政治》告訴我們,我們正處在一個可能讓我們感到比較難受的周期裡,但是這個時候我們怎麼看到緩解身份政治的緊張,不僅僅是福山和馬克·裡拉,像美國有眼光的政治學者們都在看到,要用更高的身份、更具有統和力的身份來解決分裂性的身份,用“一”來統“多”。中國人思考“一”和“多”的關系是最有智慧的,“一”包含“多”,“多”包含“一”,這個作為我們樸素辯證法。是以在這個意義上,當我們以統和的身份把分裂的身份略為緩解的情況下,我們就可以兜底。
福山是活靈活現地給我們表現了這個世界變化的節奏感、周期性當中,個人自身身份的緊張,但同時他也給我們指引兩種路向解決問題,如果你看福山覺得過瘾,建議你去看《曆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軟弱一點,看現實問題比較緊張,你就看福山所寫的科技發展帶來的緊張,他有一本專門的著作《我們的後人類未來》。是以在這個意義上,福山确确實實是當今世界當中最貼近社會政治生活經驗的最前沿,試圖給我們解釋問題的一個重要學者。
【推薦書目】
《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毛俊傑 譯
《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我們的後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黃立志 譯
👇《身份政治:對尊嚴與認同的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