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江柏拉圖學員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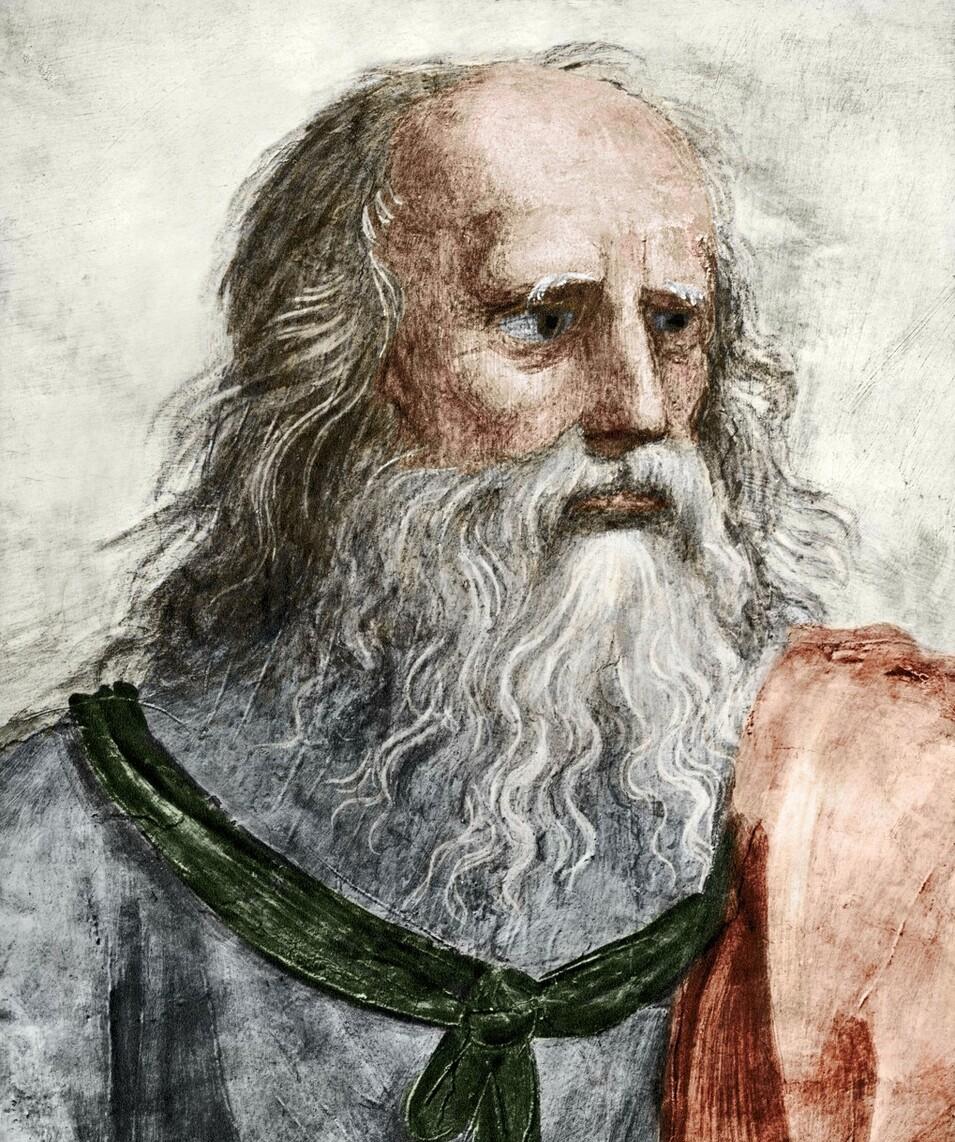
蘇格拉底和獄卒的對話
柏拉圖對話訓練三則
蘇格拉底和獄卒對話之一
虎嘉瑞
菲洞:我不得不再次稱贊我們那位朋友的勇氣,就在他交待完一切,那位叫做卡戎的獄卒遞上滿滿一杯苦芹汁的時候,我們那位朋友還不忘和送他最後一程那個好人打趣閑聊,以至于差點誤了時辰。
艾克格拉底:故事到了這裡,蘇格拉底将要離我們而去,我内心的悲傷本來就要溢出了,在這最為悲壯的時刻你卻又要逗我發笑,我們的朋友和那位好人都說了些什麼?
菲洞:那位本邦人卡戎遞上早已準備多時的苦芹汁,囑咐蘇格拉底一飲而盡不要剩下一點杯底,畢竟我們和他說了太多的話可能影響到了藥效。除此之外,那個人并未交待什麼,隻是靜靜地注視着蘇格拉底。這時,蘇格拉底卻按耐不住,犯了老毛病,他發話了。
蘇格拉底:卡戎啊!我的朋友,我見過的這麼多人中沒有誰比你的工作和名字更為相稱了,你的名字就像裁剪精良的衣服一樣,完全是為你量身定制的。就像神話講的那樣,你日複一日的擺着舟,引領人們穿越冥界到他們将要去也必将去的地方。人們說你是個堅啬的人,如果不含上那一枚銀錢作為擺渡費你是不肯讓他們上你的船的,我是不是要囑咐我的朋友提前給你交上一筆,你也知道,我是放不住一丁點錢的。不久的将來,當我奔到冥河之岸卻發現因為缺乏旅費而上不了船的時候那可就糟糕了。
卡戎:蘇格拉底,你可真是風趣。的确,這逼仄陰暗的獄室無異于我的小舟,我每天注視着形形色色的人們,陪伴他們度過人生最後一段曆程,擺動小舟帶他們到另一個世界去。但你可真是個怪人啊,在我見過的所有将死之人中隻有你是如此的鎮定,那些快要死去的人要麼絕望異常,眼中看不到一絲生命的光澤,他們知道自己必将死去而他們又無力再挽回什麼,隻是絕望的等待着死亡的來臨。還有一些人完全被死亡沖昏了頭腦,他們甚至比那些絕望的人還要懦弱,為欺騙自己,掩蓋絕望與恐懼,他們裝出一副泰然自若毫不畏懼的樣子,甚至一再的催促我送上鸩酒。可他們在獄室中踱來踱去的雙足,遊移不定的眼神,接過酒杯時微微發抖的雙手輕易的出賣了自己。還有一些人幹脆抱着他們的所愛痛哭流涕,他留戀這世間一切美好的事物,不願棄之而去。你和這些人是如此的不同,你可真是個怪人啊。我一定要抓住你,在你将要棄我們而去時好好的拷問一下你心中的秘密。
蘇格拉底:你這一番話無異是我聽過的最美的贊譽,就此,我也隻好老老實實的聽任你把我捆起來,任由你皮鞭一般的問題盡情地抽打,晚一點到我的主子那裡去了。
卡戎:好啊,蘇格拉底你說一個哲人期待死亡,唯有死亡才能讓他的靈魂徹徹底底的擺脫肉體的羁絆,完全進入不受幹擾的靈魂沉思态。隻要他活着,讓他不受肉體的幹擾孜孜探尋真理就是困難的,他仍需要不斷的克制自己的肉體,對嗎?
蘇格拉底:我想是這樣,卡戎。
卡戎:然而即便哲人深知他的未來屬于死後的明天他也不能自求死亡,因為他的一切屬于他的主子。就像你我知道的,如果我們飼養的一條柴犬因為塵世生活的苦厄而投河自盡,我們不會是以而感到震驚生氣嗎?就像我們的主子也不會因為我們太過期待于去那個世界以至于早早的自我了斷而感到開心,畢竟我們的全部是屬于他的,隻有他正式的召喚我們過去的時候我們才能應答對嗎?
蘇格拉底:當然是這樣!
卡戎:你之是以不懼死亡一來由于你知道定然靈魂是不死的,同時也定然存在着那樣一個亡靈的世界,我們死後都會到那裡去。二來你覺得時候到了,你的主子已經要喚你回去了,你不必為自己擅自尋死以至于死後你的主子大發雷霆而感到擔憂,是以你愉快的、輕松的去赴死,對嗎?
蘇格拉底:完全如此。
卡戎:蘇格拉底啊,我真為你的這番論述感到震驚,它是如此的漂亮完美以至差點把我的疑問完全遮擋。可我是個容不得瑕疵的人,即便面對如此完美的論證、面對一個将要去了的人我還是要指出我的困惑。正如我說,你的論證是完美的,我承認哲人的天職在于沉思,而虛僞無識的感官、欲念永遠也填不飽的肉體總會幹擾他,讓他不能專注于沉思,是以哲人努力擺脫肉體的幹擾努力尋求内在的沉思。我也承認有那麼一個我們的主子,也有一個不朽的靈魂,我們死後将會見到我們的主子,永永遠遠和他生活在一起,這些我都不否認。我所懷疑的并不是靈魂不死、以及為何哲人要去求死本身,令我不解的是它的前提——死亡是一個人自己的事情嗎?又或者說死亡僅僅是你和你的主子的事情嗎?
蘇格拉底:請原諒我的無知,你的問題是如此的嚴肅,以至于我的思維都被它凍僵住了,像塊粘在地上的石頭。那麼,能否請你把我凝固的思維再往前推上那麼一點?
卡戎:好吧,讓我再重述一下我的問題。就像我之前所說的,你是一個怪人,幾乎所有的人都懼怕死亡,因為它們相信死後就歸于虛無,死了就什麼也沒了,這點,我認為他們是無知的。但對于那些不舍所愛,抱着他們的戀人、孩子痛哭流涕的那些人的心情我确實可以了解,畢竟死亡代表着别離,死亡更不僅僅是我們的一己私事。
蘇格拉底:卡戎啊、卡戎,再想想你說過什麼?你說死亡是一種别離,但你之前卻承認有那麼一個死後的世界,而你卻不相信和我們的夫妻終将在這個世界相遇,這不是很不可思議的事嗎?
卡戎:你的思維真如嗅覺敏銳的獵犬,一下就發現了我的觀點中可疑的氣息。好吧,我們再想想看,你說靈魂是有來有去的,他們最初寓居在上屆,後來被主子指派到塵世履行苦差,到了時間主子将叫他們回去。我深信如此,大概是由于我時常陷于某個詭異的夢境,每當我進入沉睡我總是感到被送回了前世。在那,我在一個叫帕若戴斯的地方和前世的戀人愛若斯重逢。就好像我真的生活在這兩個世界一樣,我回想起前生的好多事,我和她曾分别于阿多尼斯節。正如你所說,那天我的主子喚我到他的跟前,他告訴我,我就要去遙遠的國度行差了。我問他,我的戀人呢?她是否跟我同行?主子告訴我她的時辰還未到來,她比我晚一日。他像你一樣安慰我,我們會在差旅中相見的。于是,我和我的戀人在天界的盡頭告别,我就在我的雙唇将要吻到她那姣好的面頰時,我的魂魄竟感覺猛地一沉繼之而來的是不斷的下墜,我昏了過去,也不知墜了多久。當我醒來時我發現自己被注入了一個醜陋的肉體,手腳也變得無比的沉重,再也不能像原來那樣輕快的飛翔了。随後,我便失去了所有的意識,在既往的數十年中我不斷的回憶曾經擁有的那些東西,好不容易才在靈魂的深處搜刮到一些支離的碎片,隻是支離的碎片而已。我向你說的這一切也隻有在夢境中才可窺見,唯有在夢境中才讓我知道在自己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就這樣在塵世徘徊,自從我在夢中回想起了前世的戀人,我就費盡心力的找尋她,可是我苦惱的發現我竟記不得她的長相,即便在夢中她是如此的真實與清晰。蘇格拉底,我全忘了,全都忘了。如今我已垂垂暮年,不再期待在塵世還能夠尋到她。我相信神沒有欺騙我,可世界這麼大,我怎麼能夠在異鄉再次和她重逢呢?或者即便我曾經和她擦肩而過,也不能夠回想起那是我曾經的摯愛了。蘇格拉底啊!正如我所說,你能确信回到上界以後我們還能和我們所愛的人在一起嗎?難道我們不會在寓居帕若戴斯的十億靈魂中和她失散嗎?又或者由于我們的失憶,即便萬幸能夠遇到她,也隻是把她認作路人擦肩而過了。戀人是如此,父母、兄弟、子女、朋友,對于我們的一切所愛不也是如此嗎?即便靈魂不死,死亡不也是一種訣别嗎?為了和我們的夫妻在一起,我們不是應該盡可能的規避死亡嗎?畢竟死後就不大可能再此尋到他們了,不是嗎?是以死亡不隻是我們的一己私事,也不僅僅是我們和主子的單方約定,不是嗎?如果我們早早的抛棄他們而逃走不是做了身為男人最最恥辱的事情當了逃兵嗎?
蘇格拉底:你說的沒錯,卡戎。但我并不認為死亡和誕生同樣會使我們失去記憶。想想看,你說你注入肉體時失卻了所有的記憶,難道這失憶不是由于肉體的幹擾嗎?那麼,有朝一日我們重歸故裡,擺脫了這沉重的肉體,失去的記憶難到不會重新回來嗎?我們和夫妻們不會在那裡再次相見嗎?你還會擔心找不到他嗎?是以,我們可以期待。就此,死亡不是究竟意義上的别離。
卡戎:好吧,蘇格拉底,你是善辯的。那讓我們再想想人這個動物本身?人這東西很奇怪,他既不像獵豹也不像老虎那樣獨處容不得任何同類,他更像螞蟻。自從人誕生那一刻起他過的就是一種群居的生活,就好像在天上神明已經為他設定好了角色。他被母幫所培養,也為母幫而戰,他接受母親的哺育,也哺育自己的子女,一代又一代生生而不息。但有一種人很奇怪,他們要麼整日的忙着和人論辯,并不從事任何實際的工作,要麼把論辯當作工作,以此收取酬金,他們中鮮有兼職的,他們的事業是沉思,這些人都是哲人。但是,這種人中的第一類更為人們所認肯,因為他們超脫世俗,專于沉思,凡是那些不是為思而思的人總讓人覺得不那麼幹脆。是以,哲人這個名号便代指那些熱愛思考的人,其中那些單純的為思而思的人,肯于擺脫世俗羁絆的孤獨沉思者更加的令人敬佩。你說是嗎?
蘇格拉底:如果你說,哲人是熱愛思考的人我大概會同意你的觀點,因為一位先哲曾說過:哲學就是愛智慧。這裡的愛正是指去愛,也就是去探尋它,而熱愛思考無疑正是熱愛去探尋智慧之源。
卡戎:好啊,蘇格拉底,接下來就奇怪的很了。哲人的天職是熱愛智慧,熱愛智慧就是熱愛探尋智慧,熱愛探尋智慧就是熱愛思考,這沒錯。但是這些哲人們呐,他們是全職的思考者,正如你說,哲人對物質的歡愉漠不關心,完全沒錯。也不隻是物質的歡愉,塵世的大多數瑣事都不在他們的思考範圍之内,塵世的繁雜事務大都會占用他們的精力和時間,以至于幹擾他們對智慧的探尋。于是他們是群體中的特殊的人,他們樂于在在内心中過着獨居的生活,即便身處人群之中。他們不關心衣食住行等的一切享樂,即便衣衫褴褛。他們不僅不關心自己的享樂,也不關心家人和朋友的物質生活。他們真和死了一樣,他們是塵世的人,卻又是極力擺脫塵俗生活的人。他們是群體中的人,卻又是獨居的人。哲人真是最奇怪的一些人,由于他們的孤獨,死亡就好像隻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一樣。這些智慧的人隻看到了自己,卻沒有看到自己身居的世界。對于他來說,死,隻是一個哲人死去了,這死也不是真真正正的終結。而對于他的母幫,它失去了一個優秀的公民,對于他的妻子,他失去了一個善良的丈夫,對于他的子女,他們失去了一個慈愛的父親。對于他的朋友們,他們失去了一個可愛的人。哲人可以輕易的死去,而他的家人卻要承受他所留下的無盡痛苦。哲人自己為可以早日的脫離苦戰而快樂,他的戰友們卻依然在戰場上煎熬,難道哲人不是最可鄙的逃兵嗎?人畢竟不是自己在塵世間戰鬥,他要逃走了,回家去了,難道隻是他一個人的事嗎?
蘇格拉底:卡戎啊,卡戎!我明白你所說的,可我就要歸去了,也許對于他們,哲人真的是有所虧欠的。但此時此刻我隻有和我的家人、朋友們真誠的道别。至于這一切孰對孰錯,或許隻有上蒼知道,祝願我們在那裡重逢。
卡戎:有位哲人說過,有些東西很奇怪,你不問則罷,我清楚得很,你一問我反倒迷惑不清了。他是在說時間,我想我們今天讨論的死亡也是這樣,有太多的未知物正在遠方等待着。死亡會使我們與夫妻分離嗎?死亡真的隻是我們自己的事情嗎?如果死亡不是我們自己的事情,輕易的赴死難道不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嗎?這些疑惑,也許真的隻有神明能夠為我們解答。我卡戎除了為亡靈擺舟,還辨識那些企圖混入陰間的凡夫,蘇格拉底啊,我判你不該死!
獄吏與蘇格拉底的對話之二
劉國棟
典獄官的仆人走進來站在他的旁邊說:“蘇格拉底啊,我決不會像對待别人那樣粗暴的的對待你。因為他們在我奉令叫他們服毒的時候總是發脾氣咒罵我,我這些時候從各方面看到你是這裡來的最高尚最和氣、最善良的人。現在我知道你的脾氣總是對着别人,不是對着我的。因為你知道我的使命。再見吧,請你盡量地完成對你的要求吧。”說完後,他淚如泉湧,轉身走出去了。
蘇格拉底:請留步,我看現在時間還早,太陽還在天上高高挂着,距離太陽下山還有很長時間呢,不如我們也找些問題來讨論一下,也算是你送我最後一程。怎麼樣?我想,人都應該是懼怕死亡的吧,死亡來臨的時候都應該是恐懼的,聽了我剛才和他們之間的對話,不知道你是不是仍然有什麼很疑惑的地方或者是對死亡仍心存恐懼,對靈魂與肉體的問題仍然感覺難以了解,心存疑惑。如果有什麼問題和疑惑就盡可能對我說出來吧,看看我能不替你解答這些疑惑。
獄吏:蘇格拉底,您說哲學家是追求死亡的,是終生都在聯系死亡準備死亡的。而我聽說,所謂的死亡在您那裡就是靈魂與肉體的分離。但我覺得靈魂與肉體分離實在是很難以想象的。
蘇格拉底:怎麼講?獄吏:我們平常思考問題時都是從我們看到的東西聽到的東西來思考的。比如當我們一開始學習的時候,或者說是剛認識事物的時候的樣子。例如:父母對我們說,這個東西叫桌子。然後我們根據我們的視覺看到的,我們知道了什麼是桌子,我們的聽覺也聽到了,原來這個東西就叫做桌子。我們同時也會對它有一個認識,認識到原來這種東西叫桌子。如果沒有視覺和聽覺,如果靈魂和肉體分離了,那又如何學習和思考呢?
蘇格拉底:那我來這樣問你好了。我先這樣問,蘇格拉底是什麼?
獄吏:蘇格拉底是一個喝了毒藥即将被處死的雅典哲學家。
蘇格拉底:很好,這是你對我的認識。那我再問,哲學家是什麼?
獄吏:哲學家是愛智慧的人。
蘇格拉底:人是什麼?
獄吏:人是有智慧可以直立行走的雙腳雙足的動物。
蘇格拉底:那什麼是動物呢?
獄吏:動物是能夠自己活動,自己吃東西,有生命力的物體。
蘇格拉底:那什麼是物體呢?
獄吏:物體應該是有長有寬有高的。
蘇格拉底:那什麼是長寬高呢?
獄吏:蘇格拉底,你問的這些問題和我們要讨論的問題有什麼關系麼?
蘇格拉底:好的,我不再問下去了。你有沒有覺得你回答我的問題的時候和你感覺聽覺所能得到的東西的關系越來越少呢?
獄吏:是的,是這樣的。
蘇格拉底:你是否覺得,我們讨論的東西如果繼續下去會與你平常所了解的看到的聽到的東西的關系越來越少呢?
獄吏:似乎是這樣的。
蘇格拉底:那好的,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
獄吏:你問吧。
蘇格拉底:你能告訴我,是,是什麼嗎?
獄吏:天哪,這個問題我還從沒遇到過,好像和我沒有什麼聯系的問題,我從來沒有被人這麼問過。我的确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了。
蘇格拉底:你看,肉體的感官現在還能為你提供思考的材料麼?你現在是不是隻能進入到純粹的思考之中,一種與感官沒有關系的思考之中了呢?
獄吏:看來是這樣的。好像那些東西對我都沒有什麼幫助了。
蘇格拉底:那你現在說說,你還認為靈魂的思考需要肉體的幫助麼?
獄吏:我想不需要了。沒有肉體,靈魂也可以單獨思考。
蘇格拉底:是這樣的。
獄吏:可是我現在是活着的。如果我死了那便是沒有了肉體,如果我死的時候,靈魂也就消失不見了,那麼,我的靈魂不也是不能單獨思考了麼?
蘇格拉底:好吧,那讓我來繼續回答你的問題。現在我再來問你幾個問題。
蘇格拉底:你認為動物有靈魂麼?
獄吏:靈魂應該隻是人的東西吧,動物怎麼可能有靈魂呢?
蘇格拉底:那我說人和動物的差別是人有靈魂而動物沒有靈魂你同意麼?
獄吏:我非常同意你的說法。
蘇格拉底:那是不是也就是說人之是以成為人是因為有靈魂呢?
獄吏:我覺得可以這麼說。
蘇格拉底:那你覺得肉體是不是被靈魂控制,是不是因為靈魂,肉體才成了人的肉體呢?
獄吏:可以這麼說。
蘇格拉底:那我來給你舉幾個例子你來考慮一下吧。
獄吏:好的。蘇格拉底:就拿他們前面提到的關于豎琴琴弦和和聲的問題吧。
獄吏:怎麼說?
蘇格拉底:你覺得琴弦如果斷了,是不是豎琴也就壞了,也就沒有辦法彈出美妙動聽的和聲了。
獄吏:這是當然。
蘇格拉底:那如果我們換一個和這個差不多的完好無損的豎琴,是不是能彈出同樣的和聲呢?
獄吏:應當是可以的。
蘇格拉底:那我是不是可以這麼說,那個和聲有确定的彈奏方式,不管如何換琴,那個和聲是能夠演奏出來的是麼?
獄吏:是的。蘇格拉底:是和聲的彈奏方式決定和聲能夠被演奏出來的麼?
獄吏:是這樣的。
蘇格拉底:也就是說,不管琴是不是壞的,那個和聲的彈奏方式一直在,是麼?獄吏:是這樣的。
蘇格拉底:好的。那我再問一個問題。你一定有鑰匙吧,例如,給我解開鐐铐的鑰匙。獄吏:這我當然有。
蘇格拉底:如果你的鑰匙壞了,是不是就不能開門了。獄吏:這是自然啊。
蘇格拉底:那我繼續問你。你的鑰匙是不是有特定的制作方式,因為這種制作方式,你才能解開犯人身上的鐐铐。
獄吏:沒錯,是這樣的。
蘇格拉底:如果你的鑰匙折斷了,你可以按照這種方式再造一把鑰匙。也就是說,你的鑰匙是否在并不對鑰匙能開門這件事起什麼決定作用。
獄吏:這樣看來,應該是這樣的。
蘇格拉底:也就是說,雖然你的鑰匙壞了,隻要你再按照那種制作方式重新制作一把就可以讓你的鑰匙繼續發揮作用了是麼?
蘇格拉底:好,那我們現在這樣來說。你是不是認為靈魂決定了人成為人。
蘇格拉底:那麼根據上面的例子,你是不是覺得,決定人成為人的形式隻要在,無論換掉一個什麼樣的肉體都不會使那個決定性的東西消失呢?就好像隻要鑰匙制作方式在那,隻要和聲的演奏方式在那,無論換什麼鑰匙,換什麼豎琴,都可以打開鐐铐和演奏出美妙的和聲呢?
獄吏:似乎你這麼一說,的确是這樣的。蘇格拉底:那是不是說,因為靈魂在那裡,無論換什麼肉體人都可以成為人呢?獄吏:是這樣的。
蘇格拉底:也就是說,靈魂決定了人成為人,推動人成為一個人是麼?
蘇格拉底:好的,我們繼續來談。你是不是認為一個東西要活動,要運動必須要有另一個東西推動呢?
蘇格拉底:你的推車會動是不是因為你的手在推他呢?
獄吏:一定是這樣的。
蘇格拉底:那你的收會動是不是因為你的身體讓你做出這樣的動作呢?
蘇格拉底:那你的身體動又是因為什麼呢?是不是因為你的靈魂讓你的身體做出這種動作?
獄吏:似乎是這樣的?
蘇格拉底:那你認為有什麼東西讓你的靈魂做出動作呢?
獄吏:似乎沒有了,好像沒有什麼東西會讓我的靈魂做出動作了。
蘇格拉底:是以說,你的靈魂是最初的推動者了?
蘇格拉底:那最初的推動者是不是沒有辦法被推動呢?
蘇格拉底:既然沒辦法被推動,他又在時時刻刻的運動,是不是說明,他是一直在運動的呢?因為不被推動卻又在運動的東西應該是自動的。能夠自動的東西就是一直在運動的咯?一直在運動的東西肯定是不朽的了,這個你同意麼?
獄吏:這個我完全同意。
蘇格拉底:那答案就很明顯了。既然一個自動的東西源源不斷的運動,那他肯定是不朽的了。靈魂就是這樣一個可以源源不斷運動的東西,那靈魂就是不朽的了。
獄吏:看來真的是這樣的,蘇格拉底,你似乎真的向我很清楚的解釋了靈魂不朽的原因了。
蘇格拉底與獄吏對話之三
王季玉
獄吏:蘇格拉底啊,你昨晚睡得好嗎?
蘇格拉底:我的好人啊,你又來和我說話了。我在這裡呆得很安心,自然睡得再好不過了。這裡沒有其他事來煩擾我,反倒可以好好思考。
獄吏:你真是這裡最高尚最善良的人了,即使快要離開我們了,仍然那麼平和。不過話說回來,蘇格拉底啊,你本可以不呆在這的。
蘇格拉底:雅典的人們雖然對我做了不公正的事情,但判定是合乎城邦法律的,我不能因為别人對我做了壞事就去做壞事啊。
獄 吏 你這樣說似乎也很對。
蘇格拉底:人終究是要死的,我已經活到七十歲了,現在雅典要我去死,是神要把我的靈魂召走罷了。
獄吏:蘇格拉底啊,那你覺得靈魂是什麼呢?
蘇格拉底:你要讓我來來定義靈魂,給它一個固有概念的話,我也說不清楚。我隻能告訴你什麼不是靈魂。靈魂是有别于我們周遭可感官的實體物質的,那麼可感官的,有實體的便必然不是靈魂。
獄吏:你是說像是思想精神一類的嗎?
蘇格拉底:是的。或者說他就是思想精神,是認知,是理性的。
獄吏:我相信這樣的靈魂的存在。不過老實說,蘇格拉底啊,我不認為靈魂離開肉體仍可以存在。
蘇格拉底:你是說靈魂會死是嗎?
獄吏:是的。我認為靈魂是依附于肉體而存在的,即使是思想認知,也是依靠腦細胞和神經系統得以存在的,如果人都死了,那靈魂也會随之消失了。
蘇格拉底:那你認為死後是怎樣的呢?
獄吏:哦,我沒法回答你這個問題,親愛的蘇格拉底。不僅是我,在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沒法回答你,因為我們都還活着,而這個問題隻有死後才知道。不過我想死就像是睡着了一樣吧,沒有知覺也沒有思考。從此世界與你無關了。
蘇格拉底:你說得很好。但你要怎麼解釋人的潛在認知呢?我的好人啊。當你還是小孩子時,有人告訴你那一個是杯子,于是你就知道了所有的杯子:有人告訴你那一個是凳子,于是你便知道了所有的凳子。這種類推是怎麼來的呢?難道這不是與生俱來的嗎?
獄吏:是與生俱來的吧。
蘇格拉底 :那麼也就是說我們本來就具有這種知識,隻是忘記了,而當有人告訴你一個是什麼的時候,你關于這種東西的記憶都醒來了,于是你便能認得這種東西了。這樣說你能接受嗎?
獄吏:就算是吧,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我們來到這個世界,身體是全新的,沒錯吧?
獄吏:沒錯。
蘇格拉底:既然身體是全新的,那麼身體不可能攜帶知識的,那就隻有靈魂了。獄 吏 似乎是這樣的。
蘇格拉底:我的好人啊,既然靈魂傳承着人們長期積累下來的經驗知識體系,那當然是一直存在的。也就是說,當肉體死亡以後,靈魂依然存在。
獄吏:可是蘇格拉底啊,就雅典而言,那現在的人口已經遠遠超出了以往的人口,這多出來的靈魂該從哪來呢?
蘇格拉底:我想你是太局促于個人了。這個靈魂是人類共有的思想認知,經驗積累,是具有公有性的,隻有當它實實在在落在某個肉體上的時候,才會具有個體性。
獄吏:你這樣解釋的話,我覺得是沒錯的,如果在之前那個從回憶習得知識的前提下。
蘇格拉底:聽你這樣說,你認為我們不是原先就有一個知識體系,我們不是從回憶原有的認知來重新獲得知識的,是嗎?
獄吏:是的,蘇格拉底,我不太認為我們是從已有的知識體系中重新習得知識。
蘇格拉底:那對于之前所說到的潛在的類推,你要怎麼解釋呢?請告訴我吧,我的好人。還有顔色,如果這種知識不是随人類共有的認知而來,你怎麼确定人們所說的綠色會是一種顔色呢?我的意思是說,當你指着樹問你的父母這是什麼顔色的時候,他們會告訴你那是綠色,但你是如何知道他們眼中的綠色和你的綠色是一個顔色呢,也許他們眼中的綠色是你眼中的其他顔色呢。
獄吏:會不會是這樣呢,蘇格拉底。我們不具有原有的知識,但我們具有類推認知的能力。比如說,你的父母告訴你那是杯子,然後你就會在自己的知識體系中設定一個概念,隻要滿足這個概念的那就可以劃分到杯子那一類去了。關于顔色,我也說不清楚,也許是要依靠感官來确認的吧。比如紅色黃色就比較溫暖,比較熱情,而藍色紫色就比較清冷。大家的顔色認知和感官感覺沒有什麼偏差的時候,大概就是說的一個顔色吧。不過也許我看到的世界和你看到的世界還真的不一樣呢,這可說不準啊。
蘇格拉底:和你說話真是件開心的事兒。你說得不錯。但是這個概念是怎麼定的呢。為什麼大家的概念都差不多呢?為什麼你定義的杯子在我的定義裡也是杯子呢?
獄吏:我也不清楚這是為什麼。這個也許就是人類的一些共性吧。
蘇格拉底:沒錯,總有些東西是共有的。也許這些共性就是人一直存在的靈魂。
江安柏拉圖學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