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未知生,焉知死。”哲學家李澤厚在世的時候總是談到孔子的這句話。他解讀了這樣兩個層面:一是要知道人“如何活”,即“人類如何可能”的問題,它涉及了吃飯穿衣、群體秩序等大大小小的方面,而“知生”有不止于這些世俗性的事務,由此即引出了第二個層面——形而上的“為什麼活”與“活得怎樣”。
李澤厚認為,哲學不同于知識,它不建造體系,甚至可以說是體系建構的對抗者,《周易》講“天下同歸而殊途”,中西各派的哲學有不同的路、不同的視角,但他們最終要歸到“人活着”這個命題上。有思考上帝的哲學,也有崇拜理性的哲學,對于今人時時感到的孤獨無依,他寫道:“人生有限,人都要死,無可皈依,無可歸宿,把愛、把心靈、把信仰付托于一個外在超越的符号,比較起來,似乎還順當。現在卻要自己在這個人生和世界去建立皈依、歸宿、信仰和終極關懷,即有限尋無限,于世間求不朽,這條道路豈不更困窘,更艱苦,更悲怆?”
但李澤厚的思想是以進取為基的,他偏愛魯迅,偏愛儒家所說的“知其不可而為之”,他說,“儒知空卻執有,一無所靠而奮力自強。深知人生的荒涼、虛幻、謬誤卻珍惜此生,投入世界,讓情感本體使虛無消失,是以雖心空萬物卻執着頑強,灑脫空靈卻進退有度。修身齊家,正心誠意,努力取得超越時間的心靈境界——這是否就是‘孔顔樂處’?”2020年疫情爆發後,他接受了人生中的最後一次采訪,再度談到“吃飯哲學”與“人活着”的緊要。中原標準時間11月2日21時,李澤厚在美國科羅拉多去世。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摘編了一篇他談“人活着”問題的文章,與讀者一起緬懷這位啟發了幾代人的思想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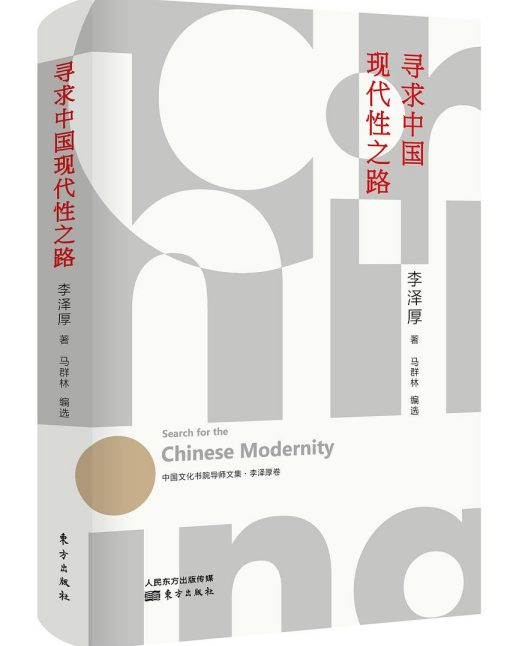
文 | 李澤厚
哲學本是精工細活,妙理玄言,如今卻作探尋劄記、粗糙提綱;分析哲學家必大搖其頭,形而上學者或悻然色變。但哲學既非職業,而乃思想,則常人皆可思想。此“想”不一定高玄妙遠、精密細緻,而可以是家常生活,甚至白日夢呓。哲學維護的隻是“想”的權利。
人一定要“想”嗎?人活着就有“想”。睡覺做夢,也還在“想”:在夢中吃飯做事,奮搏逃奔,離合悲歡。這不就是“想”嗎?“至人無夢”,這“至人”當是一念不生,一塵不想,免除和殺死一切想、夢的人?殺死之後,又仍活着,便如行屍走肉,不如真的自殺。
但并非每個人都會自殺。恰好相反,實際是每個人都在活着。活着就要吃飯穿衣,就有事務纏身,便被扔擲在這個世界中,衣食住行,與人共在,進而打交道,結恩怨,得因果,憂樂相侵,苦甜相擾。盡管你可以徹底排遣,精神解放,“境忘心自滅,心滅境無侵”,但這解放、排遣、“忘滅”本身,其是以必要和可能,不又仍然是人們努力“想”的結果嗎?
在世界而求超世界,在此有限的“活”中而求無限、永恒或不朽;或者,“打破砂鍋璺(問)到底”,去追尋“人活着”的(人生)道理、意義或命運;這種哲學或宗教課題,在“後現代”,或隻可看作庸人自擾?“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硬要思量這些本無解答的問題,幹什麼?真實的存在不就在個體自我的當下片刻嗎?其他一切都隻是空間化的公共語詞,不足以表述那自意識而又不可言說的“××”。與現代追求“反抗”“獨創”“個性”相反,這裡完全不需要這些。一切均已私有化、瞬間化,無本質,無深度,無創造,無意義。中世紀思考和崇拜上帝;啟蒙以來,思考和崇拜理性或自我;如今,一切均不崇拜,均不思考,隻需潇潇灑灑亦渾渾噩噩地打發着每個片刻,豈不甚好?遊戲人生足矣,又何必他求?用完就甩,活夠就死,别無可說,曆史終結。生活已成碎片,人已走到盡頭,于是隻一個“玩”字了得。這個世紀末正偶合“後現代”,不好玩嗎?
既然如此,也就可以有各種“玩”法。即使日暮無時,何妨強顔歡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絕望之為虛妄,正如希望相同。”明知無解,何妨重問?總有人要問人生意義這個本無可答的問題,畢竟人也有權利來問這問題,而哲學的可能性就在于人有權利叩問人生,探尋命運,來做出屬于自己的決定。于是,以“人活着”這一原始現象作出發點,便可以生發出三個問題:
1.曆史終結,人類何處去?人會如何活下去?
2.人生意義何在?人為什麼活?
3.歸宿何處?家在何方?人活得怎麼樣?
《周易》說:“天下同歸而殊途,一緻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蓋即此思此慮也。東西各學說各學派都為“人活着”而思而慮。雖“同歸”,卻“殊途”。“途”即是路,也是視角,這也就是哲學。哲學隻是路的探尋者,視角的選擇者。是“路”、是“視角”,便可能有某種全面性和“系統性”,而不是随感或雜談。但它卻不是程式、構架、“第一原理”。它沒有确定的規範、論證、文獻資料、科學規範、體系建構。哲學将是體系和建構體系的抗争者。對我個人來說,哲學探尋也許隻是“聊做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罷了。
上節結尾是“做無聊之事”,此節卻要“為天地立心”,有些滑稽。不過,以落寞心情做莊嚴事業,恰好是現代人生。說得更莊嚴也更好玩一點,這也正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儒學精神和它的悲劇。于是本“探尋錄”可能就是這種欲調侃而未能的滑稽劇。但今日的哲學已五光十色,五味俱全,如真能多出一種,豈不更好,抑又何妨?
今日有反哲學的哲學:眼前即是一切,何必思前顧後?目标、意義均虛無,當下食、色才真實。這大有解構一切陳規陋習及各類傳統的偉功,但也就不再承認任何價值的存在。無以名之,名之曰“動物的哲學”。
今日有專攻語言的哲學:醫療語言乃一切,其他無益且荒唐。于是,細究語詞用法,厘清各種語病,技術精而又巧,卻與常人無關。無以名之,名之曰“機器的哲學”。
今日有海德格爾哲學:深求人生,發其底蘊,知死方可體生。讀《存在與時間》有一股悲從中來,一往無前的動力在。無以名之,名之曰“士兵的哲學”。
當然,還有各種傳統哲學和宗教及其變種,林林總總。其中,基督教神學最值得重視。它自神而人,超越理性。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海德格爾的存在(Being)也相形見绌。高聳入雲的十字架,在陽光中燦爛輝煌,崇高聖潔,直接撼人心魄,人生真理豈不在是?命運歸宿豈不在此?無怪乎有論者要強調“聖愛”高于倫理,與康德強調道德律令在先、道德感情在後、後者低于前者恰好相反。于是,人生直是一種情感,這是一種普泛而偉大的情感真理。是邪?非邪?
中國哲學也充滿情感,它從來不是思辨理性。但是,它也不是這個“走向十字架”的情感真理。以“實用理性”“樂感文化”為特征的中國文化,沒去建立外在超越的人格神,來作為皈依歸宿的真理符号。它是天與人和光同塵,不離不即。自巫史分家到禮崩樂壞的軸心時代,孔門由“禮”歸“仁”,以“仁”為體,這是一條由人而神,由“人道”見“天道”,從“人心”建“天心”的路。進而,是人為天地立“心”,而非天地為人立“心”。這就是“一個人生”(天人合一:自然與社會有曆史性的統一)不同于“兩個世界”(神人有殊:上帝與包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在内的感性世界相差別)和中國哲學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本根所在。
人生有限,人都要死,無可皈依,無可歸宿,把愛、把心靈、把信仰付托于一個外在超越的符号,比較起來,似乎還順當。現在卻要自己在這個人生和世界去建立皈依、歸宿、信仰和終極關懷,即有限尋無限,于世間求不朽,這條道路豈不更困窘,更艱苦,更悲怆?
在這條道路上,“活”和“活的意義”都是人建構起來的。人為自己活着而悲苦地建構。由于不把它歸結于神的賜予,它就雖然可以超越任何具體人群的時代、社會、民族、階級、集團,卻無法超越人類總體(過去、現在、未來)。過去、現在、未來這種空間化的時間系列便是曆史。人生意義不局限、束縛于特定的時、空,卻仍然從屬于人類的總體,此即“主體性”,即曆史積澱而成的人類學曆史本體。是以人類學曆史本體論一方面是立足于人類社會的馬克思哲學的新闡釋,另一方面又正好是無人格神背景的中國傳統哲學的延伸。這個哲學即以“人活着”為出發點,也就是為什麼要将“使用—制造工具的人類實踐活動”(亦即以科技為标志的生産力)為核心的社會存在命名為“工具本體”。
人活着要吃飯,但人并非為自己吃飯而活着,把一切歸結為吃飯或歸結為因吃飯而鬥争如“階級鬥争”,是一種誤解。人生意義雖不在人生之外,但也不等于人生,于是有“為什麼活”的問題。
馬克思提到“自由王國”,它的前提是人的自由時間的增多。當整個社會的衣食住行隻需一周三日工作時間的世紀,精神世界支配、引導人類前景的時刻将來臨。曆史将走出唯物史觀,人們将走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進而“心理本體”(“人心”—“天心”問題)将取代“工具本體”,成為注意的焦點。于是,“人活得怎樣”的問題日益突出。
從世界情況看,人“如何活”的問題遠未解決,“活得怎樣”隻是長遠的哲學話題,但由“工具本體”到“心理本體”卻似可成為今日一條探尋之道,特别對中國更如此。這不是用“馬克思主義”架構來解釋或吞并中國傳統,而很可能是包含、融化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傳統的繼續前行,它将成為中國傳統某種具體的“轉換性創造”;由于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也可能成為世界意義的某種“後馬克思主義”或“新馬克思主義”。
如張載所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立心”者,建立心理本體也;“立命”者,關乎人類命運也;“繼絕學”者,承續中外傳統也;“開太平”者,為人性建設,内聖外王,“開萬世之太平”,而情感本體之必需也。
“太初有為”還是“太初有言”,似乎也可作為中西哲學異途的某種标志。“太初有言”,進而語言成了人的“界限”“家園”。但各種語言哲學恐怕已不複如日中天,能繼續統治下去了。
“為什麼有有而無無?”“為什麼總是點什麼而不是什麼也不是?”就并非語言所能解答。神秘的是世界就是這樣的。世界存在着,人活着,這就是“有”,這就是“原始現象”,它超越語言。各種宗教、半宗教(包括儒、道)以信仰、情感,禅宗則用棒喝、機鋒來點明這個“有”的個體性、偶發性、超語言的不可傳達、不可規定性。于是,哲學歸趨于詩。
然而,哲學非即詩也。哲學關乎“聞道”和“愛智”。它是由理性語言表達的某種“體認”和“領悟”,雖充滿情感與詩意,卻仍是理性的。“愛智”之“愛”,情感也。“聞道”的“聞”,即“恐懼乎其所不聞”,不“聞”則不足以終極關懷、安身立命,亦情感也。而“智”和“道”,則理性之徑途、内容和體認。
人們說,是語言說人而不是人說語言。但漢字卻顯示“天言”仍由“人言”所建立。漢字是世界文化的大奇迹,它以不動的靜默,“像天下之積赜”,神聖地凝凍、儲存、傳遞進而擴充着生命:“人活着”的各種經驗和準則。難怪傳說要張揚人造字使“天雨粟,鬼夜哭”。是以,恰恰不是随抹随寫,寫了就抹;相反,“敬惜字紙”,應敬惜這生命的曆史和曆史的生命。漢字凝結、融化了各方面的口頭語言,哺育了一個這麼巨大的中華文化的時空實體,并證明着這個實體在活着。《周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系辭焉以盡其言。”又說:“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用知性語言,表述某種超語言的實存的情感體認以推動它的存在,即此之謂也。
進而,哲學作為視角和路的探尋者,便隻是某種觀念、概念的發明者和創造者。因是“發明”,它總反射出“客觀”制約,在古希臘不可能有康德的“發明”,在康德時代也不能有海德格爾的“發明”。因是“創造”,哲學具有“主觀”情緒。康德不進教堂,與他的理性批判有關。海德格爾不反納粹,畢竟令人想起他前此的“此在”充滿悲情的沖力。哲學觀念、概念之不同于許多其他包括科學的觀念、概念,在于它的“無用性”和無所不涉性。哲學不提供知識,而轉換、更新人的知性世界。泰勒斯的“水”,笛卡爾的“我思”,康德的“先天綜合”,海德格爾的“此在”“存在”,等等,無不如此。這如同藝術轉換,更新人的感性世界。于是,無用之用是為大用,作為視角建構和路的探尋,哲學展示了語言的巨大的構造功能。“中國哲學”以實用理性的根底,通由“仁”“義”“道”“氣”等觀念、概念将感性、知性、理性混同融合,更突出地顯示了“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的“語言說人”。這語言與書寫相連,以經驗的曆史性支配着人。
本文書摘部分和圖檔節選自《尋求中國現代性之路》一書,經出版社授權釋出,較原文有删節,标題為編者自拟,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