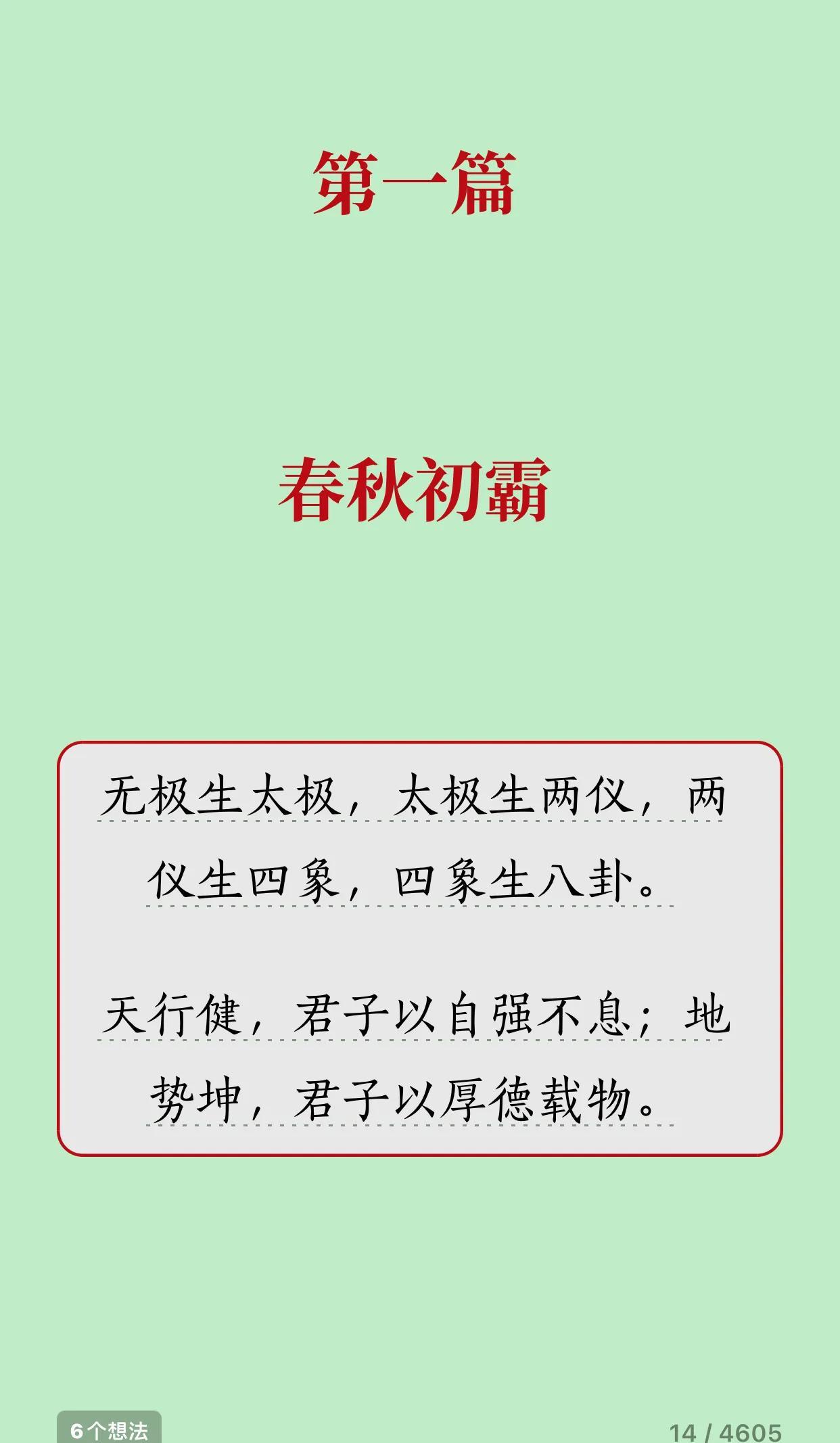公元前744年,从郑国都城新郑的一座宫殿里,传出琅琅读书声。突然读书声被打断了,一位雍容华贵、美丽大方的妇人走进来,对教书先生和殿里的几个学生说道:“段儿岁数小,你应该让他多学一会儿。寤生大了,要多到外面走一走。”“是,母亲。”那个叫寤生的少年应声答道。他在走出宫殿的时候,隐约听到他母亲对教书先生窃窃私语。
这个妇人叫武姜,是郑国夫人。寤生是郑国世子,姬姓,刚满十三岁。在父亲郑武公百年之后,他继承君位是顺理成章的,但他隐隐感到不安,因为他的母亲偏袒小他三岁的弟弟姬叔段。或许有一天,姬叔段继承君位,那姬寤生就要大祸临头……姬寤生不敢想下去,但又不能不想。
“布谷、布谷……”杜鹃鸟在啼叫着。
到了春播的时候了,但中原大地久旱无雨。为了乞求上天下雨,郑武公率领臣民设坛求雨。祭坛上,堆满了干柴,干柴上,架着一头牛、一头猪、一只鹿、一只羊。宣读祭文后,身穿盛装的郑武公点燃了干柴。霎时,烟气腾空。祭坛下的人们见此情景,立刻欢呼雀跃起来。在他们的心中,认为掌管下雨的神灵一定收到了郑国君臣的虔诚心愿。这时,人群中的郑武公突感不适,他一面捂着胸口走向马车,一面嘱咐姬寤生到城外体察民情。
虽然旱情严重,但城外槐树成荫,正值开花的时候,香气扑鼻,蜂飞蝶绕。槐树旁,是大片的龟裂田地,数百名奴隶正在几个人的指挥下辛苦劳作。这些奴隶相貌不一、口音不一,原是战俘和被掠获的平民。在官府,他们每人都有一份丹书,那是用朱砂书写的奴籍。这丹书逼压着他们去耕作。一名年长者扶着木犁,前面十几个人用劲拽着绳子拉犁。木犁的犁头是用尖锐的石头做的。
世子姬寤生登上一个高坡,放眼望去,前面的土地阡陌纵横,犹如一个“井”字。姬寤生知道,这是周朝的井田制留下的土地耕作方式,一井分为九个方块,一个方块一百亩,由一户耕种;周围的八块田由八户耕种,谓之私田,收成全部归耕户所有;中间一块是公田,由八户共耕,收入全归封邑贵族所有。
教书先生告诉过姬寤生,井田制自夏朝就有了,现在发展到极致,是百姓生存的基本依靠。姬寤生虽小,但也明白有饭吃才有人生存,人口旺盛才有国家富强。他遵从父命,边走边看,边看边走,一个时辰的工夫就走出了十几里地。翻过一个土坡后,姬寤生看到这儿的农人不在田间劳作,而是坐在槐树下乘凉闲聊。带着疑问,姬寤生问他们为什么不干活。
一位家臣也就是替封邑贵族领着奴隶干活的人答道:“我们并不是怠工,而是干劲十足。因为明天就要下雨,所以我们都在这儿等着雨水滋润田地呢。”
“明天要下雨?难道你们知道都城内刚刚进行祭祀求雨?”姬寤生问道。
“祭祀的事,我们也听说了。不过,明天要下雨的消息是镐京过来的一位贵人预言的。”家臣答道。
“他的预言准吗?”姬寤生问。
“很准,凡是他预言的,都一一应验。”家臣恭敬地答道。
从家臣的眼神中,姬寤生感觉到这位镐京来的贵人神不可测。姬寤生想去拜访他,但他不急着去找这位贵人,而是要看明天是否真的会下雨。这种沉稳的性格与他的年龄并不相符,或许是因为他在宫中长期受压抑所致,也或许是因为先天素质过硬。
世子姬寤生回到都城新郑,天已经黑了,这时竟然起了雾,而且越来越大。
第二天天还没亮,雨就下了起来。郑国群臣都向郑武公道喜,祝贺祭祀灵验,他们个个眉飞色舞。郑武公强撑着身体鼓励大家用心督促农耕,务必搞好春播。将近一天了,郑武公感到胸口越来越疼。
雨越下越大,姬寤生向父亲问安后,便坐着马车去寻找那位镐京来的贵人。他有很多问题想问,既问如何知道第二天要下雨,还要请教如何避祸趋利。在雨中,在车上,姬寤生又一次回想到自己名字的由来——
十三年前,母亲武姜难产,痛得死去活来,几次走近鬼门关,最终生下了他。小孩子出娘胎,一般是头先出来,但他是脚先出来,因此郑武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寤生。姬寤生四岁的时候,弟弟姬叔段出生了。从那以后,母亲武姜对他越来越冷漠。
世子姬寤生想,如果那位贵人真要是擅长预测,他就问问自己今后的吉凶,还要问问今后如何在宫廷中进退。
雨没停,车停了。姬寤生下车,一点儿没有世子的架势,向那位镐京来的贵人拜了又拜。镐京来的贵人叫祭足,原是周王室的一名小吏,西戎攻打镐京的战乱后,祭足到了这里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