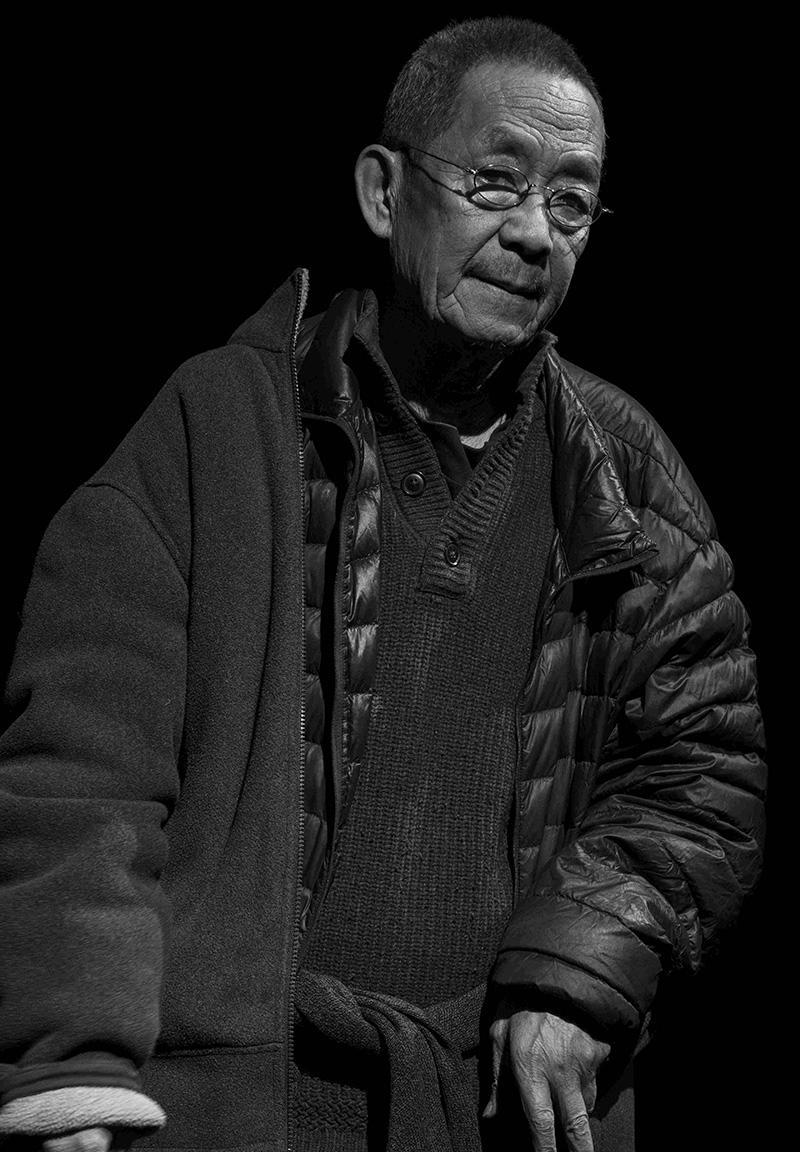
1994年,歌德学院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林兆华重新编排浮士德,犹豫了一年,然后回复了歌德学院院长。但中国人对它有中文的解释,如果不是跟我儿子一起来我就不划船了。"
然后他带来了乐队"43 Bower Street",让这个时髦的乐队大受欢迎。
在一部宏大而庄严的经典戏剧中加入摇滚元素,震惊了所有观众,也让严谨的戏剧专家感到惊讶,理论家和媒体都声称这个人"根本没有理论框架!但在林兆华看来,舞台美术不是理论出来的,他承认从他当导演的那天起就没有理论依据,并声称"是直觉救了我,当时我也发现了很多直觉的书,抄袭了一些引语,给自己的勇气。"
虽然他一直声称"他的创作状态也是半费半懒,没有组织出一个完整的导演构思。""但是,中国副总裁,一个柯本出生的学生,怎么可能不懂戏剧呢?"
他只是把规则和规则看成是绊脚石。
他说,创造者必须始终蔑视权威。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7">1. 烟花再华丽,看多不打扰</h1>
大多数伟大的人都靠直觉生活。要看林兆华的戏,很难想象下一幕会出现什么惊人的道具或台词。谁会想到,一部本该被归类为严肃文学的戏剧,竟然会如此俏皮呢?但在林兆华眼里,严肃的舞台剧是那么的好玩和好玩。
天津人骨子里具有不拘一格的性格。小时候,林兆华精力充沛,玩乐的乐趣十足。小学因为顽皮被降级了两年,他家门口的酒馆被俄罗斯人开了,他和小伙伴放学后跑到酒吧,用一根小棍子抵住女老板的裙子,晚上会跑到巷子里用手电筒躲在亲密情人的脸上。长老们给他的评论是"坏的",但他只承认"不承认"不好。
21岁那年,他进入了中国剧,但玩性爱还是没有改变,但现在他不再玩手电筒和棍子,而是想"玩戏"。但那个时代剥夺了他的玩权,一心想钻戏的他被安排在13灵水库工作,一年只有三五天象征性地坐在教室里,也只是学习大庆,当时他总是在想,"我为什么要来玩戏?为了深入农村和工厂,我学习农业学院,好吗?"
天生的叛逆者总是一个选择,他开始给医院的领导人写信和建议,后来被贴上了"自由派"的标签。
幸运的是,毕业后,他做了他作为导演想做的事情。他浪费了几年的学习时间来弥补这一点。当时他自称是"屁帘导演",后面跟着老一辈人叫谁老师,但真的让他开门,但对剧的理解更多,骨子里的叛逆精神又开始腾飞,有纪律地引导了几部不折不扣的戏,他开始沉思, "这部剧在中国几十万的历史中,为什么剧本要按照方式写?"导演是被老导演的思维所引导,演员们也想复制老模式来演戏吗?"在他的感觉中,这部剧应该像烟花一样,点一条新线,总是一样的声音像颜色,烟花再亮,看更不打扰?"
找志同道合的非演员,做自己不喜欢的戏剧,也做一个最不喜欢导演的导演。自由主义的幼苗开始在他们的心中忍受着疯狂的春天。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1">2. 表单本身就是内容</h1>
1982年,高行健(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与铁道剧团编剧刘慧源合作,创作了开创性的戏剧《绝对信号》,讲述了火车抢劫期间社会失业青年的心理变化。林兆华将其改编成一部没有场景的小剧场式戏剧,但艺术领袖却不支持,因为《绝对信号》的表演主题和林兆华的"小剧场"形式不符合社会情境的需要,二是侮辱了严肃戏剧的正统观念,其主题和表演的开创性风格使得很难登上大雅殿堂。但林兆华的团队已经成立,剧本和演员都准备好了,他固执的韧性又高了起来。
他首先将剧本改为"用榜样提醒年轻人"的积极主题,最后才有资格进行内部审查。但排练依然受到"歧视",院子里只提供了七盏灯,一张木桌三把椅子,剧的火车车厢都是用旧纸箱做的,林兆华买了几十个手电筒,这次不是去巷子拍那些恋人亲密闹剧,而是因为追求光是不够的。如此艰难而"不为人知"的他咬牙切齿地排成一排,内部检讨时,很多从事一生舞台剧的老大咖都大喊上瘾,"也可以这样演!"现场小组同意了这个节目。
《绝对信号》从1982年11月开始,共演出100多场,场馆赞不绝口,第一任艺术总裁曹瑜先生亲自写信表示祝贺,美国报纸也报道称"中国先锋戏剧诞生了!"
林兆华的激情被彻底点燃。年度"放屁导演"终于开始掌控新剧的旗帜。他也变得更忙了。在担任艺术副校长后,他一直对行政工作毫无兴趣,院长办公室也从未找到自己的影子,他有自己的"狗屋":院子里有一座破旧的三层建筑,一张棉帘,一张硬床,凌乱而充满只有他能读懂的"戏剧因素",在《狗屋》中诞生了无数赞美的优质作品, 每种独特的风格都非常不同。
在排好新故事时,并没有提前拿出完整的剧本,而是要求演员们在鲁迅原来的蓝图中"即兴演讲"。演员的日常任务不是排好台词,而是一遍又一遍地读《新奇兵》,找到每个人最能触手可及的句子,然后在舞台上激情拼搏,完成最后的剪辑,每场演出的动作和台词都不一样。
那是2000年,他的"狗屋"地方太小而无法打开,他们把所有演职人员带到北京南城一个废弃的作坊吃了一个半月,住在那扇紧闭的门里,舞台上做煤球道具机的是来自农村的舞蹈美人寻找真人, 道具和七八吨煤球,也就是真正的煤球,演员每天在煤球里爬行和滚动,沐浴全身上下连鼻孔都是黑色的。
更令人惊奇的是,当他们去德国演出时,球队的行李被压缩压缩,但巨大的煤球机,连同七八吨煤球,却被运上了飞机。令林印象深刻的是大汽油桶,他在德国休息期间亲自玩过,把煤球放在汽油桶里,在上面放上炉子镊子,在上面烤红薯,"真的烤,真的很好吃,真的很香。"
"林兆华这么老了,怎么还玩形式主义?"也没有从家族中学到榛尔明,回归哲学的深度。"对于别人的困惑和疑惑,林兆华只是笑而不说话,闲置会还一句话:形式本身就是内容,认真本身就是态度。
< h1 级"pgc-h-right-arrow" 数据轨道 s 42 > 3</h1>
林兆华承认,他一生都在认真踢球,认真踢球,玩得很开心。
1998年,林兆华病得很重,躺在自己的"狗窝"里一个多月,突然有一天一百种病都跳了起来,他把契诃夫的《三姐妹》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演成一出戏。学院的领导还是不一致,这么俏皮的经典,你让两位文学大师和全世界的观众多尴尬啊?林郑月娥只能靠自己筹集资金。
这是一部杰作,在未来几十年内都不会过时。于华在演出时表示,该剧"将契诃夫的忧郁美和贝克特的悲伤粗俗放在同一舞台上,同时又出人意料,令人愉悦。但最终只打了十几场戏就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丢了几辆阜康车,当阜康车一百一万一万一辆"。我没有钱可失去。"
"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制度,最大的问题是扼杀个性,大多数舆论强调一致性和统一性,但艺术最需要个性,"他说。至于自掏腰包的戏剧,他承认:"乐趣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
他永远记得这个"二合一"舞台上的经典场景:水中的孤岛,三姐妹等待离开;隔着一片寂静的水面,线掉了下来,掉进了水里,落入了他的心脏。水不宽,岛上的人可以轻松脱身,岛外的人也很容易闯入。但他们仍然无动于衷,默默地等待着,他们总是蕴含着希望,绝望的希望,就像林昭华本人一样,他永远不会在希望中绝望。
2011年,林兆华的参演题目是《什么是戏剧?2012年,在林兆华戏剧邀请赛上,他问自己:戏剧是一场游戏。一部剧不是重复一个文学主题和人生学说,而是通过导演和演员倾注到作品中的感情重新理解,在林兆华的脑海中,这是导演的"第二主题",而他对这部剧的理解是,深刻太沉重,太浅的生意,可以做一些像是幸福的事情。"我不为沙斯比·契诃夫大师服务,只是为了自我表达。
就像他的哈姆雷特排一样。剧场的南胡北林是上海的胡为民。胡为民说,戏剧的老百姓一定只排好自己的《哈姆雷特》,但对于这部经典经典,即便如此自信狂妄的林兆华也不敢轻易尝试,后来胡为民的追悼会上,林兆华郑重承诺:我必须把自己的《哈姆雷特》排成一行。
最后的舞台背景是用破布和棉拼贴画,一个破碎的电风扇,一把旧理发师的椅子和破碎的旧电器制成的。演员们不戴假发,甚至不化妆,服装上满是褶皱,在类似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老上海的场景中问:生死!
这似乎是一个中国正统派的问题,就像是旧戏剧理论的丧钟。记者采访他时,他说,这出戏,是给胡为民做梦不是我的。戏剧太难了,一本书要写几年,回顾几年,排几年,十几年就这样过去了,时代怎么能跟上呢?
后来排着《白鹿原》,他特意找了西安"老空"剧团,从陕北到北京,其实剧中并不是很需要这些歌曲,但是当他得知《老空》不传姓,只传自己的家,全世界都会唱这七八个人,而最小的已经快六十岁了, 他决定把"老空洞"放上去。陈某忠实地写《白鹿原》时说,要写一本死人可以睡得像枕边书。这本书成了,陈忠心丧气。老蛀牙也是如此,恐怕一天也不会继续下去。"
< h1级"pgc-h-arrow-right"数据轨道"43"> 4.小孙子喜欢爬一棵名叫林兆华的树</h1>
几年来,林郑月娥一直不喜欢在体制内生存。在他的自传《导演之书》(The Director's Book)的封面上,他嘲笑自己。"剧是我妈妈,艺术是我爸爸,但他们不爱我,谁让我做个'逆子'?"
的确,这样一个气势汹汹的淘气老男孩,总是传统戏剧的反滋生者,也是踢法庭的替代者,以这种方式诠释了自己的反身份。"我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将我对戏剧的演绎传达给观众,但传统的、现成的表达形式是不可能的,我必须找到一种特殊的形式来传达我的演绎,但在艺术创作中,文本根本无法诠释我的戏剧。坦率地说,我认为艺术创作不可能依靠理论,我对理论有蔑视。"
中国戏剧诞生百年研讨会他收到了邀请但没有参加,人民大会堂奖,总书记亲自领取也因为排练没有赶上,他请于陶劳工作,回来和颁奖证书一起,"组织认可,心"。"至于他在中国无戏剧中获得的行政职位和荣誉,他完全不热情,明白领导和观众不了解自己。其实我是在党的教育下长大的,但阴阳也保留了一点个性,没有窒息,也许他们想消磨时间为时已晚,我只是混在一起。"
研讨会的另一个决定是,在北京青湖公园为每位获奖者种植一棵白色果树,并命名品牌,未来在这里建造一个"中国戏剧主题公园"。虽然在北京,但林兆华并没有专程去看望这棵树,也没有等它浇水一个施肥什么的,带小孙子去看一次。
"小孙子喜欢这棵树,也叫林兆华,爬上树干,赢奖品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