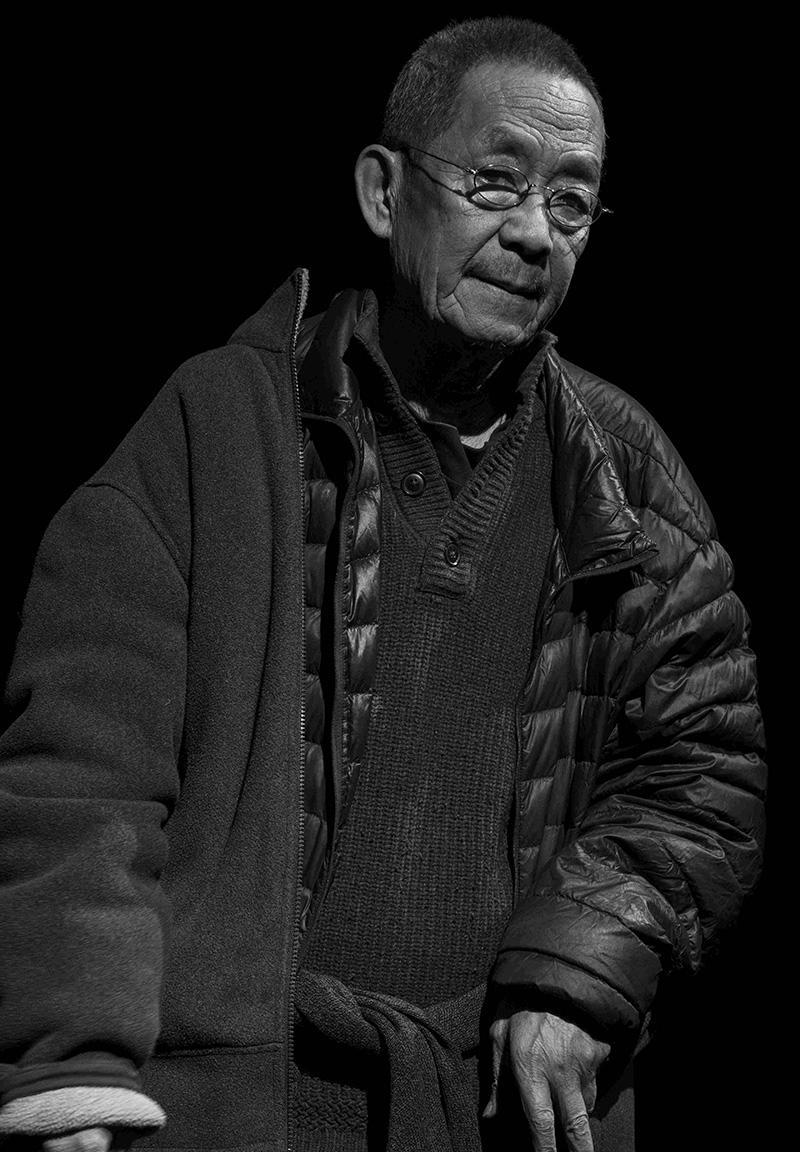
1994年,歌德學院請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林兆華重新編排浮士德,猶豫了一年,然後回複了歌德學院院長。但中國人對它有中文的解釋,如果不是跟我兒子一起來我就不劃船了。"
然後他帶來了樂隊"43 Bower Street",讓這個時髦的樂隊大受歡迎。
在一部宏大而莊嚴的經典戲劇中加入搖滾元素,震驚了所有觀衆,也讓嚴謹的戲劇專家感到驚訝,理論家和媒體都聲稱這個人"根本沒有理論架構!但在林兆華看來,舞台美術不是理論出來的,他承認從他當導演的那天起就沒有理論依據,并聲稱"是直覺救了我,當時我也發現了很多直覺的書,抄襲了一些引語,給自己的勇氣。"
雖然他一直聲稱"他的創作狀态也是半費半懶,沒有組織出一個完整的導演構思。""但是,中國副總裁,一個柯本出生的學生,怎麼可能不懂戲劇呢?"
他隻是把規則和規則看成是絆腳石。
他說,創造者必須始終蔑視權威。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7">1. 煙花再華麗,看多不打擾</h1>
大多數偉大的人都靠直覺生活。要看林兆華的戲,很難想象下一幕會出現什麼驚人的道具或台詞。誰會想到,一部本該被歸類為嚴肅文學的戲劇,竟然會如此俏皮呢?但在林兆華眼裡,嚴肅的舞台劇是那麼的好玩和好玩。
天津人骨子裡具有不拘一格的性格。小時候,林兆華精力充沛,玩樂的樂趣十足。國小因為頑皮被降級了兩年,他家門口的酒館被俄羅斯人開了,他和小夥伴放學後跑到酒吧,用一根小棍子抵住女老闆的裙子,晚上會跑到巷子裡用手電筒躲在親密情人的臉上。長老們給他的評論是"壞的",但他隻承認"不承認"不好。
21歲那年,他進入了中國劇,但玩性愛還是沒有改變,但現在他不再玩手電筒和棍子,而是想"玩戲"。但那個時代剝奪了他的玩權,一心想鑽戲的他被安排在13靈水庫工作,一年隻有三五天象征性地坐在教室裡,也隻是學習大慶,當時他總是在想,"我為什麼要來玩戲?為了深入農村和工廠,我學習農業學院,好嗎?"
天生的叛逆者總是一個選擇,他開始給醫院的上司人寫信和建議,後來被貼上了"自由派"的标簽。
幸運的是,畢業後,他做了他作為導演想做的事情。他浪費了幾年的學習時間來彌補這一點。當時他自稱是"屁簾導演",後面跟着老一輩人叫誰老師,但真的讓他開門,但對劇的了解更多,骨子裡的叛逆精神又開始騰飛,有紀律地引導了幾部不折不扣的戲,他開始沉思, "這部劇在中國幾十萬的曆史中,為什麼劇本要按照方式寫?"導演是被老導演的思維所引導,演員們也想複制老模式來演戲嗎?"在他的感覺中,這部劇應該像煙花一樣,點一條新線,總是一樣的聲音像顔色,煙花再亮,看更不打擾?"
找志同道合的非演員,做自己不喜歡的戲劇,也做一個最不喜歡導演的導演。自由主義的幼苗開始在他們的心中忍受着瘋狂的春天。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1">2. 表單本身就是内容</h1>
1982年,高行健(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人)與鐵道劇團編劇劉慧源合作,創作了開創性的戲劇《絕對信号》,講述了火車搶劫期間社會失業青年的心理變化。林兆華将其改編成一部沒有場景的小劇場式戲劇,但藝術領袖卻不支援,因為《絕對信号》的表演主題和林兆華的"小劇場"形式不符合社會情境的需要,二是侮辱了嚴肅戲劇的正統觀念,其主題和表演的開創性風格使得很難登上大雅殿堂。但林兆華的團隊已經成立,劇本和演員都準備好了,他固執的韌性又高了起來。
他首先将劇本改為"用榜樣提醒年輕人"的積極主題,最後才有資格進行内部審查。但排練依然受到"歧視",院子裡隻提供了七盞燈,一張木桌三把椅子,劇的火車車廂都是用舊紙箱做的,林兆華買了幾十個手電筒,這次不是去巷子拍那些戀人親密鬧劇,而是因為追求光是不夠的。如此艱難而"不為人知"的他咬牙切齒地排成一排,内部檢讨時,很多從事一生舞台劇的老大咖都大喊上瘾,"也可以這樣演!"現場小組同意了這個節目。
《絕對信号》從1982年11月開始,共演出100多場,場館贊不絕口,第一任藝術總裁曹瑜先生親自寫信表示祝賀,美國報紙也報道稱"中國先鋒戲劇誕生了!"
林兆華的激情被徹底點燃。年度"放屁導演"終于開始掌控新劇的旗幟。他也變得更忙了。在擔任藝術副校長後,他一直對行政工作毫無興趣,院長辦公室也從未找到自己的影子,他有自己的"狗屋":院子裡有一座破舊的三層建築,一張棉簾,一張硬床,淩亂而充滿隻有他能讀懂的"戲劇因素",在《狗屋》中誕生了無數贊美的優質作品, 每種獨特的風格都非常不同。
在排好新故事時,并沒有提前拿出完整的劇本,而是要求演員們在魯迅原來的藍圖中"即興演講"。演員的日常任務不是排好台詞,而是一遍又一遍地讀《新奇兵》,找到每個人最能觸手可及的句子,然後在舞台上激情拼搏,完成最後的剪輯,每場演出的動作和台詞都不一樣。
那是2000年,他的"狗屋"地方太小而無法打開,他們把所有演職人員帶到北京南城一個廢棄的作坊吃了一個半月,住在那扇緊閉的門裡,舞台上做煤球道具機的是來自農村的舞蹈美人尋找真人, 道具和七八噸煤球,也就是真正的煤球,演員每天在煤球裡爬行和滾動,沐浴全身上下連鼻孔都是黑色的。
更令人驚奇的是,當他們去德國演出時,球隊的行李被壓縮壓縮,但巨大的煤球機,連同七八噸煤球,卻被運上了飛機。令林印象深刻的是大汽油桶,他在德國休息期間親自玩過,把煤球放在汽油桶裡,在上面放上爐子鑷子,在上面烤蕃薯,"真的烤,真的很好吃,真的很香。"
"林兆華這麼老了,怎麼還玩形式主義?"也沒有從家族中學到榛爾明,回歸哲學的深度。"對于别人的困惑和疑惑,林兆華隻是笑而不說話,閑置會還一句話:形式本身就是内容,認真本身就是态度。
< h1 級"pgc-h-right-arrow" 資料軌道 s 42 > 3</h1>
林兆華承認,他一生都在認真踢球,認真踢球,玩得很開心。
1998年,林兆華病得很重,躺在自己的"狗窩"裡一個多月,突然有一天一百種病都跳了起來,他把契诃夫的《三姐妹》和貝克特的《等待戈多》演成一出戲。學院的上司還是不一緻,這麼俏皮的經典,你讓兩位文學大師和全世界的觀衆多尴尬啊?林鄭月娥隻能靠自己籌集資金。
這是一部傑作,在未來幾十年内都不會過時。于華在演出時表示,該劇"将契诃夫的憂郁美和貝克特的悲傷粗俗放在同一舞台上,同時又出人意料,令人愉悅。但最終隻打了十幾場戲就不能繼續下去了,因為"丢了幾輛阜康車,當阜康車一百一萬一萬一輛"。我沒有錢可失去。"
"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教育,我們的制度,最大的問題是扼殺個性,大多數輿論強調一緻性和統一性,但藝術最需要個性,"他說。至于自掏腰包的戲劇,他承認:"樂趣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
他永遠記得這個"二合一"舞台上的經典場景:水中的孤島,三姐妹等待離開;隔着一片寂靜的水面,線掉了下來,掉進了水裡,落入了他的心髒。水不寬,島上的人可以輕松脫身,島外的人也很容易闖入。但他們仍然無動于衷,默默地等待着,他們總是蘊含着希望,絕望的希望,就像林昭華本人一樣,他永遠不會在希望中絕望。
2011年,林兆華的參演題目是《什麼是戲劇?2012年,在林兆華戲劇邀請賽上,他問自己:戲劇是一場遊戲。一部劇不是重複一個文學主題和人生學說,而是通過導演和演員傾注到作品中的感情重新了解,在林兆華的腦海中,這是導演的"第二主題",而他對這部劇的了解是,深刻太沉重,太淺的生意,可以做一些像是幸福的事情。"我不為沙斯比·契诃夫大師服務,隻是為了自我表達。
就像他的哈姆雷特排一樣。劇場的南胡北林是上海的胡為民。胡為民說,戲劇的老百姓一定隻排好自己的《哈姆雷特》,但對于這部經典經典,即便如此自信狂妄的林兆華也不敢輕易嘗試,後來胡為民的追悼會上,林兆華鄭重承諾:我必須把自己的《哈姆雷特》排成一行。
最後的舞台背景是用破布和棉拼貼畫,一個破碎的電風扇,一把舊理發師的椅子和破碎的舊電器制成的。演員們不戴假發,甚至不化妝,服裝上滿是褶皺,在類似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老上海的場景中問:生死!
這似乎是一個中國正統派的問題,就像是舊戲劇理論的喪鐘。記者采訪他時,他說,這出戲,是給胡為民做夢不是我的。戲劇太難了,一本書要寫幾年,回顧幾年,排幾年,十幾年就這樣過去了,時代怎麼能跟上呢?
後來排着《白鹿原》,他特意找了西安"老空"劇團,從陝北到北京,其實劇中并不是很需要這些歌曲,但是當他得知《老空》不傳姓,隻傳自己的家,全世界都會唱這七八個人,而最小的已經快六十歲了, 他決定把"老空洞"放上去。陳某忠實地寫《白鹿原》時說,要寫一本死人可以睡得像枕邊書。這本書成了,陳忠心喪氣。老蛀牙也是如此,恐怕一天也不會繼續下去。"
< h1級"pgc-h-arrow-right"資料軌道"43"> 4.小孫子喜歡爬一棵名叫林兆華的樹</h1>
幾年來,林鄭月娥一直不喜歡在體制内生存。在他的自傳《導演之書》(The Director's Book)的封面上,他嘲笑自己。"劇是我媽媽,藝術是我爸爸,但他們不愛我,誰讓我做個'逆子'?"
的确,這樣一個氣勢洶洶的淘氣老男孩,總是傳統戲劇的反滋生者,也是踢法庭的替代者,以這種方式诠釋了自己的反身份。"我必須找到一種方式,将我對戲劇的演繹傳達給觀衆,但傳統的、現成的表達形式是不可能的,我必須找到一種特殊的形式來傳達我的演繹,但在藝術創作中,文本根本無法诠釋我的戲劇。坦率地說,我認為藝術創作不可能依靠理論,我對理論有蔑視。"
中國戲劇誕生百年研讨會他收到了邀請但沒有參加,人民大會堂獎,總書記親自領取也因為排練沒有趕上,他請于陶勞工作,回來和頒獎證書一起,"組織認可,心"。"至于他在中國無戲劇中獲得的行政職位和榮譽,他完全不熱情,明白上司和觀衆不了解自己。其實我是在黨的教育下長大的,但陰陽也保留了一點個性,沒有窒息,也許他們想消磨時間為時已晚,我隻是混在一起。"
研讨會的另一個決定是,在北京青湖公園為每位獲獎者種植一棵白色果樹,并命名品牌,未來在這裡建造一個"中國戲劇主題公園"。雖然在北京,但林兆華并沒有專程去看望這棵樹,也沒有等它澆水一個施肥什麼的,帶小孫子去看一次。
"小孫子喜歡這棵樹,也叫林兆華,爬上樹幹,赢獎品真好。